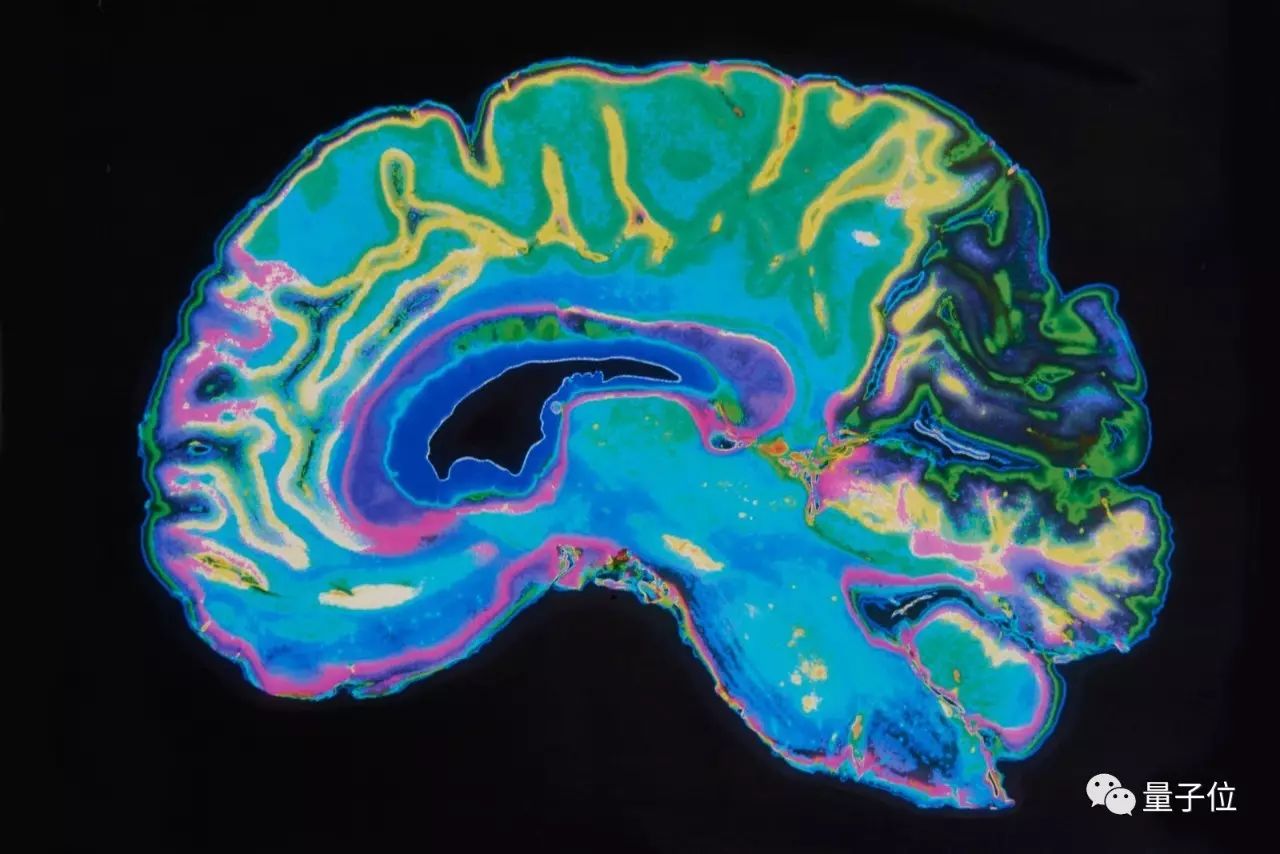中国的高等教育学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酝酿,到1983年3月进入《学科目录》,其实只有短短的五六年时间。在进入《学科目录》之前,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实际上还很少。第一部名为“高等教育学”的著作,即潘懋元的《高等教育学讲座》,1983年8月才正式出版。作者在书中坦陈,“因为现在中国还没有一部高等教育学”,所以这本书“只能谈一点关于高等教育学基本体系和内容的设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高等教育学自身的条件在当时还很不充分。作为学科诞生标志的第一部《高等教育学》,其上、下册分别在1984、1985年出版。从时间顺序上看,高等教育学进入《学科目录》在前,而作为学科诞生标志的著作却出版在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高等教育学早在1983年就进入《学科目录》而成为建制内学科,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早产儿”:还没有等到足月,还没有等到标志性的《高等教育学》出版,就已经在《学科目录》上出生了。
在我国的学科体制之下,早早列入《学科目录》,这对于学科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后续效应,高等教育学40年的快速发展就是有力的证明。
首先,进入目录就意味着学科获得了体制内的“户口”,并且获得由“户口”决定的各种资格,特别是高层次学位授予和研究生培养的资格,从而使得众多的高等教育研究者有了自己的学科归属,有了安身立命的学术领地,可以“学科化生存”。
据笔者对我国高校官网上研究生招生信息的不完全统计,2022年我国高校以“高等教育学”为“研究方向”(即“二级学科”)的博士点约有36个,硕士点已超过200个;如果再加上公共管理类学科点和专业学位点的相关方向,那么,与高等教育研究相关的博、硕士学位点数量会更多。由于获得了建制内身份和学位授予权,因此以学位点为依托的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组织基础相对比较牢固,不会被轻易取消或并入其他机构。仅此一点,40年前推动高等教育学进《学科目录》的先驱者们,功莫大焉。
其次,进入《学科目录》之后,高等教育学置身于学科体系之林,有了明确的学科参照系,虽然不可能与自然科学相比拟,但高等教育学作为教育学一级学科中的一个新成员,必不可少地要与教育学其他的二级学科相比较,甚至还不得不与其他的社会科学相比较。
身处学科参照系之中,学科间的异同、优势和劣势,显露得格外醒目,这就有利于高等教育学在研究的实践中不断地进行自我反思、自我改进,有利于加速内涵的发展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
再者,进入《学科目录》之后,随着学位点的增加,高等教育学硕士和博士的培养过程对学科本身的建设和发展,形成了强有力的倒逼作用。
只要研究生招进来了,这种作用就会直接而现实地发生着;任何一个对学生负责任的学位点,面对着自己的学生,都不得不直面这样的拷问:用什么培养他们?以什么方式培养他们?要把他们培养成什么样的硕士、博士,怎样才能使得他们在毕业时真正学有所获、学有所长?这就需要在培养过程中不断研究和调整培养计划,不断改进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不断提高培养质量;任何负责任的研究生培养过程,实质上都是学科自身充实、改进和发展的过程。在教育学发展史上,很多学科其实都是直接应师资培训、校长培训的实际需要而产生并得以发展的,高等教育学也是其中之一。
另外,进入《学科目录》也有利于吸引更多有才华的年轻学者,有利于吸收体制内外的各种学术资源,有利于扩大学术发表和出版的园地。这些对于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发展,也都是显而易见的利好。
4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学的研究质量和学术水平一直在不断地进步和提高,这是不争的事实。将当前各大期刊上高等教育学的论文与40年前的做一个简单比较就不难看出,在学术立场、研究方法、研究质量和学术水平方面,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与高等教育学早早进入《学科目录》,学科建设目标取法乎上,当然有重要的相关性。
不过,“早产”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某些先天的不足,比如孕育不充分、营养不良、体质不强,在学科上表现为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不够严密、学术范式不够严格、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不够科学,等等。40多年前,先驱者们在推动高等教育学进《学科目录》时,实在来不及从容地思考这门新学科到底需要哪些条件和规范,也等不及这些条件和规范成熟之后再去创建学科,就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进入《学科目录》的迫切性显然超过了条件和规范的建设(这本身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情有可原。如果我们因此而苛责先驱者,那显然既不公道,也于事无补。
“早产”的先天不足,原本可以在后天加以弥补。事实上,弥补的努力一直都在进行之中,从《高等教育辞典》到《教育大辞典》《教育学名词》,从《高等教育学新论》《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到一批严肃的译介成果、史料汇编,以及一大批以比较严格的学术规范和方法对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的诸多成果,都可以看作是对学科先天不足进行弥补的努力,效果也有目共睹。但总的来看,后天的弥补还不够充分,还没有达到理想的程度。这与教育学研究本身特有的复杂性和高难度有关,也与中国高等教育学在出生之后面对的后天环境有关:它一出生,面对的就是一个超常规发展的研究对象,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热点、主题一个紧接着一个,令人目不暇接,以致高等教育学在出世之后,依然等不及条件的成熟和规范的建设,而是不由自主地被裹挟到超常规发展的节奏之中,以致形成了“热点趋向”和“研究泛化”的偏颇。研究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的热点问题,本来也是高等教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本来无可厚非,但要害在于“跟风”:一个热点出来,往往是一哄而上,主题先行,随风而飘,往往身不由己地偏离了学术的轨道;“热点趋向”成风,“研究泛化”也就难以避免,以至于学术研究与工作研究的边界被混淆。其后果就是,先天不足不仅没有得到充分弥补,后天失调又接踵而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等教育学内涵的发育和成熟。
高等教育学的先驱者们很早就敏锐地看到这种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现象,并力图有所矫正。1991年,
潘懋元针对很多研究者的困惑,指出高等教育研究当时在方法论上的两大缺陷,“一是理论脱离实际,内容贫乏,理论空泛,教条味重;一是实际脱离理论,铺叙事实,就事论事,发表局部经验或个人感想,以偏概全,不能上升到一般理论上来。”
1999年,汪永铨直面“教育学科的不成熟”,指出“人们容易把某些个别的狭隘的经验,甚至是某种主观愿望(尽管可能是善良的愿望)当作是教育发展的规律或必然”;他强调,“要在提高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水平上下功夫”,“建立能反映高等教育研究特性的方法和方法论”,培育“不唯上、不唯书、不唯众、不唯我、不唯风”的“五不唯”学风。这些声犹在耳的论述今天听来仍振聋发聩,对当下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