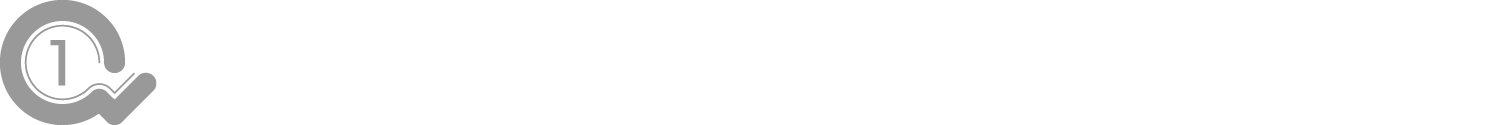
我在《第一财经日报》工作的时候,策划过关于万达集团在吉林长白山圈地、部分手续不全的报道,由产经中心一批优秀的编辑记者深入实地调查,刊出后曾经沸沸扬扬。
去年初,我在微信公众号发了
《致王健林书:万达式扩张狂飙该歇歇了》
,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是,
“让万达式扩张狂飙歇一歇吧,也让诚惶诚恐的心意代替世界首富的梦想”
。在爱奇艺的脱口秀节目中,我也批评过王健林公开向迪士尼(上海)的喊话——
“我在公司内部讲了一句话,要让迪士尼中国的这一块财务十年到二十年之内盈不了利”
。迪士尼是世界最大的IP工厂,万达是中国最大的商业地产商,商业逻辑不一样,把话说得这么大、这么绝对,不好。
在一些论坛上,我和王健林打过照面,但直到今天,没有交流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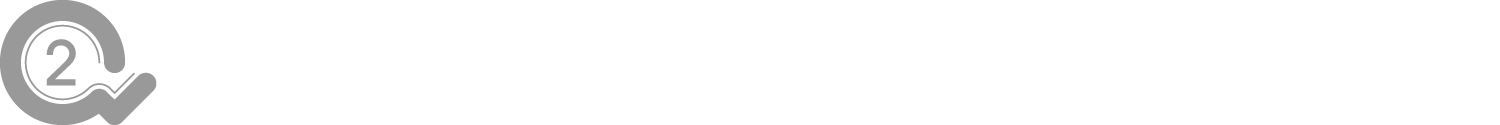
今年全国两会,在3月10日举行的记者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回答人民银行系统内媒体《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网记者关于跨境直接投资的问题时说,
“大家就形成一种风,都在考虑对外投资,其中也不乏有一部分是过热的情绪,投资具有盲目性,有的人也是事情做得很
急”,“这
其中有一部分实际上跟我国对外投资的产业政策要求不符合,比如投一些体育、娱乐、俱乐部,对中国也没有太大的好处,同时在外面还引起了一些抱怨。因此,进行一定程度的政策指导,我们认为是有必要的,也是有成效的。”
人民银行系统的媒体来提这个问题,说明这个内容是周小川一定要说的。央行的职责并不是选择什么样的产业项目,那是发改委、商务部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考虑的事,这又说明
周小川表达的意见,不是代表自己,而是代表政府的统一立场。
体育、娱乐、俱乐部,万达都有投,量还很大。这一类的东西,不像收购一个工厂,估值比较恒定,其溢价幅度往往很难把握。有人说不贵,有人就说高溢价。在2015年人民币备受贬值压力的时候,到国外买这样的东西,虽然符合万达的轻资产转型方向和宏观资产配置原则,但
时机肯定欠妥
。
然后我们就看到
了6月22日
万达的
“股
债双杀”
,起
因是银监会通知部分大型银行,要求它们提供对包括万达在内的5家集团的境外投资借款情况及风险分析。再往后,王健林把旗下文旅项目91%的股权和酒店卖给了融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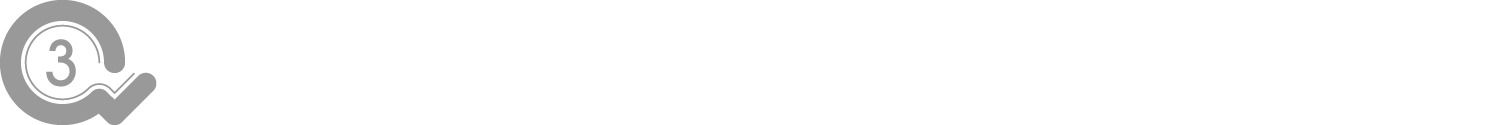
7月17日,有一条新闻在网上热传,就是银监会口头转达对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六个境外项目的处理措施。主要精神是,
“万达集团六个境外投资项目是近期我国对外投资严格管控的领域,拟对六个项目严肃处理,中国金融机构不得就万达已完成并购交割的四个海外交易向其提供融资服务”
。《新京报》记者称,从消息人士处证实,这六个境外投资项目的融资确已受到严格管控;对万达集团等企业海外投资项目的融资风险排查,发改委外资司也有参与。
我的看法是,
如果万达这六个境外投资项目在进行交易前的报批环节,政府部门就明确反对或者提出了修正、暂缓等意见,那今天的处理是万达应当承担的代价。
虽然总体上说,企业对市场的判断要比政府更准确,企业花自己的钱也会更用心更谨慎,反倒是政府主导的很多产业政策和项目问题很多,“打水漂”的也不少——但既然政府有明确的规定,你非要突破,而不是通过理性的博弈获得理解和支持——那就要认,就要服,就要遵从。
如果当时政府部门不同意,而基于自主决策,你认为你的方向是对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硬做了,事后也不是没有辗转腾挪的空间。我在多年采访和研究企业家的过程中发现,
那些有性格、敢冒险、成就卓著的企业家,往往不是那么“听话”,什么都听政府要求,四平八稳,很难成大事。但是,不听话而能成事,需要有两个条件,要么是政府官员能从发展的角度包容你,要么你有循循善诱说服官员的能力。
第一财经采访过中国第一批“全国优秀企业家”之一、曾任鞍山钢铁公司总经理的
李华忠
。他说,企业家永远要走在时代的前面。20世纪90年代,国内还没有专门生产厚钢板(指厚度大于3毫米的钢板)的厂,他瞄准了这一空白,但苦于暂时没有得到上级许可。怎么办?李华忠说,甩开手先干。
“不许任何人往外传,谁说我处分谁!”
他自主决定引进了国外的一套先进设备,价格很便宜。新项目耗时9个月零25天,虽然无法“见光”,却建起了3间大厂房和蔓延超过1公里的几个大矿,一开始生产就迅速盈利。等有了成绩,李华忠带着现场照片去向一位政府领导人汇报,
“负荆请罪”
,顺势还把该领导请到鞍山为厚板厂剪彩。仪式完成后,他的定心丸才算吃了下去。厚板厂成为鞍钢内部生产工艺、销售情况俱佳的企业,有一年的盈利就有20亿。
市场经济是前所未有的探索,企业家通过冒险进行试错和学习,政府也要不断学习。企业家可能犯错误,政府也可能犯错误。我们需要一种平等的、平衡的、良性的、将心比心的互动。
在这个过程中,企业要发自内心地尊重政府,但同时,政府也不要认为自己永远是对对,高高在上,仿佛握着生死予夺的大权。
我并不清楚万达这六个项目的前因后果以及应该承担的责任,但当我看到网上传播的这一条条处理措施——假定都是真的,我觉得任何做企业的人都不舒服。
如果万达错了,能不能给它一段时间,一个有弹性的空间,徐徐处理,缓缓着陆?!让所有的金融机构一刀切地“限流”,这个“不得”那个“不许”,条条路都堵死,这符合鼓励企业家投资创业的大时代的精神吗?
金融机构全都听“窗口指导”和“电话通知”,而它们绝大部分都是上市公司,都有公司治理和决策规范,这样的管制会给投资者、企业家一种什么印象和诱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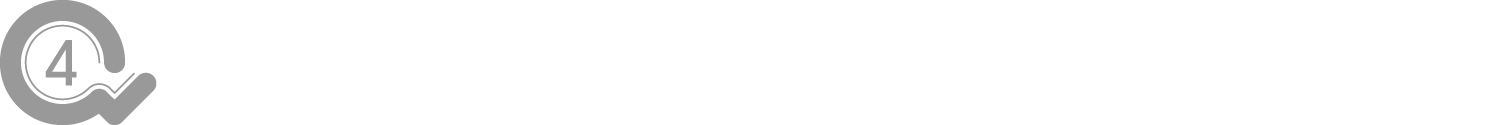
跳出王健林最近遭遇的风波,就中国经济如何长治久安的问题,我还想说几句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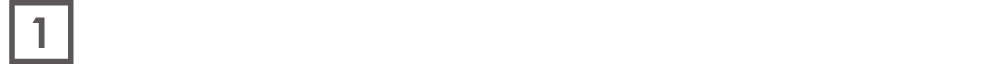
第一句,我们的政府、企业和社会要倍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中国经济局面,对引领我们走到今天的规律善加总结。
我一直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企业与市场(无形的手),一个是政府。政府的手是helping hand,是帮助的手,无论从硬件(基础设施)、软件(法律和政策)、促进人力资本发展等等方面,这只手的帮助的因素都是主导性的。是两个“经济人”共同造就了中国的奇迹,哪一种力量都离不开。所以,
政府要善待企业,善待企业家,而民企无论有多“牛”,各地政府无论对你多么趋之若鹜,都不要以为我就是靠企业家才能在赚钱,而要有大局观,厚德载物,走正道,走诚信之道,走创新之道。
(这里不谈国企,国企领导人总体上是奋斗又听话的老黄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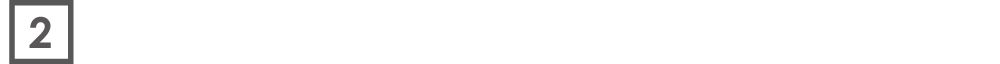
第二句,从政府的角度,要深刻体认“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意义,尊重市场,尊重企业家。
中国经济和美国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美国早期联邦政府力量非常薄弱,企业和州的力量很强,没什么国企,典型的自由经济。由于自由经济的缺陷,逐渐完善了联邦的财政体系、货币体系、国债体系、证券监管体系、反托拉斯体系等等,达到了
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平衡
。
而中国的情况是,改革开放前是高度统一的指令性经济,国企一统天下,改革开放后不断放松,放开,下放,放活,用市场机制激发起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某种意义上,
中国经济的奇迹是政府采取了明智的“让渡政策”,让出空间,让出领域,让效率更高的市场化主体去开拓,去冲去闯。
美国经济是在一片新大陆上新造的,中国是在一片有沉重包袱的大陆上“让”出了新空间,用新长出来的力量化解了旧包袱。中国有长期的权力集中体系,这个体系对中国的稳定和效率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正是这个体系能自我变革,为民间让渡出空间,中国经济才有了巨大的发展。千万不要下意识地总是回到用行政命令解决问题的老路上。对于效率更高的民企,政府更应该继续保持大的胸怀,充分利用他们去创业创新,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改善社会的福祉。即使他们有问题,也不要用强压的、否定的态度,而要采取
“问题归问题,发展归发展”
的建设性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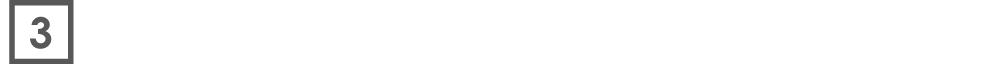
第三句,从社会的角度,要采取建设性的、冷静、客观的态度对待企业的问题。
由于传统增长模式遗留的诸多问题,中国经济、金融、商业都存在着不少弊端,最近以来此起彼伏的企业风波和问题,加剧了人们的紧张感。我向来主张以
“不虚美,不隐恶”
的态度对待企业家的问题,我也一直在写对中国企业家和富豪的争鸣与批评的文章,但是我反对那种“墙倒众人推”、恨不得再踩几脚、恨不得那些受挫、落难、失败的企业早点完蛋的情绪,我反对随便指责他们的人格,我反对没有依据的猜测
。谁都不容易,我们并不共有一个身躯,但可能共有一样的生命历程和各种磨难。特别是在中国法治化建设还不完善的这个时期,某种情绪、某些妄测可能会影响到行政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