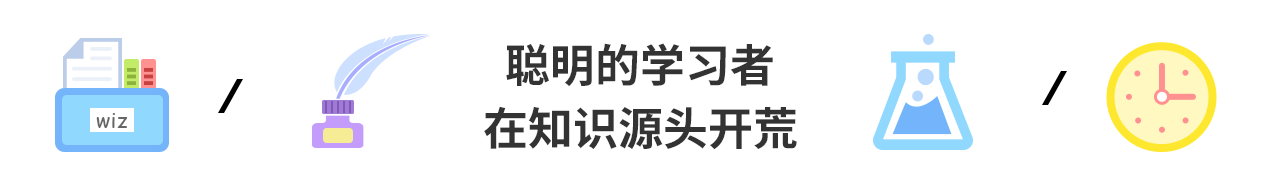
— Note170519003 —
十三维按:一个礼堂,可以是敬拜上帝的场所,可以是黑暗交易的场所,也可以是凶杀血染的现场,当然它还可以是一场梦,一场连自己不知真假可疑的梦。但是,我的知觉与感观,却又着实在在某个时间的经历中浸染穿梭,一个个故事的碎片,在眼前如胶片般被娓娓铺来——这就文章的文气与笔力,它不在一处,但你读罢牧天同学这篇文字,就会发现它已在你胸中成形——以下全文约 7400 字,阅读时间约 10 分钟。

五十岁,躺在床上,梦中总浮现多伦蒙尼礼堂。
礼堂位于郊区,现戏称为圣彼得堡滴血小教堂。弧形穹顶有扇天窗,金丝楠木架构而起,环绕以青铜镀金的多彩浮雕和精致细碎的复杂花纹,仿若一座祭坛,辉煌夺目。想当初,仪式、舞台剧,座无虚席。我最早接触礼堂是做志愿保洁员,每天重复着忏悔,打扫,看着它门庭若市。虽则半年,安常处顺。后来,它滴血了。我目睹这场悲剧,即便在事态发酵中就昏倒在地。如今,月夜下,有猩红贴着天窗蠕动,厚厚一层,如雾中云海,只闻海声,不见其景。于是,辉煌不再,灰尘和杂草相得益彰,乐此不疲地争妍斗艳。每当我回想起悲剧那天,都能感受到痛苦,撕心裂肺般刺穿我肮脏、虚弱、求善的灵魂,在半黑半白间渴望瞥见上帝殷切召唤。让我梳理一下情绪,慢慢说起。
那天午后,斯诺特行政长官在一场新药发布会上致辞,就放在多伦蒙尼礼堂。我本想介绍一下他春风得意的华贵容貌,又觉得没多大必要。这场发布会规格之高实属难见。不久前,在大选中落败的伊万卡同样在场(只能当没权的副长官)。这两人过节颇深,在斯诺特还是政界新星时,伊万卡就公开表示「我们的政界新星是一名肺痨」。这句话流传已久,也仅仅是流言而已。这里我知道真相,后面会提到。同样,警察局长诺尔也在现场,负责一部分安保工作。
我坐在发布会第二排边席,耷拉个脑袋。前排是政客名流,正在鼓掌,答谢长官精彩的致辞。虚伪地像自然选择学说,合理而看不出破绽。当然有几个家伙,如可怜的副长官,象征性摆摆手而已。右边是位白人,虎背熊腰,是黑帮「自由天使」的头目。他曾独闯龙潭,救出心腹,为此吃了五颗枪子,伤了一只眼睛,却活了下来。之后,他抛弃姓名,自称「独眼」。鼎盛时,坐拥千百小弟,地盘势力如杂草丛生,是众多「不良分子」名副其实的老大哥。据说他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你知道那心腹最终怎样了?被独眼砍断四肢做成人棍,吊起来暴晒,就因为私吞些许利润而没上报。他还极其狡猾,故意腾出三两街区,供其余黑帮争斗。这里错综复杂,驻扎十来个黑帮。而且每隔几月,甚至几天就有新帮派宣布「有效占领」,活脱脱地像一部生了十多个孩子的家族编年史。
那时,我是其中一员,小帮派「遗落水域」的头儿,手下不过十来人,专管赌博业。别人称我「懦弱的老大」,因为我曾拱手相让自己的地盘。说出来怕你笑话,其实我不仅怯懦,还是傀儡,汉克医生的木偶。说到他,我觉得忘了明说两点:汉克是我伯父,这是汉克的新药发布会。明眼人都知道,「遗落水域」真正主人是我伯父,正是现处舞台上(礼堂正前方是拾级而上的舞台)说「感谢斯诺特长官亲临现场」的汉克。他与上层人物关系甚密。我暗中得知,原因在于治好斯诺特的肺痨,救活独眼的命。伯父医术虽然不错,糊弄人的伎俩更强,还不为人知,享有美誉。同时,他贪财,为此我甘为马前卒。有次,他盘下一个黄金街区(其实是斯诺特吩咐独眼让出这块地盘),让我这个侄子帮忙打理,利润基本都进他的口袋。可惜有个外来人不懂事,抢走地盘。据说被人剖了肚,掏出五脏六腑,塞进石头后又缝合好,沉到郊区梅茵湖底了。伯父叫人做的,或是我太丢脸让他恼怒,或是觉得没必要,事后才心不在焉地提起过。
伯父开始在台上介绍新研制的药剂。我看着他慈祥而温柔的脸庞,想起私底下满是刻薄、贪财、唯利是图、不知廉耻、阿谀奉承,不由一阵气闷,但更多的只是失落。怯懦和傀儡像个影子,始终跟随着,甩不掉吹不走;又如心底明晃晃的刀子,日日夜夜翻搅着,终身难忘。有次半夜,振聋发聩的敲门和枪击声将我吵醒。我从情妇肚子上跳起,恐惧支配了我肮脏的行为,哆哆嗦嗦地赤身躲进床底。被揪出来后,毫无遮掩地站在枪口下,灵光一现,果断用地盘、钱和这个情妇才换来这条命。
「女士们,先生们,我将再次重申,这药主要是治疗疟疾,经过临床分析有极高成效,疗效也快。现场有提问者敬请发言。」会场中,汉克语调拔高,像一把黑暗中骤然亮起的火把,驱散之前一系列医学术语引起的煎熬。
「汉克医生您好,我是一名记者。据我所知,好几位病人服用这副药后并没有好转,最终失去生命,是因为副作用较强吗?」后排有人站起来。
「先生您好,每一位病人我都会进行跟踪观察和治疗。不幸之处,总有些人病情恶化后才找到我,恕我尽力后无能为力。阿门。」汉克虔诚地画了一个十字架。底下众人依葫芦画瓢,「阿门」在礼堂上空盘旋,掠过柱子,直抵天窗。
看着伯父,年过四旬,背头,西装革履,巧妙地扭转一个接一个问题,我愈感难堪。摸了摸袋中雪茄,佝偻着背,沿过道悄然走出后方十尺高门,像一条独行而饥饿的野狗,去了外侧拐角处打起火来。瞥见远处警察和独眼的小弟各占一旁,心中嗤笑着,这次安保工作居然是黑白两道协同组建,当真滑天下之大稽。
我在吞云吐雾间,凝眸眼前——走廊精美的浮雕,天使在高歌,恶魔继续沉沦,乳白色的四方合八角柱子,格子窗花后隐约的人群——这些富含艺术和魅力让我不由鞠上一躬。觉得自己不过是礼堂外一捧骷髅草,或是黑白地砖缝隙间的无名尘埃。我何必要冒风险证明自己多么伟大。我能退就退,能让就让,保住自己脆弱的形骸还在世间游荡,苟活于世总胜过去撒旦那报到。只要跟对人,包括斯诺特长官、伊万卡副长官、伯父,他们都能决定我渺小而可悲的命运。接着我抬起头,看着礼堂后院。那边空无一人,地势下坠,有条蜿蜒小径,两侧茂林深篁,尽头便是梅茵湖,风光无限好。真想现在就去一趟湖边,欣赏风景。接着,我不由给自己扇一巴掌,苦笑着面对现实。又想到为什么要将自己的命运拱手交给他人打理?尤其是汉克,一副虚伪嘴脸,不过是运气好救到贵人,只是个案而已。今天这药有什么成分。不过是老配方,多加些狗尾巴草,晒干的罂粟,可能还掺杂骨灰。他坚信自己医术无双,或许知道自己完全错了但不承认。雄辩有一手,正也是他对,反也是他对,总能找到理由。我越想越气,自己帮他挣钱,冒掉脑袋的风险,却没多少油水可拿。难道天生就要做这下流肮脏,上不了台面的傀儡吗?我靠近高大精制的窗户,想把自己嵌进格子窗花里,这样就永存于这儿,还没这么多跌宕复杂的心情。然后,撇见里面会场准备休息,斯诺特和汉克都站了起来。
我终于回到座位上,是从舞台的边门进去,寻了点水,想平复心情。
只要想起与多伦蒙尼礼堂的初次相遇,内心如深海之底的宝藏,富裕而有力量。起因是在赌场,我拿着刀架在一名出老千的散客手上,不知为何手起刀落,砍下一只手来。第二天赴礼堂赎罪,出钱做了名志愿保洁员。这期间,身心合一,仿佛感受到碧空如洗上天使的侧目,倾听到万丈深渊下恶魔的呐喊。半年后不幸降临,主说我不够虔诚,惨遭驱逐(其实是钱不够续费)。那段日子造就我富丽堂皇般的内心充盈,学会把控情绪。默念「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休息的会场虽然喧嚷,我心从容安谧。
独眼进进出出,事务繁忙。然而每次坐定,伤疤狰狞地从额头穿过眼睛,蜿蜒到脸颊骨,给人一种奇怪的安宁。纹丝不动时,仿佛礼堂内众多雕像中不可或缺的一员。那个时间段,整个会场切割成四块,最前方左侧,舞台边,有数十位权贵优雅站立着,一面奉承着诺尔,一面等候长官大人归来——休息时出门了。又一次说到诺尔,我觉得有必要说一下他。他是名门之后,为人不参与党派之争,善于抓机会,爱惜名誉,待工作如情人。前排右侧留有副长官和几位心腹,他正朝我这边侧望,我赶紧点头示好。左后方是一群不良分子,黑帮成员,说话粗俗而嘈杂。右后方剩下一波人,包括媒体、商家,人员复杂。余下少数人或散坐着,或在外聊天、排泄,可能更有阿谀奉承者紧跟长官商量龌蹉事。我知道接下来的议程是拍卖,拍卖此药的销货商。这些商家大多是看在长官、独眼的面子。最终,竞拍价由这三人分摊,如「遗落水域」的利润一样——汉克每次分完钱都会记在郊区别墅保险柜的账本上,碰巧我知道。
之后,正戏出场。
时间太巧妙,时而白驹过隙,时而逝水流年。大概已沧海桑田,反反复复,长官和伯父还未进来,众人略显躁动。边门跑进一位督察,贴着诺尔说了几句,然后一同离开。随后,礼堂像是开了真空泵,声音渐稀,说话变成体力活,可以说举嘴维艰。之后,骤然听到门外有人细语:「斯诺特长官死了。」当真是顶恶毒的咒语,空气似乎已消失殆尽。闻者置于真空,面色由红润转而蜡黄,泛白,冻结在原地。唯独冷汗是活物,从人们头顶淌下来,对着天窗折射的光芒,泛起粒粒珍珠,逞娇呈美又为鬼为蜮。咒语开始蔓延,从边门扩至全场。几秒以后,珍珠叠叠绽放,映射着各人内心独白,惊愕、窃喜、粗俗,众相百态。大概过了三年五载,待首枚珍珠落地,接二连三,像大珠小珠落玉盘,惊醒世人,慌忙关上真空泵。「怎么可能?」「在哪?」「哦,上帝。」「死了?」
独眼猛地站起来,如猛虎被惊醒,腰间用衣服盖住而鼓起的枪支也蠢蠢欲动。他鄙夷地滑过我因不知所措而显得怯弱的脸,向后方小弟打个手势。
这时,会场内有人喊道:「汉克医生呢?他不是跟长官一起出去的吗?」话音刚落,汉克摇摇晃晃地走进门来,衣服湿透,发型凌乱,软绵绵地靠在头皮上,显得极为无力。诺尔紧跟其后。
独眼用一只眼剐了下哄闹的人群,巡视领土般。礼堂明显降温后,冷静发问:「汉克,长官怎么了?」
「长……长官说肚子难受,去卫生间的隔间……好久之后,血,血流出来。我们,之前一直在外面……喊他也没应,就踢开隔间……他满脸的血。有子弹穿过后脑勺……然后,发现隔间的后壁有个可移动的活孔……」
一片哗然。诺尔狠毒地瞥了眼独眼,许是憎恨他喧宾夺主,向前走了几步,问一旁督察:「墙后面是什么地方?」得到是锁着的杂物库后,转向独眼斥道:「你们的人怎么检查的?」
独眼哼哼两声,没有理睬,看着那个督察,道:「其余隔间也有孔吗?」
督察看着诺尔回答:「没孔。不过其余隔间都被反锁,也没人会进去。」
独眼看向同样站起来的伊万卡,道:「长官死了,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副长官您了?」
伊万卡阴沉着脸,自嘲道:「我?连你都能质问我这个无权的副长官,我还能做什么?这次安保都是你和诺尔安排的,而且只有你俩带枪进来……不过,汉克医生,在你的发布会上出现这种状况,而且还是你带着长官一同出去……肚子为什么难受呢?」
诺尔早就吩咐手下检查水杯等细节。听到这话,自己也跳上舞台,带上白手套,仔细检查边边角角。
众人用眼珠瞪着汉克,无声地谴责就如一条近在咫尺的竹叶青,看得见却躲不了。汉克徒然回过神,吼道:「关我什么事啊?我不过去趟卫生间而已。查,随你们查。」
几方对峙中,气氛终被督察打破:「杯中水需要检验,送去了。泡水壶在汉克医生那,而且在他座位旁发现一些粉末。卫生间纸篓里查到泻药的包装,用湿纸巾裹着。」
底下众人屏息凝视,如孩子逛动物园看人蛇表演,聚焦舞台中心刺激的表演。汉克霎时声调抬高:「这怎么能证明是我……怎么跟我有关呢,我从没做过啊。」
斜阳下,多伦蒙尼礼堂像镀上一层金,在金属重压下气氛略显凝固。伊万卡一拍脑袋,说:「哦,我记起来了。独眼,上次你不是跟我说知道汉克保险柜的账本吗?跟这有关吗?」
汉克颜色倏得煞白,似乎踌躇了几个念头,猝然指着独眼高喊:「是他,肯定是他,刚才他首先说话。肯定是每次分钱你都最少,还有那地盘……」
独眼板着脸,吼道:「白痴。闭嘴。什么账本?」
伊万卡轻声吹了下口哨,吹到一半却戛然而止,估计是因为气氛不对。他从公文包中拿出一蓝色小本,道:「就是这个,谁送我来着?让我随便翻一页读读看。」
「1945年5月2日,上月实际利润142.35万。告诉斯诺特是70万,给他35万;告诉独眼是20万,给他8万……啧啧啧,好心机。还有……你要自己看吗?」
清脆的拔栓声传出,独眼掏出M1935手枪,指向汉克:「你一直在骗我?」
汉克哆哆嗦嗦,嘴里不停嚷嚷:「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诺尔依旧带着白手套,拔出M10警用转轮手枪,指向独眼:「无法无天了啊!刚才有人汇报说子弹是9×19mm巴拉贝鲁姆枪弹,还有消音器。就是这把吧。独眼你胆子大啊!来人,抓起来。」
独眼手下和警察争执着,推推搡搡。会场内,有些人想先走一步,生怕惹上是非,却被拦住。我浑浑噩噩地缩在一旁,懦夫上身,目视这一切。最初我觉得真是伯父下手了,因为他早就咕咕嘀嘀,钱都让斯诺特和独眼赚走了。转念一想进场前都要搜身,他带不进枪。但若真是他下的泻药,难道是跟独眼联手设局?我感觉自己逼近真相。现在他们相互推脱,是想置身事外吗?
独眼的满脸横肉、伤疤和皮肤,皆盯着汉克,恶狠狠地道:「我敬你是名医生,还救过我命,让你多赚点。没想到你贪心不足啊。嫌钱少就直说,我多给你点就是了。但我最痛恨别人骗我……」
伯父眼神躲躲闪闪,左右环顾。猛然间趴在地上,爬到诺尔身后,抱着他腿。先是大喊,之后语调愈来愈轻:「局长,他真会杀我的,救我……我,我以后把钱也分给你。」
诺尔用手拎起汉克,甩到一旁,一眼未看。我看诺尔的眼神明显在媒体那群人中停顿数秒,眼皮跳了跳,转向独眼,道:「你敢当着我的面杀人?独眼,你越来越放肆了。」
独眼冷笑:「你们敢诬陷我,敢杀我吗?」说话时,一直盯着汉克。我仿佛看到伯父在瑟瑟发抖。总之,独眼忍住了,收枪转身,招呼手下走。他昂首阔步,把后背笔挺地朝向诺尔的手枪,似乎在嘲讽他和警察局。
我那时肯定丑态百出,头脑一片浆糊。看到独眼大发神威,觉得是时候投靠新主子了,连忙跟上,跟着起哄:「对啊,我们黑帮要团结,一起走。」吹嘘声渐起,还看到有位独眼的手下朝警察吐痰。一旁媒体交头接耳,虽细声细语,却显得叽叽喳喳。
之后,「砰」一声,独眼硕大的脑袋就在我面前裂开,滚烫的脑浆,还有一些红色犯恶心的东西溅到脸上。腿一软,我随独眼坠下身来,觉得冰凉的地板在燃烧。整个礼堂,只听到诺尔冷静而坚定的发声,赶在这群黑帮暴怒前:「嫌疑犯独眼,合谋汉克故意杀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于逃跑路上被击杀。」补了一枪汉克,硬声道:「汉克故意杀人,行贿,生产、销售假药。于逃跑路上被击杀。」
我发誓。从小到大,信奉过上帝,投靠过撒旦,参与黑帮,砍过人,但如此心狠手辣者少之又少。礼堂沉寂,只余枪声阵阵回响,黑帮中传出「不干掉他我们都得死」的声音。独眼的手下暴怒起来,个别黑帮乘势而起。一个个赤手空拳,或挥舞任何可拿之物,往舞台冲去,与阻拦的警察扭打着。舞台中央,诺尔喊道:「联系军队,扫荡黑帮。」
随着斗争升级,众人没有阶级,不分好坏,不辨男女。皆为泼红油而炸锅的蚂蚁,有些逮人就砍,有些到处乱跑。礼堂内,人身上,一切可以手持之物,包括耳环、胸针,都用来防护和攻击,猩红洒染礼堂。黑帮人员和警察不断涌进来,争当蚂蚁一员。
「该死的,马上派人……」我们英勇的战士,光明守卫者,警察局长诺尔话音未落,脖子穿过一颗子弹,生命戛然而止。然而,这乱糟糟的现场,众人自顾不暇,谁能分辨出子弹的源头?我本想着寻机会,跑出这个锅炉,正好看到这幕,又立马蹲倒在地,爬向角落。说直白点,是在众人血中蠕动。
后来,我在爬行中,被人推搡和践踏,终是晕过去了。
「先生,你真的晕过去了?」记者笑着发问,充满狡黠。
我躺在床上,僵硬地移动脖子,面朝她脸。这脸模模糊糊,可能是背着光,让人看不清。我压抑住太阳穴的跳动,尽力维持镇定:「真的。」
「你可能不知道,警方事后在伊万卡的公文包中搜出一把M1935手枪。可他人却离奇失踪,死不见尸活不见人。又在礼堂后院湖边发现血迹。您知道他人去哪儿了吗?」
「哦,我还真没注意到他,太混乱了。再醒来的时候,就在医院了。」
「我有一系列推测,全部说出来,你帮我鉴定一下。你与伊万卡勾结,谋杀斯诺特、诺尔、独眼、汉克。当志愿保洁员是为了挖孔。会场当天埋伏在杂物库,手枪也提前藏那儿的吧。后来扔到湖中?」她盯着我的双眸,想看出些什么,「藏在黑帮中挑拨关系的是你,吐痰的也是你。你用独眼的枪杀掉诺尔后,发觉伊万卡跑向礼堂后院,因为那儿没人,可以躲藏。你知道若不干掉他,事后必被灭口,于是追上去枪杀他。湖边的血迹,应该是这样来的。他人呢,被你沉入湖底了?就用掏出内脏那一招吧。你摸回礼堂内,将这把抢塞进他公文包……你流汗了?」
我凝视她,蓦然发觉,朦胧的脸竟是伊万卡。她(或许是他)邪魅一笑,伸出双手,勒住我的脖子。这双手冰冷潮湿,仿佛来自地狱,引我走向窒息。喉咙撕裂,像被一把榔头敲打着。我挣扎着,想从地狱之门挣脱,不停晃动。喉咙已然断了半截,撕心裂肺。在我即将昏迷之际,隐隐间觉得这脸成了自己模样。
「哗啦」。我直勾勾地坐起来,甩开被子,心跳加速,喉咙难受,这一切使我回神。心有余悸地摸摸脖子,方觉这是一场梦,扁桃体应该发炎了。
门外传来窃窃私语,侧耳倾听,似乎在说我……是在复述这一切。转向一旁,同床的娼妓不见了。
该死的,我居然说梦话了。
(编辑:十三维 2017-5-23)
- The End -
↓↓↓戳原文,预约认知写作学第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