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9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post-modernism”早已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至少在十年以前,由唐小兵翻译整理的杰姆逊(Fredric Jameson)教授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录出版后,被统称为「后现代主义」的这一庞杂的西方人文哲学思潮就开始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在被大量翻译引介的同时,「后现代主义」逐渐生成为一支新的批判言路,开始活跃在今天人文研究、社会科学和文化批评等领域。
后现代思潮在中国的「本土化」倾向引起了某种兴奋,也带来了不少争议。鼓动者确信其批判功能在中国语境中的有效性,正致力于用后现代语词全面审度和清算中国80年代中以「科学、理性和真理」为主导的「新启蒙话语」。批驳者忧虑于这一思潮的「非理性、反智主义」的倾向,认为这是一条危险的歧途,有可能使我们误入遍布「解构碎片」的思想废墟,在价值虚无主义日渐流行的今天特别值得我们警觉。讥讽者则否认后现代言路与中国现状有任何真实的相关性,嘲笑当下的「后现代热」是某些知识分子对西方时髦习惯性追逐的延续,是盲目而肤浅的「拿来主义热病」的新近症候。而相当一部分学者则在这股「热潮」中保持冷静而谨慎的沉默。
实际上,对后现代思潮的这种复杂反应并非中国知识界独有。至少在美国,后现代话语在学术界和社会政治运动中所产生的分歧、紧张和困扰也相当显著。不久前,由「苏卡尔事件」所引发的激烈争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本文将对这场争论的背景及要点进行引介和评论,并由此阐发笔者对后现代问题的一些初步思考。
一 「苏卡尔事件」的背景
1996年春季,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的著名的「文化与政治分析」学术季刊《社会文本》(Social Text)推出一期题为「科学战争」的专号,其中发表了纽约大学物理学教授苏卡尔(Alan Sokal)的一篇论文,题为〈逾越边界:关于量子重力学的转化性阐释〉。文章的开篇以挑战的笔调写道:
很多自然科学家,特别是物理学家,一贯否认社会与文化批判的学科能够对他们的研究起任何作用。没有多少人承认他们世界观的根基必需依照这种批判来重建。他们宁愿固守一种信条,一种由长期的启蒙主义霸权在西方知识格局中所形成的信条,可以将之概括如下:存在一个外在的世界,其性质独立于任何个人或人类整体,而隐含于一些「外在的」物理规律之中;通过由(所谓的)「科学方法」配置的「客观」程序及严格的认识论检测,人们可以获得可靠的(虽是不完备和暂时的)关于这些规律的知识。
苏卡尔继而声称,二十世纪科学所经历的深刻观念转移,有力地挑战了这套笛卡儿─牛顿式的形而上学;科学哲学与历史的新近研究进一步质疑其可信性;而最近女性主义及后结构主义的批判已经揭开了西方主流科学实践的神秘外衣,暴露了其隐藏在「客观性」表象之下的意识形态控制。他自己的论文试图在这条路径中迈出新的一步:通过讨论量子重力学(一门据称是综合了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的物理学新分支)的最新发展表明,科学所依赖的时空、几何等根本性的概念框架已成为相对的、可疑的。这一观念革命对未来「后现代的、解放的科学」和社会政治运动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这篇论文引用了从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波尔(Niels H. D. Bohr)、海森伯格(Werner Heisenberg)到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拉康(Jacques Lacan)、德勒兹(Gilles Deleuze)、李欧塔(Jean J. Lyotard)等的219篇文献,有109个注释,以雄辩的文风「论证」:量子重力学摆脱了「绝对真理」与「客观现实」之类的传统观念束缚,是一门「后现代科学」。它应和了后现代文化理论的重要主张:独立于文化之外的所谓「客观世界」并不存在,「物理现实」正像社会现实一样,本质上也是一种「社会和语言的建构」,所谓「科学知识」绝无它所自称的「客观品格」,而是产生这种知识的文化中权力关系的产物。后现代科学的崛起有力地否定了传统科学中的权威主义和精英主义,为进步的政治事业提供了强健的理论依据,「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它将逾越边界、打破壁垒,有力地支持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的激进民主化进程」。
令人惊讶的是,苏卡尔的这篇檄文发表后不到三个星期,一家专事学术界趣闻轶事的杂志Lingua Franca注销了苏卡尔自己的一篇「坦白书」,声明那篇论文完全是他蓄意编造的荒谬之作,投寄给《社会文本》是想以恶作剧的方式进行一次「物理学家对于文化研究的实验」(Cultural Studies):测试一份在北美具有权威地位的、由著名学者杰姆逊和洛斯(Andrew Ross)等参加编辑的文化研究刊物究竟有怎样的学术标准,看看它是否会采纳一篇漏洞百出、荒诞之极但编造得貌似有
理且投编辑所好的文章。不幸的是,事实证明了他的猜测——「在人文研究的某些领域,严格的学术标准正在下跌」。
苏卡尔的声明刊出后引起一片哗然,立即激起热烈的反响和争论,形成了所谓「苏卡尔事件」。《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新闻周刊》(Newsweek)、《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和英国《泰晤士报》(Thames)等主要媒体对此竞相报导;《异议》(Dissent)、《新政治》(New Politics)及《梯坤》(Tikkun)等文化政治评论刊物也纷纷卷入讨论。而互联网上更是「群情沸腾」,各种交流小组发出上百篇各抒己见的电子通讯。苏卡尔任职的纽约大学又组织了一场公开辩论,让苏卡尔与洛斯当面交锋,将此事件推向戏剧性的高潮。「苏卡尔事件」很快波及法国。正当辩论方兴未艾之际,苏卡尔又在1997年10月推出了一本与比利时鲁汶大学的理论物理教授布里克蒙(Jean Bricmont)合作的法文版新书《知识分子的欺诈》(Impostures Intellectuelles),出版后立即登上了非小说类的畅销书排行榜,在法国知识界掀起轩然大波。《解放报》(Lib谷ration)、《世界》(Le Monde)周刊及《研究》(La Recherche)杂志组织了专题报导,包括德里达在内的一些著名学者纷纷发表观感,使「苏卡尔事件」成为欧美知识界近两年来最为令人注目的热门话题。
在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一些非常尖锐的对立。有人指责苏卡尔以欺骗的手段愚弄编辑和读者,这种「恶意的玩笑」本身已经违背了最基本的学术道德,是哗众取宠、博得虚名的负面典型,对科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对话毫无建设性的意义。也有人激赏这是一次「绝妙的实验」,认为当一知半解却以把玩晦涩的名词术语来假冒深奥成为时尚,当所有「外来的」批评质疑都被拒斥为「观念陈旧」或「政治保守」的傲慢气息日益膨胀,恶作剧式的嘲弄是有效的、也许是唯一有效的批评策略,将某些「后现代理论家」披着「皇帝新装」的真相大白于天下。而更多的评论者力图与情绪性和戏剧化的纷争保持距离,希望通过冷静的讨论澄清迷惑和误解,在不同学科、不同学派之间建立有效的对话。
二 一个物理学家对于文化研究的实验
毫无疑问,苏卡尔的恶作剧是有趣的、精彩的,也的确触及到一些重要的问题。但其意义究竟何在却有待进一步清理。如果像苏卡尔自称的那样,这是「一个物理学家对于文化研究的实验」,我们首先要追问的是:这个「实验」到底想证明甚么?它结果又证明了甚么?
苏卡尔在他的声明与应答中多次引用了劳丹(Larry Lauden)写在《科学与相对主义》(Science and Relativism)序言中的一段话:「从相信事实与证据的至关重要,到认定一切都可归结于主观的利益与看法,这样一个观念转换是我们时代反智主义最为突出和有害的表现。」苏卡尔感到,美国人文学界的某些领域正是在这种时髦的「观念转换」中失去了应有的严格学术标准,特别是一些人文学者在他们的「科学学」研究论著中,对自然科学新成果的误解和滥用达到了令他吃惊的地步,多年以来他一直为此而困扰。但作为一个物理学家,他无法确定他对某些人文研究的迷惑不解是由于自己身处外行的理解局限,还是因为那些「文本」自身的混乱离奇。
于是,他决定做一个实验,蓄意编造一篇荒谬的「论文」,没有确凿的证据、没有明晰的逻辑论证,而只是将一些被任意歪曲了的科学发现成果与某些后现代大师的陈述用含糊不清的语言相互圆说,进而武断地否认外在世界的存在,否认以科学方法获取客观知识的可能,并推论这样一种「后现代式的否定性批判」将对进步的左翼政治产生积极的影响,以此迎合编辑的知识取向和意识形态偏好。
那么,《社会文本》对这篇奇文的采纳究竟证明了甚么?它不过证明了一次编辑失误。这是《社会文本》的编辑对此事件的解释,或者说是他们希望公众能够接受的解释。失误的原因是由于他们对物理学知识的局限造成了「暂时的盲目」,使他们在处理一篇出自物理学家之手却挑战传统科学观的论文时失去了准确的判断,他们对其探索性和独特性的欣赏淡化了他们作为编辑应有的审慎。
这个解释在最表层的意义上可以成立。从「实验」设计的逻辑上看,它的结果所能直接证明的只是一个特定的刊物在处理一篇特定的来稿时发生了编辑失误。然而,任何事件的理解都不应离开它的「语境」作孤立的阐释。考虑到《社会文本》在文化研究方面的权威地位,考虑到苏卡尔所仿效的后现代观点和文风在近几年的文化研究领域中有相当的代表性,我们有理由进一步探讨这一「失误」背后更深刻的知识学和社会学原因。
作为人文研究的教授,《社会文本》的编辑对物理学的浅陋学识并无可非议。但他们不经任何物理学家的审阅咨询就发表这样一篇充斥了专业术语的论文,就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疏忽。在苏卡尔看来,这是后现代理论在知识问题上的傲慢走向了它的逻辑极致的例证。这种傲慢是盲目的,它并没有坚实的知识论根基,而是由被他称为「草率思想」(sloppy thinking)的荒谬性所致。苏卡尔将其要害诊断如下:否定客观现实的存在,或者,承认其存在但否定其在知识实践中的相关性,一切都只是社会、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建构,事实和证据并不能用来鉴别知识的可靠性,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都不存在客观真理,任何陈述的有效性都是相对的(相对于陈述者个人、或其所属的族群和文化)。这是后现代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和认知相对主义所依赖的「草率思想」。
苏卡尔进一步推论,以这种荒谬的草率思想作为知识论前提的文化研究,当然不可能确立严格的学术评判标准:
如果一切都是话语和文本,那么对于真实世界的知识就是多余的,物理学也只是文化研究的另一个分支;如果一切言辞都是语言游戏,那么内在的逻辑自洽也就无关紧要。于是,不可理解成为美德,引述、隐喻和双关语代替了证据和逻辑。
苏卡尔认为,在这种日渐流行的后现代文风中,他所编造的论文还只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例子」。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依照苏卡尔的阐释,这个事件不是偶然的,而是后现代文化研究在荒谬的知识论引导下,严格学术标准必然丧失的例证。然而,这个阐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立仍然需要更为细致的讨论。
首先,具有「哲学敏感性」的学者对于苏卡尔的「诊断书」立即会提出一系列质疑。例如,本体论上的实在论问题、认识论上的可知论和客观论问题及语言学中的话语建构问题,彼此虽然存在某种关联,但不具有直接的逻辑一致关系。一个反实在论者可以同时是一个可知论甚至是认识客观论者;一个实在论者也可以同时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但是无论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持哪一种立场,都并不必然导致严谨学术性的丧失。从笛卡儿后的「认识论转向」到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后的「语言学转向」,这些问题在哲学史上有过许多细致而重要的工作,达成了一些结论,也存在一些分歧,但不能说都是没有事实和证据的荒谬奇谈。令人惊讶的是,在「苏卡尔事件」的整个讨论中,几乎没有人对此进行充分的「哲学清理」。也许是问题过于复杂,无法在三言两语的辩论中澄清。结果是苏卡尔以简洁而幽默的方式宣告了科学实在论的不战而胜。
其次,苏卡尔的「诊断书」具有过于简单化和概括化的倾向。例如,他没有区分在庞杂的后现代言说中,到底是谁明确宣称了「客观世界并不存在」,谁只是暗含了这个设定,谁仅仅是「悬置」或回避了这一问题,而谁又是接受了客观世界的存在而仍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有论者指出,苏卡尔有效地攻击了后现代理论中最为极端、也最为荒谬的版本,但他进而用以偏盖全的方式否定整个具有后现代倾向的文化研究是有失公允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申辩中,《社会文本》编辑洛斯和罗宾丝(Bruce Robbins)以及该刊的创始人之一阿若诺威兹(Stanley Aronowitz)都一再重申,他们不是激进的「解构主义者」,也没有人会荒谬到拒绝承认客观世界的存在(既然如此,又如何解释他们接受了一篇「荒谬」地否定客观世界存在的论文?他们对此避而不谈)。他们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现实是否存在,而在于我们有关现实的知识是否「明晰」(transparent)?理性、逻辑和真理的含义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是否确切无疑?
在此,我们可以确认论辩双方的一致和分歧所在。《社会文本》一方承认客观现实的存在;苏卡尔也同意事实本身不是「自明」的,必须服从于「阐释」。分歧在于,苏卡尔及其支持者坚持认为适当的科学方法可以在发现事实的过程中「过滤」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但对于《社会文本》一方来说,这种观念几乎是「宗教式的信条」,因为任何方法都是在文化和语言中建构的,其中隐含了深刻的权力关系,无法保证其可靠的客观性。
正是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双方的争论陷入了「焦点错位」状态:苏卡尔的证据主要限于论证自然科学内部的知识成长机制的有效性;而另一方则重于强调科学研究的外部环境问题(谁花钱支持甚么样的研究项目等等)以及科学成果在社会应用中的政治文化控制因素。在相当大程度上,争论演变为科学认识论对知识社会学的一场「混战」,从中很难确切推断苏卡尔的「实验」结果究竟证明了甚么。
三 对「越界」的回应:检讨后现代主义视野中的科学图景
然而,笔者认为这场混战仍然具有丰富的意义,也并非不可解读。对论辩的细致考察会使我们发现,「焦点错位」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学科之间理解与表达的障碍(所谓「两种文化」的交流困难),而是双方论点所针对的「问题域」不同所致。苏卡尔一方集中攻击的对象是激进的理论——那种将后现代言路延伸到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越界批判」,以及对各种知识的有效性不加区分、全面否定的「总体批判」;而另一方所能够辩护的(或者说最后「退守」的),是温和的后现代言路——那种对知识生产环境及应用效应的社会文化批判。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对比双方「批评策略的有效领域」来解读这场混战的意义,从中得出一些重要的启示。
首先,后现代理论对自然科学内部知识有效性的否定是一个严重的「越界」失误。
长期以来,某些人文学者为自然科学共同体虚构了一幅漫画式的荒诞图景。在他们眼里,科学家们是一群哲学上的低能儿,在认识论问题上仅仅停留在「机械反映论」的水平,对事实观察和理论建构中的人性和社会因素毫无反思意识;或者,将科学家们形容为一群幼稚而狂妄的「绝对真理病」患者,对科学知识的真理性陷于盲目的信赖。于是,「后牛顿物理学」所引发的一系列当代科学的新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方法论转换,被某些论者臆想为「导致了科学认识论的危机」,甚至科学本身的危机,以致得出「可靠的知识在自然科学中也不再可能」的结论。而这一切,完全是某些后现代主义者一厢情愿的幻觉。
在这场争论中,没有人再继续坚持这种对科学的天方夜谈式的批判。当苏卡尔在其「伪作」中所仿效的这一言路已成为笑柄,后现代主义者似乎也只有从激进的越界位置上后撤,由对科学内部知识有效性的否定转向对其外部功能的检讨。虽然阿若诺威兹还提到了科学研究中「观察的理论依赖」及「研究范式的变革」等问题,但这对于苏卡尔及其支持者并不具有任何挑战意义,因为这些问题对于科学家早已不是甚么新鲜观念,它们是科学知识成长机制的内在组成部分。至少从伽利略开始,科学家就是按照这套方法工作的。
第二,后现代理论有必要澄清其批判话语在知识论问题上的确切意义。
虽然后现代理论在原则上拒绝或回避「总体批判」的方式,但仍有不少后现代主义者明确地或暗示性地以「全称否定句式」来讨论知识论问题,但其涵义却经常暧昧不明。例如,「没有离开权力的知识」这句被反复引用的「后现代名言」究竟意味甚么?如果说它只是意味「绝对的真理并不存在」,那么几乎没有人会为此争辩。正像人人都会同意「绝对健康的人是不存在的」这样一个医学陈述。在清晰的语言中,「没有人是绝对健康的」也绝不意味一个在草地上健步如飞的运动者和一个接到了病危通知的患者具有同等的健康状况。但正是在这样的逻辑关节点上,某些后现代主义者以模糊的语言发挥了「卓越」的跳跃才能:「所有的知识都是社会、文化和语言的建构」可以被引伸为「所有的建构都同等有效或同等无效」;「绝对真理并不存在」可以被用来暗示「一切知识的相对真伪都无法定义、无法判断」。当然,后一个陈述并非完全不能成立,但它需要证据支持,无法直接从前者逻辑地导出。
似是而非、闪烁其辞的浮夸文风在后现代言路中甚嚣尘上的事实,是论辩双方一致公认的。这种语言风格几乎成为识别「后现代文本」的第一特征。学术界有人讥讽说,「如果你不能写得朦胧晦涩,你就没有希望也没有资格成为一个后现代主义者」。苏卡尔曾坦言,他在编造那篇论文时,花了很长的时间才使语言达到了「应有」的模糊水平。他还谈到他与一些后现代论者的接触经验:「许多貌似新颖激进的观点一经清晰的语言追问,就变得不那么激进,而且很容易让人接受,但却不再是重要的了。」
那么,在知识论问题上,后现代批判的确切涵义究竟是甚么?如果只是「绝对真理并不存在」,那它没有多少新颖的思想意义,这本身也不是一个后现代陈述。如果意味着「任何知识都无所谓真伪」,那它就必须有效地响应整个自然科学界的挑战。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批判在激烈否定科学方法有效性的同时,从来不曾充分地解释为甚么自然科学可以在那么长的历史实践中保持生生不息的知识新陈代谢,为甚么科学共同体内部能够展开最为有效、最少歧义的交流对话,甚至可以超越不同文化、语言和政治背景所构成的障碍。这当然不是所有后现代理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但的确是那些主张或暗示了「无真理面前所有知识一律平等」的总体批判言路无法回避的问题。
第三,后现代理论有必要认真反省对当代科学成果的误解和滥用。
这也许是围绕「苏卡尔事件」的讨论所带来的最直接、最明确的启示。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对科学方法的大加鄙薄,毫不妨碍他们同时引用「科学证据」来支持某些后现代论点。一些人文学者以望文生义的「虚假博学」方式阐述——从「测不准原理」、相对论、哥德尔定理到「混沌理论」、「非线性时间」、突变论、灾变说等等——当代科学的前沿学说,发掘其中的「后现代意义」。这一「奇妙的景观」激起了许多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的强烈不满。伴随这场讨论而推出的两本着作《建在沙滩上的大厦:揭穿关于科学的后现代主义神话》(A House Built on Sand: Exposing Postmodernist Myths about Science)及法文版的《知识分子的欺诈》,以大量的例证分析表明后现代理论家,包括声名显赫的大师级人物德勒兹、拉康、李欧塔对当代科学的误解和滥用达到了如何惊人的地步。
德里达应法国《世界》周刊之邀对《知识分子的欺诈》一书发表观感,除了反复指责苏卡尔的恶作剧「很不严肃」之外,唯一的响应就是这个问题已经缠绕了他三十多年了,他「没有甚么新的东西可说,绝对没有」。互联网上有人评论说,一位解构大师对苏卡尔的任何论点毫无「解构」,却大谈严肃不严肃的问题,实在耐人寻味。
第四,人文及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苏卡尔明确表示,他与《社会文本》编辑在许多问题上的看法并不冲突,人文及社会科学家对自然科学所提出的很多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例如,甚么样的科学研究项目被确定为重要的,研究基金如何分配,谁在其中拥有权力和声望,科学家在制定公共政策中所承担的作用,科学知识以何种方式转化为技术,谁会从中获利等等。他甚至同意,在一定意义上,科学讨论的某些内容(如鉴别相互竞争理论的标准)是受到文化制约的,所以也应该在科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中进行分析。他所强调的是,这些研究应该具有严格的学术评判准则。虽然科学家与人文及社会科学家侧重的方面不同,研究的对象和路径也不同,自然科学方法论并不能在其它学科中被简单的移植或借用,但这些差异并不应该成为排斥理性讨论的借口。
我们从这些评论中看到了苏卡尔平和、公允的一面。但它们是泛泛而论的原则性陈述,究竟怎样的评判准则才算严格?到底如何讨论问题才是理性的?哪些对科学社会功能的后现代批判可以达到严格的、理性的标准?在这些问题上还有相当大的争论空间,其结果也未见分晓。
四 后现代批判的「主义化」倾向
应该特别强调的是,笔者认为,以上所有批评即使全部成立也不足以证明整个后现代的文化批判是一套背离了事实与证据的荒诞学说、根本经不起任何严格的学术标准评判。问题远不是那么简单。这场争论中真正受到有效攻击的后现代论点可能是这一言路中最为拙劣的部分,有些甚至违背了后现代经典论说的基本精神(例如将「局部批判」扩张为「总体批判」),可以称之为「庸俗的后现代主义」。在笔者看来,这种庸俗化倾向所伴随的不只是对科学的曲解和滥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后现代「源流思想」的背离,而其症结要害在于将后现代批判作为「主义化」的纲领来实践。
马克思曾宣称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那些在形成后现代思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思想家,除了李欧塔之外,几乎没有人承认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或「后结构主义者」。德里达从未使用过「后结构主义」这个术语,并反复强调「解构」从不是一个思想流派。福柯(Michel Foucault)曾幽默地问道:「甚么是人们说的『后现代』?我有点跟不上形势。」他又明确表示:「我不理解有甚么样的问题对于被称为后现代或后结构主义者的人们是共同的。」克莉丝蒂娃(Julia Kristeva)曾公开指责后现代主义,而拉康的学说是直接反对后结构主义的。
这些后现代思潮的「源流人物」之间有不小的差异,有些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他们各自从不同方面对启蒙以降的现代理性主义传统提出了不同性质的问题,有些是建设性的,有些是挑战性、颠覆性的,但其中没有任何一位把自己的理论视为彻底瓦解这一传统的「思想武器」,也从未声称能够全面取代理性主义在知识、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各个方面的实践。(对德里达来说,「解构」并不意味「摧毁」,它不过是一种「阐释策略」;对福柯来说,他研究的是特定社会实践中的知识—权力关系,而如何改变这种关系是重要的,但却不是他所承担的问题。)他们总是各自面对特定语境中的特定问题,谨慎地界定自己理论的有效边界,从不假扮自己可以回答边界以外的任何问题。在这些源流思想家那里,并没有一场「后现代」对「现代」的革命召唤,也没有以后现代替代现代社会的宏伟纲领。
用「后现代」的标签统称这些互不相同的思想言路是很勉强的,再加上「主义」的后缀就更加可疑。严格地说,「后现代主义」——将「后现代」这个反一体化的思潮用一体化的「主义」来总括——是一个矛盾术语(contradiction by definition),但如果实践者对此保持充分的警觉,可以避免因「方便之用」而可能造成的简单化危险。实际上,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一些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中,许多具有后现代倾向的学者完成了相当独到而出色的工作,其中不少对(揭示隐蔽的结构性不公正、反映弱势族群的利益以及社会的全面民主化等)进步的政治实践产生了积极的意义。
然而,庸俗化的倾向也开始出现并有蔓延的趋势。庸俗的后现代主义者们真的将后现代思想言路作为一种「主义」,一种革命纲领,一种无所不能、无往不胜的批判武器来实践。在他们那里,源流思想家所树立的谨慎的、细致的、高度语境化的分析风范几乎荡然无存。到处可见的是,以引述代替证据,以关键词(如「霸权」)游戏代替逻辑论证,以宣言式的声讨代替深入详实的批评。伊朴斯登(Barbara Epstein)教授在讨论中指出,美国的人文学界目前出现了一种「后现代亚文化群」,在学术体制中拥有越来越明显的权势地位。他们激烈地攻击和排斥异己的学术思想,因为启蒙时代已经终结,除了后现代之外,其它一切思想言路都是「陈旧的和保守的」,可以一网打尽。在这种风尚中,「后现代」的卷标成为「知识先进」和「政治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的天然凭证,只要站在「后现代」旗帜下,就获得了可以四面出击却免受批评的特权。这种傲慢与偏见激起了广泛的不满,这也是「苏卡尔事件」之所以会产生强烈情绪反应的一个重要原因。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后现代思潮滥觞于60年代的左翼政治运动,从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实践意义。正因为如此,庸俗化的后现代主义批判在社会政治的具体实践中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就特别值得警觉。任何一种思想的滥用都是危险的,而任何一种思想都可能被滥用。后现代批判在此并不具有天然的豁免,打起后现代的旗帜也绝不意味着当然(学术上和政治上)的进步。在学术界,以「反抗霸权」为出发点的批判言路本身正在演变为一种话语霸权,这种现象不止具有讽刺意味,更应使我们深省那种似曾相识的「始于革命家终为独裁者」的历史陷阱及其灾难性结局。在社会政治实践中,后现代批判可以用来支持正义的抵抗事业,却也完全可能在特定的条件下与极端民族主义、恐怖主义和宗教狂热结盟。一种开启了批判和反抗的思想言路,一旦被庸俗化地滥用,也有可能流变为专断与独尊的意识形态,「后现代热」就可能变成「后现代疯狂」或「后现代梦魇」。
最后,笔者想以一个存而不论的问题来结束这篇评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是否、或者要在多大程度上对这一思想在历史发展中的意识形态化负责?对列宁主义的党国(party-state)政体的实践负责?这是学术界至今仍有争议的问题。而奠定了后现代思潮的那些源流思想学说与「庸俗的后现代主义」之间究竟有甚么联系?这也许是另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西方政治史上最重要的 25 本书,都在这里了

东亚巨变500年——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与现代世界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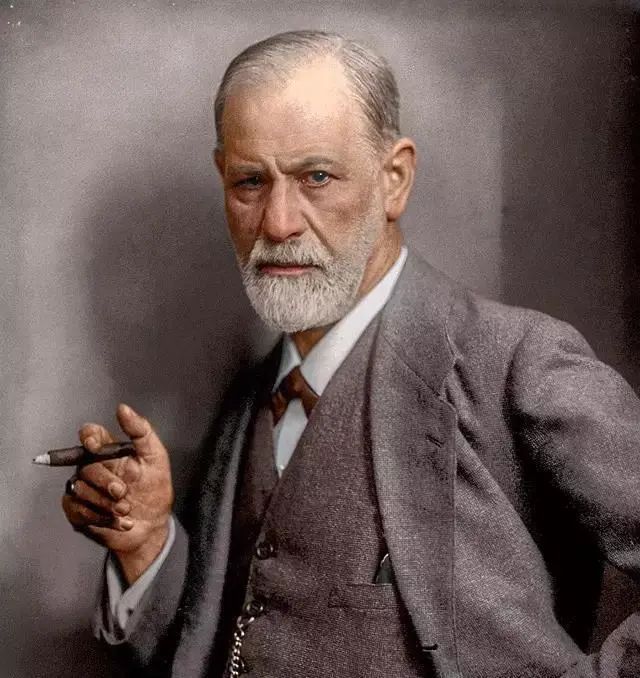
梦见坠落、掉牙、被追赶……这10种梦隐藏着你的哪些秘密?

|
北大医学部教授:如何活得长、病得晚、老得慢、死得快?
《统一与分裂》之后,葛剑雄又提供了哪种看懂中国史的方法?

回望我们的精神疆土,是什么样的智慧支撑我们一路走来?

诺奖得主揭晓背后,人类的终极问题是什么?

周濂·西方哲学思想100讲
20世纪思想的启示与毁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