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姐》剧照
一碗唆螺,奶奶做了一辈子,我也心心念念了半世。每回吃到,都似一种美好倏忽而至,让人由衷欢喜。记忆里绵延的悠香,如同这个居大不易的家庭持续迸发出的热情,生生不息。
人间有味 | 连载13
楔子
2013的这个时候,或者更晚一些,我去派出所做了一次笔录。起因是在某宝上购买了药品,那家店并没有售药资质,我被要求协助调查。
药是给奶奶买的,奶奶嚷嚷腿痛有六、七年了,总是腿不受力、又痛,爸爸想尽了办法,带着她遍访名医,得到的都是一句话:“年纪大了,骨头老化,膝盖磨损了,不可逆。”
买来钙片给她吃,老老实实吃了一段,擅自加量,被发现了,爸爸没收了她的药,定时定量给她发,“坏咧,药都不给我吃。”她生气了。
爸爸哭笑不得。
偶尔奶奶和我聊天,总是哀叹她的病痛,“你爸带我到处看,也没个结果。”她皱着眉,苦着脸,好委屈的样子,“我只要走得,还是做得事的咧。”
我找我的医生朋友们到处打问良方,偶尔结识的,也有枣没枣打一杆,“能缓解也好啊。有什么药吗?”
终于有朋友介绍说,香港的骨刺灵可能有些效果,托朋友带回一箱。奶奶吃了一段时间,有些效果,腿没那么痛了,嚷嚷要出去走走,妈妈拗不过,搀她出了门,下了电梯,单元门口站了一会,又上楼了。
“她说她脚不受力,站不稳啊。”妈妈打电话告诉我。
我忙向朋友打问,朋友苦笑着回答,“老年骨病那么好治的?那药就是麻醉成分多些,能缓解痛疼。”
从此,这种药,奶奶就长期服用,不但自己吃,还送给娘家人,娘家人送得多了,自己不够用了,又打电话让我买。老是托朋友帮忙,我也不好意思,听人说某宝上有卖,选了一家排名靠前的,买了一箱。于是,不久后,我生平第一次进了派出所协助调查。
● ● ●
给我做笔录的民警很客气,结束询问后还送我出了门。我上了车,掏出手机拔家里电话,爸爸接的,我请他让奶奶听。
“格伢啊,什么事呦。”奶奶略带沙哑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响起。
“奶奶,药别送人了,自己留着吃啊,”我略感烦闷,“为了给你买药,我都进了派出所了。”
“派出所,你冇犯事不?”奶奶听不清。
“没啊,没事啊!”我忽然泄了气,觉得自己的抱怨有些好笑。
“什么时候回来啊,奶奶给你做好吃的啊。”奶奶在电话里头笑,“吃唆螺好不好?”
“好啊,”我的心情顿时好了起来,“什么时候?”
奶奶做的唆螺,自我小时起,就是难得的美味。这道菜工序繁复,如今她越发做得少了。
奶奶做唆螺,总在入秋时。幼时去乡下小住,她会做给我吃,那时候奶奶的身体尚健旺,挑得土,做得田,整饬得一家熨贴。相较之下,爷爷常偷懒,按他的说法,他读过书、当过兵、去过朝鲜,复员回乡又做过民兵连长和大队保管,热心公家事是当然,家里的事自然管得少些。
奶奶姓刘,比爷爷大得三岁,十二岁上嫁到张家做童养媳,一做做了一世。
如今奶奶老了,乡间有了名声,大家都说她是个福婆婆,每次亲戚接她回乡小住,总有人奉承,“刘婆婆真有福,”人们啧啧称赞,“祖坟葬得高,一屋搞得好,享了崽福享孙福。”
她眯着眼笑,双手直摆,笑完又撇嘴,“哪里,操劳命,饱饭子孙靠娘养,我现在还搞饭给他们吃呢。”她抬眼望天,一副没我不行的样子。
奶奶做唆螺,会选大颗的田螺,养在清水里,每日换水,过得一段时日,才做。这道菜,爷爷也很爱吃,可她不专做给爷爷吃,小时候,得是我跟着父母回乡时,爷爷才伴搭着享享口福。
“你们不来,我就吃不到。”那时,爷爷尚未戒酒,唆螺下酒是他的最爱。手指拈着田螺吸出螺肉,细细咀嚼,间或咪一口谷酒,一脸惬意。可说归说,丝毫不见他有埋怨的脸色。
● ● ●
三十年前,乡间尚未实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我们要回乡,全凭乡党捎信。
“刘婆婆诶,友初(父亲)哥交待了,下个月初四,会带婆娘、崽回来咧。”
话捎到了,奶奶就留了心。每日经过田间地头脚步放缓,偶尔也去塘边、溪边转转,看到大个的田螺就拾回家,放在水缸里养着。
水缸从此日日换水,原本用得两三日的大水缸,奶奶要爷爷每日挑满。爷爷也不争辩,闷头出力。
到得那一日,爸爸带着一家子,提着大包小包,坐上了东去的小火车。
回乡,在我是挺开心的一件事,乡间的一切都显得新奇,破旧的老祠堂,屋后的大枫树,屋前一条清澈的小溪,再往前下老坝(乡间以坝称河)终年汨汨的流水。还有乡间的虫鸣鸟叫,夜晚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一切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神秘,就像心里模糊的一处地方,门窗紧锁,我依稀去过,却丢了钥匙。
秋日,幼小的我随着父母走过下老坝的大桥,走近小溪前,远远地看见一个身影蹲在对岸岸边洗衣,身边尽是深绿的野草,渐凉的秋风从西边吹来,溪水叮叮咚咚,捣衣锤捶在湿衣上发出沉闷的响声。一条泥土小径在岸边斜插到坎上,远处,老屋后的大枫树叶子青转红,如一把大伞,遮出半天朱翠。我认出了那个身影,怯生生地喊了一声“奶奶”,走近些,又喊了一声,她抬头来看,丢了手上的活计,站起了身子抻直了腰打望。
“孙咧!”奶奶大声应着,一脚踏进水里,扑腾扑腾地涉溪而过,爬上坎,大步地跑到近前,一把将我抱起。
“想奶奶不?”她笑得眉眼弯弯,用脸摩挲着我的脸,“就等你回,给你做好吃呢。”
做唆螺是个大工程,奶奶会用上小半天的时间来给田螺剪尾。彼时,捡回的田螺有小半桶了,从水缸里捞出,提到堂屋门口,用细毛刷反复刷干净,再持一把大剪慢慢剪,螺尾扔在坪里,放养的鸡飞奔过来啄食,很快在奶奶身边围了一圈。我蹲在她身边看,看那些无法反抗的大田螺们在剪刀的咔擦声中被剪去尾巴,她剪几个,侧头看一看我,麦色的脸上漾着慈爱的笑,怕手脏,小心地用手背碰碰我的头,“做田螺给我孙吃啊,喜欢吧。”
我不作声,她笑嘻嘻地回转头去,自说自画,“最好吃哒。”
螺尾要剪好久,吃饱了的鸡咕咕地轻叫,迈着蹒跚的步子走开去。奶奶提起桶,进了屋。
奶奶用大针逐一挑出螺肉,摘去螺盖,扔进海碗里,用清水反复洗。螺壳复扔进水盆里,洗荡几次,沥干备用。
作料是最紧要的,屋前、屋后野蛮生长的紫苏,菜土里的韭菜、薄荷摘扯几把,洗净剁碎混合螺肉,浇上香油、谷酒、酱油、盐拌匀,略腌一腌,再逐一回填到洗净的螺壳里,填好了,海碗盛起,洒上一撮辣椒粉。
灶下已经烧旺了火,灶里的水开了,饭甑(乡间煮饭用的木桶)搁上去,海碗放进饭甑里,盖上盖子,和米饭一起蒸。
不一会,悠悠的香气就飘了出来了。饭熟了,田螺也就做好了。
一碗热气腾腾的田螺端上桌,暗青的螺壳,撑一肚碧绿的作料,嫩白的螺肉就藏在螺壳的深处,一口吸出,满口浓香,那味道里混合着紫苏的甘甜、薄荷的清香、韭菜的浓郁和田螺本身的鲜,连汁带肉在口中细细咀嚼时,是味蕾的狂欢,心里顿时过节一般的欢快。
“这个不用钱的,田里、塘里乱长的东西,你爸小时候最爱吃咧。”奶奶说,“唆咯,用劲唆。”
我对着螺口使劲吸,总也吸不出来。
“唆不出来就转过来,”奶奶我做示范,“屁股上吸一下,再唆咯。”
我试了试,还是不行。奶奶叹了口气,寻来一根针,洗净了,让我挑螺肉出来吃。
“挑着吃就没意思了。”爷爷说。
“人细气不足,以后就唆得出啦。”奶奶笑眯眯的。
爷爷在一边唆得吱吱响,小酒喝着,熨贴得眼眯起,偶有唆不出的,在桌上墩一墩,再不出来,就跟我借针用,“何必压得这么紧呢?我都唆不出。”他低声碎碎念着。
“你莫吃啊。”奶奶眼一瞪,腔调提高,嗔怒着,“本来就不是做给你吃的。”
爷爷不作声,挑出螺肉塞嘴里,伸手去拿下一颗。
螺肉鲜香,越嚼越出味,我渐渐吃出味来,满头的汗,不肯停。奶奶停了筷,伸手给我抹汗,看着我,“好吃不?”她问。
我嘴里嚼着,无暇回答,“最好吃哒吧。”她自问自答,笑眯眯地看着我,眉眼弯弯,麦色的脸上透着满足。
正是入秋时,乍寒还暖,屋外坪中青草渐枯,屋旁的柿子树挂满了果,尚未经霜,青渐转黄,远处是金黄的稻田,风吹稻浪,滚滚向天际。
九十年代末,我家搬了新家,爸爸反复恳请,爷爷奶奶终于进了城,与我们同住。
初住进楼房,爷爷总抱怨,“当街汽车吵,走又冇处走。”他说,好似诸多不便。
“怕不是吧,你是嫌没人同你下棋吧。”奶奶怼他,“出门就是路,还怕没处走呦?”
爷爷讷讷不言。
进了城,奶奶包揽了大部分家务,城里没有田地让她操持,她便将更多的时间放在厨房,除了日常饭菜,又置办了大大小小许多个坛子,伏鸡、伏鱼、伏鸭、腌菜、剁椒、霉豆腐都自己做,还想在楼顶公用阳台架起架子熏腊肉,被爸爸制止了,饶是如此,家中的菜品一下丰富了许多。
可是最好吃的唆螺,要奶奶做,还是得等到入秋后,“三月田螺满腹子,吃不得。”奶奶说,“入秋螺肉肥,才好吃呀。”
彼时,农贸市场已有田螺卖了,到了时节,奶奶就着妈妈去买,清水里养几日,做给我吃。
某次奶奶问价钱,妈妈据实说了。
“这么贵?”奶奶啧着舌,“乡里死贱的东西,城里就金贵,我还年轻得十岁,回去捡田螺来卖啊。”
妈妈笑着,不接话。奶奶又自己圆场,“也是咯,紫苏什么的都要买,土里种下随便长的东西,城里生活成本高咧。”
“好咧,有唆螺吃。”爷爷凑上来。
“你吃不得!”二人齐说。
“田螺寒性重,你的胃受不了的。”妈妈解释说。
爷爷之前做过大手术,切除了半个胃,一边肾,戒了酒,清淡饮食将养着,不能由着性子吃喝了。
城里没有饭甑,烧火用煤气,奶奶学会了用高压锅,做唆螺时间短了,味道却仍是一样。
唆螺放进高压锅,十几分钟就出锅上桌了,一家人大快朵颐,爷爷扒着饭,就着少油无辣的清淡菜肴,偶尔望一望我们,无奈地偏过头去。我递一个给他,他倒拒绝了。
“你吃、你吃。”爷爷筷子轻扬,讪笑着。
闲暇时间,奶奶也喜欢出门,到处走。她不与爷爷同路,各走各的。爷爷好急走,目不斜视,奶奶好慢走,东张西望,看到卖转糖的、打人参米的,都要停下来围观。她还喜欢捡破烂,初时什么都捡,破纸头、细铁丝、小钉子、玻璃瓶,出门时带个布袋,回家时满满一袋子,提得额头冒汗,脸泛红光,她却像捡到宝,一样样从袋里掏出给我们看,一面啧嘴,“城里人真浪费,什么都扔。”
妈妈也随她,倒是爸爸说过几次,“邻居笑话我咧,说我不给你钱用,要你捡破烂,你凭良心说,我每个月都给你零月钱的。”
“是咧是咧,你对我好咧。”奶奶不好意思地说。
“那你莫捡了好不?”爸爸说。
“好咧,好咧。”奶奶没口子答应。
可她仍是捡,专捡矿泉水瓶,踩扁了,袋子装起偷偷带回家,做地下工作一般。她请妈妈给她配了一片楼下杂物房的钥匙,捡了瓶子藏在那里,集不少了就拿去卖。“能卖钱呢。”她喜滋滋的。
后来,我也上班了,也能时不时塞些零用钱给她,她喜笑颜开,又假意拒绝,从不伸手接,总要等我塞到她口袋里去。我陪她聊天,她会仰头看我,静静地听着,橘皮一样的脸上满是笑容,偶尔抬手碰碰我的脸,“奶奶不认字,累一世寻钱不到,我也想给你们留点钱呢。”她眯着眼,有些不好意思,“你们给我的,我都存着,以后还是留给你们。”
● ● ●
那时,大姨(妈妈的妹妹)从醴陵调回了浏阳,一家人都回来了。大姨带着表妹来家玩,奶奶做了一道唆螺。
田螺早上买的,奶奶将它们养在桶里,倒一勺盐,滴几滴清油,催着田螺吐尽泥沙。
一道唆螺当晚就上了桌,不喜吃辣的小表妹吃得鼻尖冒汗,菜碗空了,碗底的汤汁,胖胖的大姨父还倒出来拌了两碗饭。
临走,大姨缠着奶奶要做法,奶奶细细说了,末了还交待,“螺肉莫炒,肉老了就不好吃啊。”大姨连连点头。
又过得几日,大姨来家,连连称赞,“您老教的硬是好,婧妹子(表妹)喜欢吃。”大姨笑着,“就是没有你做的好,硬是少了味。”
奶奶眯着眼笑,受了她的恭维。侧着头想半天,“薄荷放了没?”
“冇诶,您老没讲。”大姨说。
“怎么可能,我肯定讲了的,”奶奶笃定地说,“你没听。”
这之后的许多年里,大姨和唆螺耗上了,做了许多次唆螺,总不如奶奶。我尝过,妈妈尝过,舅舅们尝过,爸爸也尝过,吃是好吃,仍是差着一些,差在哪里,大家都说不清楚。
“她一道菜做了一世,你是少了功力。”妈妈对大姨说。
“哪里噢?肯定少教了什么的,”大姨不服,“上次就少说了薄荷。”
“真的咧,我看着做,也就是这些东西,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我做的还不如你呢。”妈妈说。
爷爷自搬到城里,到去世,再没有吃过一口唆螺。他有很强的自制力,这种自制令得他即使动过大手术,依然活到了高寿。
爷爷去世后,我们家又搬了个地方。奶奶将爷爷的一张遗相随身带着,到了新家,放在自己房间的衣柜里,时时敞着衣柜,对着爷爷碎碎念。
她开心时,和风细雨地跟爷爷说体己话,心绪不好时,就骂他。
“冇得饭吃你就跑,跑到江西砖窑上去,不管我们。”她眼泪婆娑。
“奶奶莫哭哒。”我去劝。
“那时候,他跑出去就没得音讯,总也不回咧,荒年过了都没得信回来,我以为他死了,后来上家屋里老表说人在江西。”奶奶喑哑着声音,委屈得脸皱起,告状一般,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我说着,“家里没劳力,你爸爸八岁就到石灰坳担柴,人没得扁担高,几步一歇,邻居说我呢,讲我对崽不好。我有什么办法呦,我要做田,还要帮人沤竹子,做草纸。”这件事情爸爸跟我讲过,奶奶年轻时创业,与人合伙做草纸卖,后来被割了资本主义尾巴。
“每回村上有人做喜事办酒,我都叫你爸爸去吃席,我不去。”奶奶放低声调,眼神迷离,忆着往事,“半大崽子饭篓子,吃席都吃不饱。有一回,你表叔公家办酒,他人好,看我家困难,把礼钱退回来了。你爸爸路上看到赶场卖油糍粑粑的,全买了吃了。回家来倒是不说谎,还带了两个给我。我听了急啊,哪里吃得下,钱做得大用的。”
奶奶恨恨说,“气得我拿绳子、踩凳子要缠颈(上吊)呢,你爸爸跪在地上哭,才把我劝下来。后来想,细伢子肚子饥想吃,哪里晓得那么多咯,我的脾气也不好。”她又叹了口气,“那一回他就懂事了,十几岁出去找事做。”
“我就不晓得你爷爷,我一世不懂他,”奶奶眼神空洞迷离,泪水又溢出来,缓缓地,一字一顿地说着,“年头不好你跑,如今日子好过了,你走什么呦。”
爷爷去世后,奶奶很长时间没有做过唆螺,我央她做,她总是摆手,说唆螺太费工,老了,做不动了。
我仍是好这一口,回浏阳,常有饭局,点菜时总问,“有唆螺吗?”
多数店子都是有的,可是菜上了桌,吃得两个就罢了筷,终不是奶奶做的那个味。
我常跟奶奶说,“你不想做了没关系啊,我请个厨师跟你学好不,以后开店卖,就叫刘婆婆唆螺,肯定卖得好的。”
奶奶总是摆手,笑眯眯的,“就是那样做的啊,又没有什么巧。你们只是习惯了我的口味,市面上这么多,我的不见得好呢。”
可就连爸爸也说,他吃遍了浏阳的唆螺,包括大名鼎鼎的官渡(浏阳一个乡)唆螺。“比起你奶奶做的,总还是差了一灶火(差着口味的意思)。”
● ● ●
八十岁以后,奶奶的老年病逐渐增多了,除了腿痛,还常常呼吸不畅。给她买了家用吸氧机,用过之后,她连说好用,从此时常呆在自己房间里,戴着鼻管,一吸吸好久。
“也不能吸太久呢。”我们劝她,她应承得好,用起来又忘了时间,总要人提醒。爸爸说她上瘾了,“可不能由着她来。”他忧心忡忡的。
某一次,我回到家,去她的房间看她。推开门,看见奶奶在角落里坐着,老年发胖,身形雍肿,像一只呆坐的熊。吸氧机就放在身旁的小桌上,一根鼻管从机器里接出,挂在脸上,她低着头,花白的头发耷拉着,像是睡着了。爸爸给她买的收音机摆在床边,正播着黄梅戏,悠扬的女声唱腔在室内流转,“也曾赴过琼林宴,也曾打马御街前,人人夸我潘安貌,原来纱帽罩婵娟……”
我唤了声奶奶,她没有听见。
我走了过去,轻轻抚上她的肩,她一愣怔,仿佛从久远的沉思中醒转,慢慢地回头,望向我,浑浊的眼中泛起一丝喜色,“格伢呀,你回哒啊。”
每一次,我带着妻儿回家,奶奶纵使腿脚不便,也要亲自下厨,做饭给我们吃,虽是一些简单的饭菜,却都是从前的味道,能让人多吃下一碗饭去。
可奶奶终是做不动了,平时,做饭多是爸爸的活,奶奶在一旁打打杂,妈妈生过大病的人,想帮点忙,奶奶、爸爸都不准。
爸爸已经退休了,本想过过安逸的老年生活,请个保姆做家务,保姆换了许多个,都不合奶奶的意,奶奶会很嫌弃地说这说那,挑剔得多了,人就给气走了。
“啧啧,一点气都受不得。”奶奶总是感叹。
“都怕了您老咧。”爸爸苦笑着说她,“你是三伏天的蛤蟆,不咬人,嘈人。”
年纪越大,奶奶反而越觉得自己能做事,厨房本是她的地盘,如今爸爸占了,她总想声明主权。爸爸做饭时,她常扶着墙溜过去,蹒跚的身子一步步挪,摘菜、洗菜、淘米,爸爸烦了,说她:“不要你帮忙咧,你去看电视,等饭吃咯。”她也不恼,笑嘻嘻地,不走,靠墙站着,指指点点,碎碎念。“莫嫌我咯,我做得事呢,肉起锅咯,莫炒老了。”
可是奶奶依旧不做唆螺,即使那次在派出所外的电话里,答应了我。待我回去,她又忘了。“你说要做给我吃的。”我言词凿凿。
“冇诶,我没说诶,”她摆着手,“也不是吃唆螺的时候呦。”
直到去年夏天,一家人聚在一起,去农家乐玩了一天,晚间回家,奶奶突然提议,“我给你们做唆螺吧。”
“不是入秋才吃吗?”我问她,心里倒是暗喜,奶奶终于又起了做唆螺的念头。
“是呦。”她讪讪地说,又满脸堆笑地逗曾孙子(我的孩子),“过一阵给你做唆螺,好不好啊?”
奶奶不会说普通话,拿客家话当普通话说,孩子望着她莫名所以,瞪大眼睛傻傻地笑。
“奶奶你就说浏阳话,他听得懂。”我在一旁插话。
奶奶默了默,用浏阳话又说一遍。
“唆螺是什么呀?”儿子四岁了,没吃过唆螺,见都未曾见过。
入秋时,携妻儿回家,进门就望见奶奶在厨房忙碌着,爸爸跟着打下手,一大堆洗净的螺壳在身旁的案板上堆着,螺肉拌好了,正一只只装壳。奶奶兑现诺言,终于又做唆螺了。
田螺放进高压锅,上汽后转小火,一会儿,香气就出来了。
儿子闻见,问太太,“好香啊,是什么呀?”
“唆螺,你没有吃过的。”太太摸着他的头。
到得中午,一大碗唆螺上了桌,众人围坐吃开了。“难得啦,吃刘婆婆搞的唆螺。”爸爸开心地夹上一粒。
儿子不会唆,太太用牙签给他挑出来,作料拨到一边,光吃螺肉,儿子小嘴抿着,细细嚼着,一会儿,鼻尖冒起细细的汗珠。
妈妈吃不得,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吃。
我拈起一颗,送到嘴边,用力一嘬,吸到嘴里,慢慢地品味。仍是熟悉的味道,紫苏的甘甜、薄荷的清香、韭菜的浓郁和田螺本身的鲜味相混合,记忆中的香甜,又重回到唇齿间。
“好啊。”我竖着大拇指,不住口地夸赞。
“最好吃哒吧,”奶奶眯着眼自夸,“下次回来又做给你吃啊。”
“只要我还做得动。”奶奶又补了一句,敲了敲腿,神色有些黯然。
“做得动,你是福婆婆咧。”我忙说,“你活得一百岁!”
“不要我们插手呢,田螺早就买回来了,每日换水、挑死螺,都是她自己搞,”妈妈在一旁说,“养了半个月,等你们回。今天一大早就在厨下忙开了。”
“刘婆婆诶,你这碗唆螺吃到嘴里不容易,要大补才好。”爸爸笑着,嘴里嚼着,又拈起一颗。
“好吃不怕繁,是吧?”奶奶也笑。
桌前尽是啧啧地称赞和满足的咀嚼声。奶奶却停了筷子,看着我们吃,她将耷在额前的白发朝后捋,头略扬,眉眼弯弯,橘皮般的脸上漾着满足的笑,得意洋洋的。
一碗唆螺,奶奶做了一辈子,我也心心念念了半世。每回吃到,都似一种美好倏忽而至,让人由衷欢喜。记忆里绵延的悠香,如同这个居大不易的家庭持续迸发出的热情,生生不息。
或许,对于我们来说,这一道家常唆螺的美味,不单只靠作料的丰富和炮制的精心、独到,还有家传的滴滴浸润,时光的层层雕琢,回忆的帧帧渲染。而这一切背后,是奶奶因爱而生的甘愿,不屈从命运的勇敢,和操持一生的耐心。
编辑:侯思铭
“人间有味”系列长期征稿。欢迎大家写下你与某种食物相关的故事,在文末留言,或投稿至 [email protected],一经刊用,将提供千字800的稿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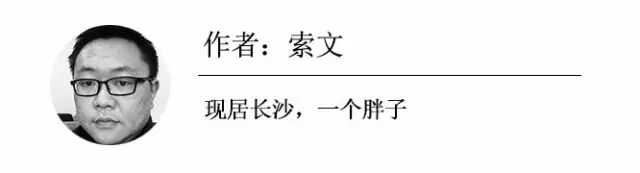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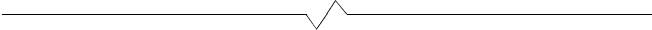
本文系网易新闻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并享有独家版权。如需转载请在后台回复【转载】。
投稿给“人间-非虚构”写作平台,可致信:[email protected],稿件一经刊用,将根据文章质量,提供千字500元-1000元的稿酬。
其它合作、建议、故事线索,欢迎于微信后台(或邮件)联系我们。
人间,只为真的好故事。
相关文章(点击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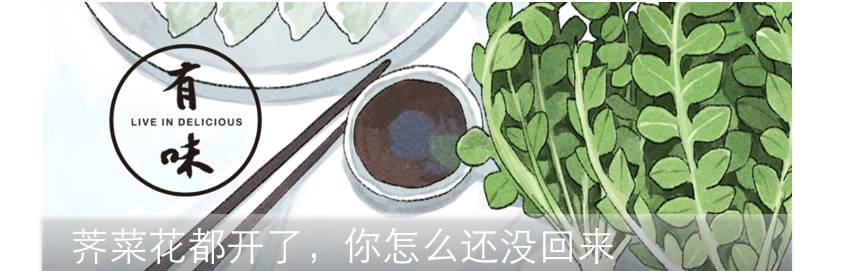

网易新闻 非虚构工作室
只为真的好故事
活 | 在 | 尘 | 世 | 看 | 见 | 人 | 间

长按二维码关注我们
点击以下「关键词」,查看往期内容:
祭毒 | 坡井 | 南航 | 津爆 | 工厂 | 体制 | 年薪十二万
抢尸 | 形婚 | 鬼妻 | 传销 | 诺奖 | 子宫 | 飞不起来了
荷塘 | 声音 | 血潮 | 失联 | 非洲 | 何黛 | 饥饿1960
毕节 | 微商 | 告别 | 弟弟 | 空巢老人 | 马场的暗夜
行脚僧 | 失落东北 | 狱内“暴疯语” | 毒可乐杀人事件
打工者 | 中国巨婴 | 天台上的冷风 | 中国站街女之死
老嫖客 | 十年浩劫 | 中国版肖申克 | 我怀中的安乐死
林徽因 | 北京地铁 | 北京零点后 | 卖内衣的小镇翻译

▼点击阅读原文,观看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