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要说的,是一个爱情故事,但我没法用浪漫的方式讲述它。故事中的恋人最终没有走到一起,他们之间只说过一句话,一个单词——
“ 燃 烧 弹 (Napalm)。”
时间回到1958年,纪录片导演朗兹曼(后来凭《浩劫》闻名于世的那位)受邀去朝鲜。在朝鲜,他和一个女子发生了一段很短暂的、名副其实的一夜情。60年后,朗兹曼已经年届九十了,他对此还念念不忘。
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但越探究这个故事越惊心。
*封面题图为当年同赴朝鲜的克里斯·马克摄影集《朝鲜人》封面
*昨天忘了打原创标,因此删掉重发一遍
1958年,法国左翼青年朗兹曼受邀进入朝鲜,作为代表团成员考察那里新建的社会主义工厂和政权。

年轻的朗兹曼(最左),瘦瘦高高,风度翩翩
那是朝鲜第一次敞开国门,让外人窥见自己被美朝战争摧残的肌肤。无数吨炸弹和燃烧弹差不多已经将首都平壤夷为平地。400万朝鲜平民也在战争中身亡。

朝鲜战争中被轰炸后的平壤街景
朝鲜三面沿海,拥有漫长的海岸线。白天,代表团沿着海岸线行走,完全靠双脚前往工厂。走了几天,朗兹曼感觉体力不支,提出想打点维生素调养一下。
于是,在宾馆里,他见到了爱情故事的女主角——金顺锦。她是平壤红十字医院的护士,年轻漂亮,让朗兹曼一见钟情。
朗兹曼与金顺锦语言不通,而维生素B又偏偏需要从臀部注入。想象一下:
宾馆的床榻,裸露的肉体,互生好感的二人...男女之间紧张且羞怯的吸引力,几乎是一触即发。
在疗程行将结束的当天,朗兹曼终于按捺不住自己。他热烈地亲吻了金顺锦,还与她约定在平壤市内的一座铁桥上见面。从那里,他们可以划船前往河的对岸,享受不被人打扰的二人世界。
我猜不到语言不通的他们是怎么约上的,其实就连朗兹曼自己也不确定金顺锦是否真会去桥上赴约。但那天,不知怎么的,这对恋人如愿了。
他们划着游船去了一个稍稍偏远的地方,朗兹曼又画图又比划,才知道金顺锦的家在鸭绿江旁。那里靠近中朝边境线,也在战争中经历了炮火的洗礼。
这时候,温馨甜蜜的恋爱气氛突然被金顺锦打断了,她撩起自己的朝鲜传统衬衣,露出了两只乳房。乳房下方,朗兹曼看到了一道触目惊心的疤痕。
然后金顺锦用英文说了唯一一句朗兹曼能听懂的话,“燃烧弹(napalm)。”
那时的朗兹曼爱上的更多是金顺锦的美貌。他吻她,约她,最终的目的还是想与她做爱。但是金顺锦亮出的疤痕震慑了他。一瞬间,朗兹曼才回想起来,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经历了什么,又正在经历什么......
之后,二人原路返回,在宾馆的院子里深情相拥,却被等待着的官员抓了正着。后者已经对这次违法的私会有所察觉。
于是,一场临时的审判会在这场爱情事故的始发地上演了。朗兹曼是金日成的贵宾,免于受审。所以“被告”只有金顺锦一人。
审判会进行过程中,朗兹曼曾经闯入,要为金顺锦脱罪。最终,金顺锦的行为被解读为“无心之过”,她与朗兹曼就此别过。

1958年的法国访朝代表团,除了朗兹曼还有克里斯·马克、剧作家加蒂等人,他们受到了金日成的接见(图中最右)
朗兹曼回到法国以后,收到了金顺锦寄来的明信片,配有朝鲜外交部的官方翻译文本。
她在字里行间提到了二人的铁桥幽会。结尾处,她写道,“所有热爱和平的人们,会再次相遇。”
他们都热爱和平,但他们再没相遇。
经历这场不可思议的情事时,朗兹曼32岁,已经参加过二战,和德国人打过游击,会驾驶飞机,会海洋深潜,和很多女人有过浪漫情事,其中还包括大他17岁的波伏娃。

朗兹曼(中右)与波伏娃(中左),波伏娃更知名的伴侣是萨特,但她曾与朗兹曼同居7年,并在信上自称“他的妻子”(his wife)
在1958年的平壤插曲之后,他结了三次婚,谈了多次恋爱,阅尽了世间各色美女。但当朗兹曼90岁的时候,他说自己最难忘的恋人还是护士金顺锦。
难忘到什么程度呢?他竟想要专门为这件事,拍摄一部电影。
朗兹曼是个很会讲故事的人,也拍过多部影片了,但他不喜欢虚构,从未拍摄过剧情片。

朗兹曼最知名的作品,是长达九个半小时的纪录片《浩劫》,影片由二战幸存者自己讲述对大屠杀的回忆和指证,没有采用任何战时影像,只有对讲述者和战后原址的当下记录
但是金顺锦一度动摇了他的理念。2000年,他想过用虚构的方式重述这个故事,让男女主角在另一个城市,另一座桥边激情拥吻。
这么做,至少操作起来会简单的多。毕竟,几十年中,朝鲜变得更难进入了。外国人在那里按自己的意愿拍电影,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平壤市中心的万寿台,两具铜像是所有前往朝鲜的国外人士都必须参观的景点
但是再三考虑之后,朗兹曼还是选择了纪录片。他觉得用虚构方式讲述这件事,是一种背叛。尽管这个爱情故事具有成为一部卖座剧情片的所有元素,但相比珠圆玉润的婉转叙述,残缺却忠实的陈述可能要好得多。
朗兹曼在自传《巴塔哥尼亚野兔》中,每每提到同为电影导演的史蒂芬·斯皮尔伯格,都故意带着冷漠的语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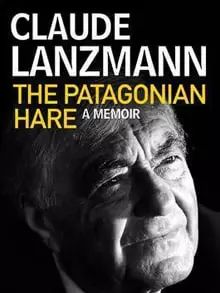
朗兹曼自传,《巴塔哥尼亚野兔》(2005)
在他看来,像《辛德勒的名单》这样的二战电影,只是记述了一个偶然事件。而这,对于六百万死在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来说并没有太大意义。
朗兹曼说他只关注最主要的事情,而在战争中,这件事确定无疑就是“死亡”,而非“幸存”。
波兰作家米沃什在谈到纳粹罪行时也说,“用每一种文学形式来表述都是可以的,唯独不能采用虚构的小说。”
朗兹曼和他的电影团队当然知道拍摄纪录片的选择意味着什么。他们在办理进入朝鲜的签证时,找的借口是要去搜集拍摄跆拳道电影的素材。
即使这样,他们也只被获准在朝鲜境内停留12天,而且整个摄制组的专业器材,都因为某些原因,被扣在了中国海关。

第一站,铜像
等到了平壤,年迈的朗兹曼马上就被朝鲜官方委派的翻译官紧紧搀扶。对方握在他手臂上的手指,像是一副镣铐,决定了接下来几天他能去那儿,能看什么,能拍什么,应该怎么拍……

被搀扶的朗兹曼,左方是一名女副官
陪同剧组的,还有一名女副官,一名女跆拳道运动员和一名女演员。朗兹曼觉得她们都很美丽,尤其是女副官的秀美,让他想起了六十年前的金顺锦。

当年(1958年)法国访朝团的成果之一,就是朝鲜/法国联合制作了这部电影叫《牡丹峰》(Moranbong)。如果你想象不出本文女主角金顺锦的样子,大约可以参考电影剧照中的这个朝鲜女子
一路上,翻译官“扶”朗兹曼瞻仰了万寿台的金日成、金正日铜像,游览了平壤战争纪念馆,当然,还有几个跆拳道馆。
在巨大的铜像前,朗兹曼看见一个新娘子为领袖献上花朵。这是在朝鲜结婚的必经的仪式。政治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变得不可分割。
而在战争纪念馆,朗兹曼也认真聆听了女副官的解说。“美国及其盟军使用了48万枚炸弹轰炸了这座只有40万人口的城市,每人可以平均分到一枚还多。”

战争纪念馆中放着朝鲜军队从美军和盟军那里缴获的武器
在朗兹曼眼中,朝鲜的一切都凝固了。
时间仿佛定格在美朝战争之后。尽管这里的人们每天进进出出,高楼也从四面八方陆续建起,但这个国家一直没有走出战争的阴影。创伤,恐惧,戒备……这些东西是不变的,它们致密地凝固在铜像中,水泥里,和人们的脸孔上。

《燃烧弹》预告片里的一个有趣的细节,朗兹曼一把推开了要搀扶他的朝鲜工作人员。你就知道他这次朝鲜之旅有多不爽
剧组一边走,一边瞒天过海地偷偷拍摄。最后得到的可用素材不够多,朗兹曼只能在影片的后半段,采用《浩劫》里用过的手法——对着镜头讲故事。
毫无疑问,故事在“燃烧弹”的高潮处结束,这也成了电影的片名。

《燃烧弹》电影海报
《燃烧弹》预告片
有件事我不得不提,那就是,导演朗兹曼一路上都在和女副官肆无忌惮地调情。我猜想,六十年前,他也是这么挑逗金顺锦的。
考虑到朗兹曼来到朝鲜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追忆过去的恋人,这样的行为,让我感觉有些别扭。但官方特地安排三位漂亮女性陪伴朗兹曼,也让我觉得异样。
我在开头就说到,这是个爱情故事,但不能被浪漫的讲述。这不仅是因为情场老手朗兹曼对他生命中每个漂亮女人都大献殷勤,也是因为金顺锦一方的蹊跷。
阴谋论者有数不清的理由怀疑金顺锦靠近朗兹曼是否另有目的——
她是不是某个地下组织的间谍,想从这个法国左翼青年身上套取信息?
她是不是朝鲜官方安插的耳目,以便监视在国外一直热衷于社会活动的朗兹曼?
她真的听不懂外语吗?如果是,那她是怎么明白约会的时间和地点的?官方又是从哪里知道了她与朗兹曼的私密情事?
此外,她在宾馆审判会上轻松脱罪,事后又给朗兹曼发明信片,这些不符合朝鲜政府一贯做法的迹象。
所有这一切,让人细思极恐。

最后,老情人当然是没找着,朗兹曼只好凭画追忆往事
朗兹曼说过,自己是一个很晚熟的人。但也许对他更恰当的评价,会是“幼稚”或者“任性”。
在自传里,他只要一提起自己过去参战的事迹,和追到的女人,言语之中都充满难以抑制的自豪感。他在《燃烧弹》中的讲述,也让很多观众听出了沙文主义的倾向。
在拍摄纪录片《浩劫》时,他更是硬逼一个理发师讲出自己的恐怖回忆。这名理发师曾经被盖世太保召入特雷布林卡集中营,为毒气室里待宰的犹太人剪头发。
在讲述这段经历时,理发师在朗兹曼施加的压力下,情绪失控,与此同时,朗兹曼关心的只是,摄影师有没有正确地捕捉到理发师的双眼。
在关于金顺锦的事情上,朗兹曼的态度也在挑战我的底线。
尽管他一次次向别人动情地讲述自己与“他的爱”(my beloved)的遭遇,整件情事也他被渲染地愈发激情神秘,但当回忆结束,他却直接表示自己根本不想找回金顺锦,即使他在2004年和2015年都回到过平壤。
“我不想看到年岁和时间留下的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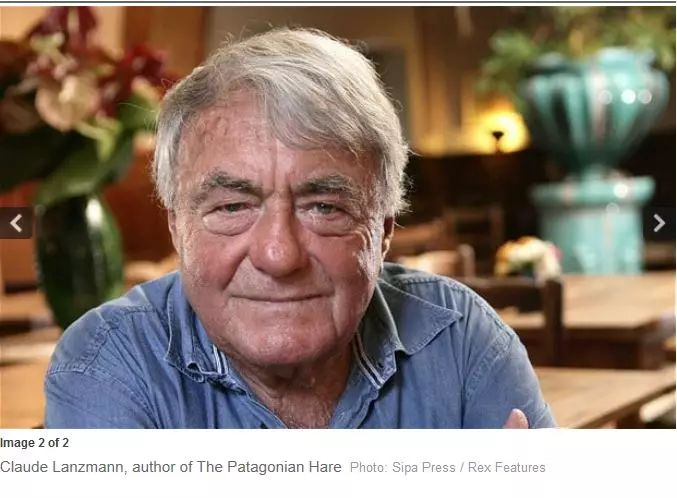
年 迈 的 朗 兹 曼
坦白说,对朗兹曼和金顺锦的故事了解的越多,我就越不想写这个故事。我怀疑他与金顺锦的爱情。这可能只是一个花花公子的风流韵事,或者是一场见不得人的政治阴谋。
但最后我发现,错的人是我。
这个爱情故事的主角并不是爱情。
即使我相信朗兹曼和金顺锦的爱恋是真诚纯洁的,但当金顺锦在船上露出乳房下的疤痕时,她心里想的绝不是用这种方式吸引对方。
对朗兹曼来说,他之所以一直忘不了金顺锦,也很可能是因为这条疤痕,以及那句唯一的交谈,“燃烧弹。”
为什么一个美丽的年轻女孩要身负这样痛苦的伤疤?
为什么她想主动向他人展示这条疤痕?
又是为什么,一对没有做错任何事的恋人只能在偏僻的河岸边偷偷拥吻?
没有答案。答案也许将永远淹没在平壤那年复一年很少变化的夜色里,无人知晓。
如今朗兹曼已过91岁,金顺锦比他还年轻,现在可能仍生活在朝鲜某地。
也许她就在平壤,也许载着朗兹曼剧组的游览车曾经开过她身旁。
她的疤痕,在她衰老皱缩的皮肤上,大概已经不再显眼了吧。而她,是否还相信热爱和平的人终会再次相见呢?
我想,她的回答,我们大概永远都听不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