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滴顺风车,揣着比我妈更无微不至的关心,鸟儿悄儿地回来了。
带来了一个希望我能鸟儿悄儿在家呆着的政策——在试运营的七个城市里,男性可以在5:00-23:00使用滴滴顺风车,女性只能在5:00-20:00的时间里使用顺风车。
政策一出,立刻有女权主义者站出来质问。

这样的质问旋即被贴上“中华田园女权主义”的标签,遭遇了另一波质问,主要观点包括——
“支棱啥啊?滴滴是那个点儿不让你坐顺风车,又没不让你出门,这难道不是为了你的安全考虑吗?”
“你觉得这样不好,那你提出个更好的方案啊”。
“滴滴已经在尽力了,不要把社会问题加到一家公司身上”。
作为一个严重的社交恐惧症患者,从有专车这个玩意儿开始,我就尽可能地使用之,因为几乎不需要跟司机师傅多讲一句话。
我从来没用过顺风车,也从来没升起过一丝体验这个产品的念头。
但这并不代表,滴滴限定八点之后女性不能再乘坐顺风车了,对我没有影响。
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某个时间之后,女生就不行了”的故事。
十几年前,我在东北老家读初中,不止一次地听老师家长念叨过一句话,“到了高中,女生会变笨,在理科上就跟不上了,男生就在你们身边蹭蹭地超过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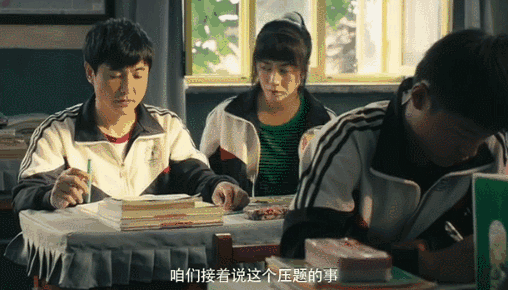
我不知道这个结论,是有多少数据支撑的,但我知道,我是怀着对这个结论的恐惧升入高中的。
高一忽然铺开的多科目和难度越阶的数理化碾压而来,在第一次月考,我物理考试考了六十多分后。
其实每一个升入高中的学生都略感不适,但在那个时刻,我认定了这就是“到了高中,女生在理科上就跟不上了”的命运转折点开始了。
看着身边那些成绩优秀或平平乃至不学无术的男生,我都有一种面对天选之子的恐惧感,感觉他们马上就要从我身边蹭蹭超过去了。
高一的每一天,我都在等待这一学年的结束,文理分科的日子快点到来。
高二第一天,走进文科班的教室,我有一种残疾人终于离开了奥运会的赛场,回归残奥会的轻松感。
许多年后,我在北京的公交车上(另一种不用说话的交通工具)听过两个初中生的对话,男生说“我这次物理又没考好”,那个扎着马尾的姑娘安慰他说“没事儿的,你们男生到了高中,理科就有优势了”。
心理暗示这种东西,是有旺盛的跨地域代际传承力的。
这是为什么,滴滴那个禁止女性在20:00之后乘坐顺风车的政策,是以保护特殊群体之名,伤害了这个群体的。
这家提供社会化服务的公司,以顺风车的产品政策,向女性传达“你不行,你不可以”,向世界传达“她们是弱者,为了保护她们,要限制她们”。

历史上有过这么贴心考虑的,还有“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其实在滴滴顺风车上发生过那些惨烈的事故后,我也会建议女性盆友们在特殊的时点要谨慎选择顺风车。
但是由提供这项服务的滴滴,明示在20:00之后,女性失去了选择顺风车的权利,事情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
前者是全面思考后的自我保护,后者是这家公司为了不给自己找麻烦,将一个群体区别对待。
上了高中,女生就变笨了;
天黑了,女性的自由就残了
。
当有人把你很弱当一个既定事实宣布出来,你妈会催你要早点儿回家,世界会簇拥着那个弱的方向加速弱下去。
当我说完这些话,相信会有人说,“u can u up,你逼逼了那么多,你倒是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啊”。
u can u up是一种奇怪的逻辑,我并不是这个曾经估值千亿美金的公司的拥有者和受益者,面对这只千亿独角兽为了狂奔下留下社会阴影,凭什么要提出完美的解决方案?
欲戴皇冠,必承其重。
一家企业,将自己产品的风险成本,外溢给另一个群体去承受,这就是作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