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在你写了好几千字之后,又全部都删掉了。也许,从一开始就不是你所满意的,那么接下来写的那些也可能成为了你发泄的东西。当然,有时候,你能从这几千字当中,找到一个吸引你的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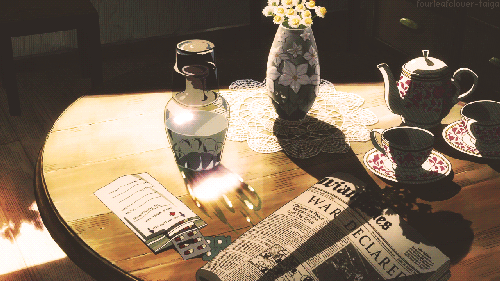
我记得有位画家在画布一角尝试描绘某个景象,却不断发现他画出来的跟脑中所想的不同,于是每次都用白色颜料涂掉,而这反复重来的过程,将会引导他发现自己想画的是什么。我的写作过程同样如此。我可能自以为了解某个特定角色是什么样的人,或一篇散文该如何铺陈,因此我依照脑中这个朦胧的草图尝试写出来。结果却发现我错了,我误解了那个角色。她身上挂着我当初为她写的广告牌,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于是我将它涂掉,再试一遍。
当我开始每月一次陪我所属教会的教友拜访养老院井带领老人们的敬拜聚会,我领悟到错误的开头有多重要。在令人心情暗沉的第一次拜访后,我自以为知道住在那里的是谁、他们有能力做什么,以及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如果当时我开始动笔,应该会信心满满地撰写他们的故事,而我会错得很离谱。
但每次还是会去,我也不明白究竟为什么。可能我潜意识地希望这样做说不定哪天就能加入青年团。然而,每当我走进敬老院,闻到那些老人散发的气味,看见他们坐着的轮椅有如弃置路旁的车辆般停在走道上,我便开始期祈求上帝别让我老了以后跟他们一样。但上帝可不是一个快餐厨师,能让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况且那些老人也曾有过青春活力,我敢说他们也祈求过上帝别让他们年老时变成现在这样。
乍看之下,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似乎相像得出奇,就像残奥会的许多参赛者都有近似一家人的外表。接着你开始注意到有些人穿着小羊皮护腿或盖着毛毯,有些人修过指甲,有些人的牙齿还很很全,有些人身上有疮,有的人没有,有些人看得出来年轻时应该很漂亮,有些人则否,有些人似乎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有些人还记得主祷文里的词句,有些人正在打瞌睡,还有一些人尝试跟着唱简单的赞美诗并随着节奏打拍子。但即使他们打着拍子,也打得各自不同。有些人的拍子打得软弱无力,几乎没有声音。
有名妇人打得极为投入,仿佛在为波尔卡舞曲伴奏。有位老爷爷只拍一下,仿佛在打苍蝇。我最喜欢的是一位跟我同样名叫安 (Anne)的妇人,第一次见到她时,我认定她只是一个头脑不清、身上有股尿味和痱子粉味的枯槁妇人,思绪空洞,心如死水。然而她其实并非如我当初所想的那样。至今我依然不了解她是什么样的人,但我知道她不是哪种人。
她从不记得我的名字,当我每个月再跟她重复一遍,她便会做出拍额头的动作,然后我们俩都笑了。我怀疑她其实是在跟我闹着玩。每当我们唱到“阿门”,坐在椅子上的她总会将双手,放在膝上,手掌合成杯状,仿佛里面有只小鸟。她会随着每个节拍将手掌稍微分开一点点,仿佛想跟着打拍子,却又不想让掌心里的鸟儿飞出来。
如果我在最初的几次拜访后撰写她和其他老人的故事,他们的气味和困惑的神情会充斥在我的描述中。我会写下我们之间怪怪异的对话——某个妇人游说我们一起去上学,另一个妇人则问我——山姆是不是一条狗——我会试图捕捉内心感受到的荒凉衰败。然而我只是继续前往拜访,并努力找出他们如此凄凉活着的意义。最后中世纪僧侶劳伦斯教士 (Brother Lawrence) 所描述的一个景象帮了我。
他将众人看成冬天里的树,能付出、贡献的东西很少, 而且叶子落光了,失去色泽和光彩,也停止生长,但不知为何,上帝依然赐予无条件的爱。我的牧师朋友玛格丽特(Margaret)参与赡养工作,她跟我分享了这个小故事,并希望我将老人看成冬天里的树,即便就传统观点来说,,他们似乎已无能力为社会做出任何贡献,但还是应该得到无条件的爱。
当你描写你的故事角色,我们会想知道他们树叶的模样、色泽以及成长的种种经历。但我们也想了解,当他们旧有的表面剥除后,显露出来的是什么样的内在。所以若你想更了解你笔下的角色,就必须跟他们处得够久,才能看出他们其实不是什么样的人。
你或许会试着要他们去做某件事,只因为这样对情节走向而言比较简便,或者你可能想把他们归类,好让自己保有掌握控制权的幻象。但他们的触角终将饶幸地从你把他们塞进去的框框内溜出来,最终你还是得承认他们的本质并非你原来认定的那样。
最能直接教导我们这点的,是那些正步向生命终点的人。通常定义他们的那些特征都调零、衰退了——例如头发、身材、技能,以及聪明才智。结果你会发现外表的色装并非那个人一直以来的本色。当外表的包装消失,另一种美便会显露出来。
例如我的朋友潘美,她在过世的十天前外出购物散心,发现自己竟无法在支票上好好签下自己的名字,于是她转头对我说:“如果你连签个支票都办不到,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只能耸耸肩肩,摇摇头。但潘美的内在本质其实和她的双手能做什么无关。她是什么样的人跟她的肢体功能一点关系也没有。
在她过世周年,我去她以前接受治疗的放射线医疗中心的纪念公园,发现有人种了一棵紫衫纪念她。那可紫衫比我还高,毛茸茸的,像是爱德华.科恩(Edward Koren) 插画中的角色。看起来仿佛会突然向前拥抱我。紫杉附近长了高高的花丛——可能是某种罂粟花,但几乎所有花瓣都掉光了, 只剩下许多缠着往上长的花径。接着我发现花茎上其实结了果,等到春天,里面的种子会成长,并再度绽放花朵。
这正是现实人生的写照。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养老院里,甚至临死前的床上,都是如此,而这也是好的写作有时会引领我们留意到的。只要你从忙碌中抽离,便能看到存在于外表下的本质,并产生令人惊喜的联系。
本文节选自《一只鸟接着一只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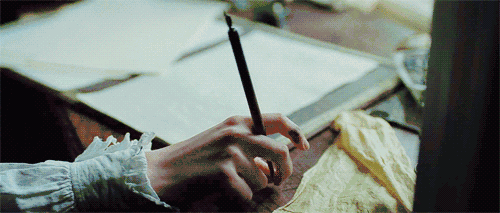
◤推荐阅读◥

 相关
阅读
相关
阅读
本期编辑 | 温不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