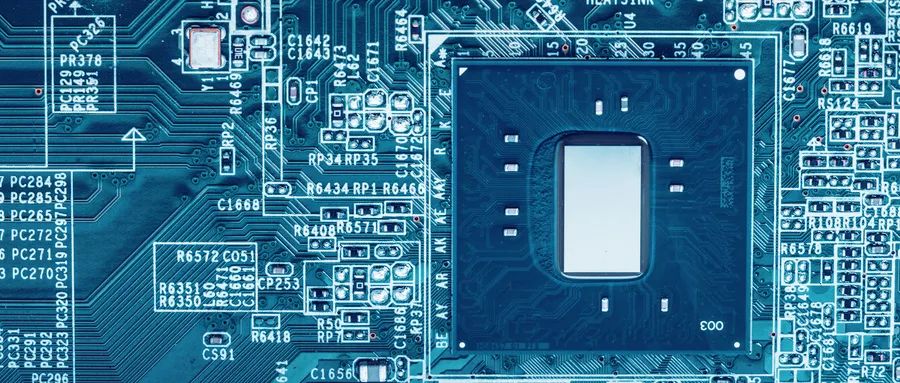喜马拉雅 音频专辑
《光远看经济》
周三、周六持续更新,
相约喜马拉雅,关注《光远看经济》
听我说人话,说真话,
告诉你经济学教科书上
学不到的经济真相;
♬
欢迎
上
喜马拉雅
,关注
《光远看经济》
免费收听全文
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再次与世界其他国家隔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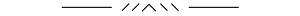
☞
文 |
刘遵义
摘要:
双循环分别指
“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
。本报告回顾了自1960年以来中国双循环的演变。双循环的相对规模及其时间变化是通过商品和服务国际贸易总量与国内总需求的比率来衡量的。
报告指出,在当今,完全的封闭和自给自足很可能导致中国实际生活水平的显著下降。报告分析了双循环的可持续性所面临的障碍,得出的结论是,
预计中国将能够成功推进双循环的可持续发展
。
引言:
2020年8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强调
“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
借此机会,笔者试探讨“双循环”的概念。双循环分别是“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循环是指供应和需求的相互满足。从1950年到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基本上只有“单一循环”,即“国内循环”。在20世纪50年代与前苏联和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易货贸易也十分有限。这一部分是由于朝鲜战争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贸易禁运,一部分是由于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与前苏联之间产生争端。

改革初期的双循环
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重新开始了第二种循环,即“国际循环”。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双循环”的恢复。但是,
改革开放初期的主要重点仍然是国内循环。
此外,也有意分离了两个循环。
例如,外商直接投资人在中国经营的“加工和组装”制造业务必须进口其所有设备和其他投入,有时还需要自己发电,以免在国内层面产生任何投入上的需求;同时,出口其所有产出,以免在国内层面增加任何供应。这种分离使中央经济计划能够像以前一样继续发挥作用。

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双循环是完全相互独立的,彼此互无联系。
在一个循环中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不能用于供应另一循环,反之亦然。“两者永远不会相遇。”唯一的共同联系是“加工与装配”业务所雇用的劳动力以及经济特区地方政府提供的土地。
但是,由于中国劳动力供大于求,外国直接投资者雇用劳动力不会对国内劳动力市场或工资率产生影响。当时,土地也处于过剩状态,而外商直接投资承租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将土地用于其他任何目的,因此也不会影响国内经济。这些安排的目的是使国内经济完全不受任何可能的国际动荡的影响。
改革开放初期的双循环可以描述为是两个不相交的圈子,一个代表国内循环,另一个代表国际循环,彼此之间几乎没有任何重叠。主导的循环仍然是国内循环。

双循环的演变
图1显示了1960年至2019年中国商品和服务进出口额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显然,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国际贸易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仅有一年超过10%,在1960年至1978年间平均占比仅7.1%。
图1: 中国商品和服务的进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1978年至1994年,人民币汇率经历了一系列调整,最终使人民币成为经常账户可兑换货币,并于1994年1月1日起大幅贬值(参见图2)。
结果是,出口开始增长,外商直接投资(FDI)开始流入中国(参见图3),使中国成为出口的生产基地,利用其低成本(特别是以美元计算)的劳动力优势
。
图2: 人民币名义汇率(元/美元,1978年至今)
1993年,外国对华直接投资在中国国内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达到峰值,15%,但此后一直下降,到2019年降至仅3%。
这反映了在国内投资总额中,来自国内的投资有所增加
(参见图4,国内投资总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随时间的增长)。
在图4中,笔者列出了国内最终总需求的各个组成部分:居民消费(C),国内投资总额(I)和政府经常性支出(G)。如图4所示,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52年的65.6%下降至2019年的38.8%,降幅明显,这部分地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低,也部分地反映了中国政府多年来保持低人力成本政策。
中国是世界范围内居民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最低的国家之一(美国相应的份额为68%)。
相比之下,国内投资总额的占比几乎翻了一番,从1952年的不到22%增至2019年的43.1%(2011年达到顶峰时超过47%)。政府支出的比重比较稳定,从1952年的13.5%逐渐增加到2019年的16.6%,在2000年达到顶峰的16.9%。
这意味着在中国,国内投资总额仍然是总需求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衡量双循环相对规模的一个有用指标是国际交易(商品和服务的出口(X)与进口(M)之和)与国内交易(居民消费(C),国内投资(I)和政府经常性支出(G)之和)的比率。
如图5所示,
在1980年之前,国际循环相比国内循环仅是很小一部分。
在1980年至1993年间,该比率从10%增长到25.7%。1994年,人民币经历了大幅贬值并成为经常账户可兑换货币,该比重从25.7%跃升至35.7%。
此后一直保持在该水平,直到2000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当人民币再次开始升值时,在2006年达到68%以上的峰值。随后,在2008年至2009年间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现在已经回落到36.7%,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水平相当。
这个比率大概是国际化的一个可维持的水平。多年以来,中国国内需求的重要性也日益提高。中国经济不再只是作为世界工厂,也已成为世界市场。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几年,有可能是由于人民币汇率被高估,国际循环的相对重要性被低估。而由于缺乏可靠的外汇支付来源,被高估的汇率也会抑制出口,从而间接抑制进口
。

是否有可能完全封闭,完全自给自足?
尽管原则上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完全封闭和完全自给自足,就像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大部分时间里所做的那样,如今的朝鲜似乎仍是如此。
但是从经济的角度看,这种做法是绝对不可取的。
两个贸易伙伴国家之间的自愿国际贸易始终是双赢的,因为双方的选择范围都扩大了,两国的福利必然是增加而不是减少,除非两国碰巧在每个部门和行业都具有相同的比较优势。
因此,非自愿性地减少国际贸易始终是双输的。

中国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其贸易伙伴国家也是。
然而,尽管经济全球化为所有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它也在每个国家中塑造了赢家和输家。自由市场只会奖励赢家,而不会补偿输家。
经济全球化实际上在每个国家中都产生了足够的收益,因此,从原则上讲,每个人都可以变得更好。但是,赔偿本国“输家”的责任落到了每个政府上。问题在于,大多数国家没有对输家作充分补偿,而中国则确保所有人都能受益。
如今,除非让实际生活水平大大降低,中国才有可能实现完全自给自足。
在过去的四十年中,中国产品的质量有了很大提高,部分原因是与进口产品竞争并且“边做边学”。然而,中国目前仍存在无法生产的产品,如大型飞机和先进的半导体。
中国目前也存在国内产能无法完全满足国内需求量的商品,如食品、石油、铜和铁矿石。这些产品和商品目前大量是进口。如果中国完全放弃国际循环,则意味着将没有这些产品和商品,或只有有限数量。
因此,
回到单一国内循环并不符合中国自身利益。
中国确实需要自力更生,但自力更生不应等同于自给自足。中国不能通过退出世界而获胜。与美国的经济脱钩并不意味着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脱钩。
为了维持国际循环,中国需要世界其他主要贸易国家的支持,特别是欧元区国家。

阻碍可持续性的因素
可能有许多原因导致可持续发展的失败。如,长期大量的贸易顺差或逆差不可能持续下去。
图6显示了1960年至2019年中国国际贸易收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从1960年到1994年,中国的商品和服务贸易差额平均为零。
中国的贸易顺差在2007年达到顶峰,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8%,但此后在2019年又回落至不到2%。展望未来,中国的目标是实现接近于零的贸易平衡。
如果关键的供应链被打断,可持续性也将受损,如果有关键的产品或投入由于某种原因而无法进口。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找到替代的进口来源或国内替代品。
任何大国都不应过分依赖国际需求或供应,国际需求或供应可能由于许多不同的原因而中断甚至停止,尤其是不能依赖单一国家。
即使其供应商是在最友善的盟国中,仅依靠单一供应商仍有很高风险。
可能破坏关键供应链的不可预见事件不仅包括贸易战和大流行,还包括地震、洪水、飓风、龙卷风和海啸等自然灾害,破产和大火等人为灾害,以及诸如三英里岛、切尔诺贝利和福岛等核事故,更不用提禁运、战争和其他地缘政治冲突与纠纷。
虽然第二来源会增加交易成本,但就像购买保险一样,既有净成本,也有益处。
拥有备用的第二来源可以防止垄断,降低垄断势力和由此产生的垄断租金,形成更稳定、更具竞争力的世界经济,对所有消费者都有利。有了第二来源,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产品出口管制就失去了其用处,最后只会伤害自己国家的制造商。
但是拥有第二来源不应等同于试图实现完全自给自足。
在另一个国家/地区拥有第二来源,尽管往往只是作为一种可能性而存在,在很多情况就已足够。储备库存是另一种选择,但从长远来看,这并不是一个可持续的策略。
通过适当多样化供应来源,也可以减轻关键商品进口可能受阻的潜在影响。
食品、石油和金属矿石在世界范围内有广泛供应,适当多样化进口来源为避免意外供应中断提供了保障。库存是一种可行但只能临时适用的保障措施。
此外,即使中国经济继续增长,中国对铜和铁矿石等进口原材料的依赖最终也会下降。旧汽车和卡车,用过的电缆和电线中的废金属可以回收利用,并且可以替代当前进口的大部分原材料。甚至纸张和木材也可以回收利用。
这将为国际循环逐步过渡到国内循环创造良好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