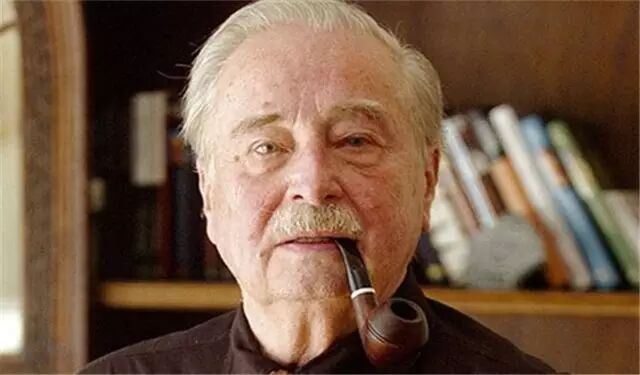
2016年12月17日下午,坐落在北外滩的建投书局,迎来了几位非常尊贵的客人:塞尔维亚驻沪总领事戴阳·马林科维奇、世纪集团副总裁阚宁辉、上海建投书局董事长滑雪、译文出版社社长韩卫东、翻译家曹元勇、作家路内、学者朱琺……他们齐聚一堂,不仅是因为一窗雾滴的外滩江景,更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参加《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的新书首发式,为了一起走进塞尔维亚文学大师帕维奇用他那精彩的文笔创造的又一个神奇的文学世界。以下是此书译者曹元勇、作家路内的对谈,主持人是学者朱琺。
朱琺:大家好!很荣幸今天和曹元勇老师、路内一起,来讨论《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这本帕维奇的第二次进入我们汉语世界中的著作。这本书具备一个有别于其他以往看过的各种小说的独特的地方,一个非常特别之处。想必有人已经开始阅读,有请本书译者曹老师介绍本书的情况。
曹元勇:帕维奇是个什么样的作家?至今为止,我作为一个译者,也没法把他讲得完全准确。就我的了解他写过诗,写过中长篇小说,最重要的是一部在世界上产生巨大影响的《哈扎尔辞典》。《哈扎尔辞典》是他在塞尔维亚(当时是南斯拉夫)产生巨大影响的第一部小说,80年代末整个东欧剧变,南斯拉夫产生了巨大变化,《哈扎尔辞典》就是在那个时代写出来的,当时还得了南斯拉夫最佳小说奖。之后,他又写了很多作品,后来还写了一些作品,《永恒之后又一天》这一类。他的作品其实有很多。随着南斯拉夫的解体,一个作家的命运往往也和这个国家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如果南斯拉夫还存在,帕维奇就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是很可惜。
路内:像帕维奇这样一位作家,在任何一种语言的翻译过程中,在任何一个国家,他都能找到自己的传承。但是很奇怪这样的作家人数是不多的,是一个少数。他对中国文学界起到的作用,对所谓先锋派作品的影响,如果我们严格地来讲,应该不是说对中国的先锋派,我觉得是对中国在当时90年代左右的小说走向都起了作用,令它走向一种更复杂的结构。其实中国先锋派小说是短篇小说居多。
但是像《哈扎尔辞典》这样的长篇大作,我当时在90年代末,自己开始写小说,我先看《马桥词典》,然后再看《哈扎尔辞典》,我觉得两者是没有相似度的。但是有一点是明显可以看到的,《哈扎尔辞典》引进后,在所谓先锋文学的实验性方面,中国也开始往“长篇的那种厚度”去努力,这个厚度不仅包括作品的厚度,还包括它的历史厚度,往深的地方去挖掘,这是因为《哈扎尔辞典》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确实引发了很多对于中国文学的可能性的遐想。
讲中国文学太大,十几亿人口统一使用汉语写作,但是有帕维奇这样的作家存在,使中国的作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退回到自己(假如说有个更小的小语种存在的话),我们退回到自己的小语种里面,应该怎么去写作。这种观念是有点潜移默化的,也包括对于我们反复去看中国民国时候的一些作品的写作方式。这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有我们南方小说的讲述的方式,有北方小说的讲述方式,我曾用广东话写小说,非常有意思,把广东的元素,闽南的元素使用得非常淋漓尽致。
刚才朱琺兄给我看了一份资料,是对帕维奇的采访,帕维奇说贺拉斯当时写作的语言,现在没人看得懂,只是经过翻译传承了下来。但是经过翻译的话,他的作品还是传承了下来,但你看到的其实已经不是他当时的语言。对小说家来说,内心都有一个梦想,第一个梦想是要完成一个对自己的语种有一个突破的作品,所以他会在自己的语种之内,整个语言非常花哨也好,非常怪异也好,还有一个目的,他要完成世界性语言的作品,经过任何翻译都能够流传出去的这样一个作品。谢谢!
朱琺:感谢路内兄很精彩地回顾了一下,或者说细化了帕维奇对中国汉语写作,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一种影响,这个影响实际上是内在的,一种深化的影响。刚才路内兄提到回到一个地域性的、小语种的地方文化,这方面上海已经有《繁花》这部小说了,之前也有吴语的文学。刚才路内兄谈到,我们台上每个人跟帕维奇都有一些渊源,这方面曹老师跟帕维奇的距离肯定是最近的,因为他对帕维奇的文本逐字逐句进行了一次翻译,这个翻译本身其实也是一种写作,尤其对于我们汉语来说。接下去请曹老师谈一下为什么会选择《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进行翻译,在翻译过程中他很有感触的、可以跟大家进行交流的事情?
曹元勇:可能跟很多90年代看到帕维奇的人一样,我是因为“马桥之争”事件开始关注他的,稍微回顾一下,没有1997年的事,也就没有后来一系列的事。当时我是去广州找工作,当时广州《花城》杂志转载了《外国文艺》的节选本,我在火车上就看了,真的看得很入迷。我心想和广州有缘无缘的也无所谓了,我完全被《哈扎尔辞典》所写的给吸引了,它的结构是非常开放的,里面描写的很多东西比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更有魅力。因为这些东西会进入到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比如说追梦人和捕梦者的形象。我恨不得自己也是一个捕梦者。当时完全被这本书迷住了。
之后我就开始找帕维奇是谁,开始了解这位作者,了解这本书。97年我没去广州工作,结果就回到上海来到了出版社。进出版社以后,那个年代在中国不看先锋小说,不读先锋小说,不写先锋小说就不是个好作家。我做了编辑,到北京找莫言交流,好歹我当时看了《哈扎尔辞典》,跟他交流这种开放式、立体的迷宫小说,莫言也很客气,他说:“你讲的我也很受启发。”之后所有帕维奇的作品我都在搜集,都在看。
《哈扎尔辞典》第一版出了阴阳本,我就逐字逐句地去阅读,比读古文下的工夫都大,不一定一眼能看明白。2012年年初,我到美国参加一个班,到了纽约,听说有一个大的旧书店。那几天我在找世界上最牛、最了不起的文学家,脑袋里面就蹦出来帕维奇的英文名字。看到书架上摆着他的三本精装版的英文本:《哈扎尔辞典》、《风的内侧》、《茶水画的风景画》。我就想是谁放在那里的,是不是在等着我呢。我把钱交了赶快领走了书,总觉得我晚交一分钟,别人就会把书抢走。从美国回来之后,2012年的年末,译文社又出了《哈扎尔辞典》的第二版。有机会通过翻译一个大师的作品,对我来说是能通过翻译,一个词、一个词地翻译,相当于一个人体一样,把每个细胞都摸了一遍,有这么一个机会用自己的手去了解一下帕维奇是什么样的人,另外也是对自己心目中了不起的作家表示敬意。2013年的时候,译文社把帕维奇另几部作品的版权也买下了,责编龚容让我选,我选了两本,一本是《风的内侧》,一本是《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风的内侧》是一个神话传说,一个是我很熟的希腊神话故事,另一本是塔罗牌小说。

▲ 三位嘉宾对谈
朱琺:很多人觉得包括《哈扎尔辞典》在内,帕维奇作品这样的一个文学世界给我们带来了灵感,有人坚信《盗梦空间》就是受到帕维奇作品的影响。请问一下路内兄,从一个作家的角度,如何来看待《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这样一部具体的作品?
路内:因为之前已经出过了卡尔维诺的塔罗牌小说,我对塔罗牌小说只会更感兴趣——就是帕维奇会怎么写?既然有过所谓的辞典小说,塔罗牌式的小说,帕维奇还有沙漏小说,易经小说已经被人写了,我就说要写一个麻将牌的小说。事实上小说这个东西很有意思,不是说我看了塔罗牌才学会怎么写小说,而是说我学会写小说以后,我要找到一个更有意思的形式来把它重新布局。
我那天看到一个关于塔罗牌的介绍,它说原先塔罗牌并不是一个吉普赛人算命的东西,实际上一开始就是看牌讲故事,每一个随机抽取来的牌,大家胡言乱语用一种叙事诗歌的方式来讲,我很想知道当时的人们是怎么想的,这种形式很有意思,如果你写短篇会发现,短篇小说有一种发轫的方式,就是你看着这个东西,然后你去想它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好的小说家我给你一个瓶子,一杯咖啡,一个椅子,三分钟让你写一个故事,把这三种元素串起来。我认识一个文学天才女作家,她可以看着辞典当中的词条,猛看半个小时就用这个词开始写小说。其实塔罗牌也一样,我们会发现讲故事这中间本身就带有很多巫术的传统。写小说就是讲故事,讲故事就是带有巫术这样一个性质的东西。当然一个作家也不是说完全在用语言小说的形式在玩弄结构,如果只是玩弄结构这个作家的作品留下来的时间不会很长。所以我觉得帕维奇给到我们一个非常宏大的东西,从他的结构形式把玩中间,像电子游戏玩法,中间给到一个非常宏大的东西就是家国命运,他把这个东西容纳进去,所谓文学的力量就被爆发出来了。那你会发现在一副牌中间、一副麻将中间,所谓家国命运已经存在了,这些都是在我们讲述的话语之中,在我们穿戴的符号之中,爱情可能就在一个纹身里。
朱琺:我们在讨论帕维奇的时候,必然也会连带着讨论卡尔维诺,这似乎已经是必然的,有记者问帕维奇,如果博尔赫斯在你面前,你会说什么?帕维奇说我就听他讲。刚才路内兄也谈到,塔罗牌小说之前至少有《命运交叉的城堡》,其实只完成了两部,一部是《城堡》,一部是《饭店》。使用塔罗牌的方式,我觉得倒是比较接近路内兄提到的塔罗牌最初作战争之外讲故事的设定,只能通过摆塔罗牌的方式一张一张摆,摆出来以后来表述自己的经历,但是失声了,通过让你们看让你们读来表示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一张塔罗牌相当于一个情节的单元,他可以被这样理解,也可以被那样理解,但是它的可能性还不确定。这个跟今天讨论的帕维奇使用塔罗牌,他要构造一种无限阅读的可能性,这个并不完全在同一个层次上,使用的方式并不一样。
路内:帕维奇这本书很好读的,后面还有一些后记,包括塔罗牌的使用方式,我以为翻到那一页已经结束了,这种阅读感觉是很有意思的,有一些书你盼着它快点结束,还有一些书你已经预知到它已经结束了,但这本书在你没有预知的时候已经结束了,我觉得很有意思。
朱琺:按照顺序来读的话,没有按照它的指示。
路内:这本书还是要按照顺序来读,这个顺序也是帕维奇写的这个顺序,他如果打乱写的话我没有办法读,但是他这样顺着写的话,我还是按照愿意顺着的方式来阅读。
朱琺:曹老师在翻译过程中,有没有觉得一些精彩的,乃至有难度的一些地方?您对它的意义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觉?
曹元勇:刚才说的卡尔维诺的《命运交叉的城堡》里,每个人切牌摊牌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摆开后一张一张地讲,我要编故事,它的意义在于看图说话。卡尔维诺写了一本以后又写了第二本,写了第二本,后来就没办法进行了,他从大塔罗牌写到小塔罗牌,这个难度很大。帕维奇就用了22张主塔罗牌,这些牌的名称相对来说比较容易,零号牌,这是一个起点,他找到了一条捷径。
我一边翻译一边想,假如说让来我写个战争题材的书,可能洋洋洒洒写个几部曲,长征是一大卷,朝鲜战争又是一大卷,当然那个大部头的书可能一个晚上就看完了,《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看第一遍时是个不复杂的故事,如果再看第二遍,你跳着看,抽出随便一章看,你会发现它其实是很复杂的,包含了很多细节在不同章节里,有埋伏的,这点我还是觉得很吃惊。翻译第一遍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小说是不是有点太简单了,和《哈扎尔辞典》不在一个档次上,但在我不断修订和重读过程中,发现他在每一个章节里,每一段里面埋伏了很多细节、暗示。就像讲一个人的命运一样,你前面走的路早已有很多暗示,只不过你在走的过程当中你没有注意,你没有发现。当然我没写过小说,至少可以告诉你一个宏大的题材其实可以用一个最凝练的方式把它写出来,不一定每本都写成洋洋洒洒的百万字,甚至七卷本八卷本,不一定要这样。而这样的小说它的信息量是藏在里面的,等着读者去发现。再加上帕维奇很多书里面都在讲,天才的读者永远比作家多,当然比翻译家更多,不知道在哪儿的了不起的读者,随时会冒出来。实际上作者是把这本书需要创造的东西交给读者,这是个最独特的地方。

▲ 塔罗牌
朱琺:话题已进入到帕维奇的文学观念这方面了,曹老师表达的时候,我就想到一点,我很想把《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拆开来,但译文社送给我的这本书,我实在舍不得拆,把塔罗牌放在旁边,而把里面的章节拿出来进行重组,或者像塔罗牌一样放在某一个部位进行阅读。
曹元勇:比方说《哈扎尔辞典》现在中文版排版的形式是按照英文版的排版,如果按汉语编排肯定会是一种新的方式,我建议译文社出个真正的汉语版《哈扎尔辞典》。《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我是2014年就给了译文社,我们的出版社是第一读者,出版人首先想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书,22张塔罗牌,正面塔罗牌的形象,背面是一个暗盒,暗盒展开来就是这一章,这样多好,这书现在卖128块钱一本,这样以后卖1280块钱一本,你抽出一个暗盒,拉开一个拉页,看到里面的故事,甚至里边再注解一下这个牌的要义,方式有很多。帕维奇当时只是想说读者可以随便从哪里开始读,但他真的没想到他的书会被我们中国人折腾成各式各样的。
路内:如果要按汉语顺序出版的话,汉字古代阅读方式从右往左竖着读的,跟横着读的感觉又不一样了。
朱琺:这些想法都蛮有意思的。帕维奇非常重视文学的建筑性,他父亲在塞尔维亚困难时期做过建筑师,对于文学作品,从小说这个角度上,他又提出一些新的或者按照我们刚才的说法,这是一种面对未来的这样一种看法,以往我看到一种说法,整个20世纪对形式主义文学有种诉求,但也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先锋小说家的表述,小说重要的可能不是写实,而是怎么写。在我看来,这样一个命题好像还没有完成,或者说还没有完成类似于从哲学史那个角度来说,好像帕维奇从这个角度走得更远了一点,他更进一步提出是怎么读的问题,他说书的危机是存在的,但是我们读者,包括刚才说的天才的读者,天才的阅读对象,他们可以对这本书进行不同的读法,对于作者来说,他其实可能要提出一些对以往书籍破坏性这样一种做法,或者这样的一种设置,我们可能会注意到,最近这段时间好像特别密集,徒有书籍的外形,里面掺杂其他东西,不跟我们书籍一面钉起来的方式一致。不知道路内兄怎么看?这对我们未来文学的发展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
路内:有些观念早在上个世纪就已经被接受了,但是有一种说法,帕维奇一直被认为是属于21世纪的作者。但我们从整个世界文学的角度来看,其实有一个倒退的现象。现在的世界后现代主义文学已经不像在上世纪末那样被大家看好,事实上我们至少退回到了现实主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以为这个时代会往前推进。从文化的角度来看,那是因为好莱坞太强大了,因为所有写书的人指望他们的小说被拍成电影,但是后现代小说是没办法被改成电影的。比如《哈利·波特》,它的内核说白了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传统、陈旧的文学观念,只是加入了很多奇幻元素,以这样一种写作方式被呈现出来的东西,也许这个东西更受人欢迎。有时候我们也挺悲观的,原来文学和政治一样,也会出现倒退,会开历史的倒车,没有办法,诗歌也是这样,唐诗之后中国没有诗了,那怎么办呢,那个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一千年了,再也没有可能回到那样一个时代去,那谁知道呢?不知道。
朱琺:可能小说也不能独立于世界之外,它也会受到包括影视在内的各种文化的强烈冲击。
路内:所以帕维奇还是走在前面的。

▲ 右起:阚宁辉、马林科维奇、韩卫东、滑雪
·END·
大家 ∣ 思想流经之地
英文ID:ipress
洞见 · 价值 · 美感

※本微信号内容均为腾讯《大家》独家稿件,未经授权转载将追究法律责任,版权合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