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席
抽 一根烟吧

电影《咖啡与香烟》剧照,导演贾木许
今天是世界禁烟日,我们邀请了五位诗人/小说家来和我们聊聊他们和烟的故事。此外,我们也编选了十首和烟有关的诗作供大家品读。欢迎各位读者在留言区和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和故事。
1 第一次抽烟的契机是什么?
身边有谁?
赵松:第一次抽烟,其实谈不上什么契机,也就是好奇而已,是十三四岁的时候,很偶然的,在家里柜子里翻东西时,发现了两条古瓷牌香烟。当时我父母都是不抽烟的,我奶奶抽烟,但抽的是旱烟,不抽这种卷烟的。于是我就确定这烟在我们家是没有用的,就拆开那条烟,拿了一包,叫上几个十三四岁的男孩,跑到对面三十中学的后院里,一口气把那包烟都抽光了。那烟挺冲的,我们又都不会抽,更多的时候,其实是拿在手里的,每抽一口,目的似乎只是为了不让它熄灭,而不是享用它的气味。
张尔:八十年代末读初中的时候吧,从家里顺走父亲的一包《阿诗玛》出去和野孩子们分享。觉得当时的硬装过滤嘴烟盒挺酷,那时整天和小伙伴们玩香烟盒的游戏,大部分是那种廉价的软装平头香烟纸,从路边捡到被扔弃的烟盒拆开后再折叠成一个个平板小方块。最终我父亲发现我偷走了烟,回家遭一顿棒喝。
2 您会喜欢在特定时间
/特定场所抽烟吗?
您是激情抽烟派还是温和抽烟派?
赵松:我不喜欢在有风的地方抽烟,不喜欢在人多的地方抽烟,不喜欢在不能开窗的地方抽烟,不喜欢在车子里抽烟,不喜欢在早晨起来后就抽烟,不喜欢在感觉饿的时候抽烟。最喜欢的抽烟地方,是自己的书房里,晴朗无风时的阳台上,少数好友聊天喝茶喝酒的时候。我可以一白天都不抽一枝烟,所以肯定算不上“激情派”。我也可以整晚都在抽烟,所以肯定也算不上“温和派”。只有在看书或写东西的时候,是不能不抽烟的。其它的时候,都无可不无不可。当然,我不会在家人面前抽烟,尽量避免。
孙磊:没什么特别的,首先是写作的时候,然后是聚会,烟量密度很大。我以前是一个烟鬼,每天接近三包,抽的很凶。现在因为身体原因,戒了。有两年多了。但还是不自觉的有些触及性的动作,也经常加入到抽烟的人群里,享受一下。甚至特别要求宇向抽一两根,聊一会儿,过过瘾。自己绝不动烟了。悖论的是,我网络简历上照片几乎都是抽烟的,也许我应该发一些不抽烟的照片了。

Unknown Photographer | Photograph of Siegfried Sebba leaning on a wall smoking a cigarette 1917
3 喜欢独自抽烟还是和别人一起抽?
有人数偏好吗?有理想烟侣吗?
赵松:自己抽烟,跟几个人一起抽烟,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的。甚至可以说,是两件事。只有自己抽烟的时候,才能清楚地感觉到烟的存在。而跟朋友们一起抽烟的时候,基本上是想不起烟的味道的,甚至也想不起抽了多少枝烟。人数最好不要超过三人。人多了,都抽烟,会觉得空气变得很臭。其实,自己抽烟抽多了,第二天醒来,也会觉得自己变得很臭。理想的烟友,一个是鲁毅,一个是萧开愚。鲁毅是平和派的。老萧是激情派的,他每一口都是深吸的,会让你觉得抽烟真的是件很舒服很过瘾的事,而他是绝对不会浪费一丝烟的。
孙文波:独自呆着就独自抽,和人一起就一起抽。
4 您会迷恋某种口味的香烟吗?
赵松:最初那些年,也就是整个九十年代,只抽云南的烟,当然是烤烟型的,焦油含量得在10毫克以上的。两千年后,逐渐喜欢抽相对淡一些的烟,从10毫克降到了8毫克、最后是4毫克,从只抽云南烟,到哪里烟都抽,从只抽烤烟型的,到混合型的也抽了。总的来说,喜欢醇厚些的柔和些的,具体的牌子就不说了。
孙磊:以前迷恋浓烈的烟草味,尤其纯粹的烟草。现在迷恋以前的那种迷恋状态。
张尔:九十年代末有几年喜欢抽两种烟,555和万宝路,偶尔也会买KENT和MILD SEVEN,那时有点迷恋一种略带些野性的味道。后来彻底不再吸这类混合型外烟了,只抽烤烟型,最佳口感还是云烟系。
哑石:说迷恋还谈不上。相对喜欢Marlboro的double bur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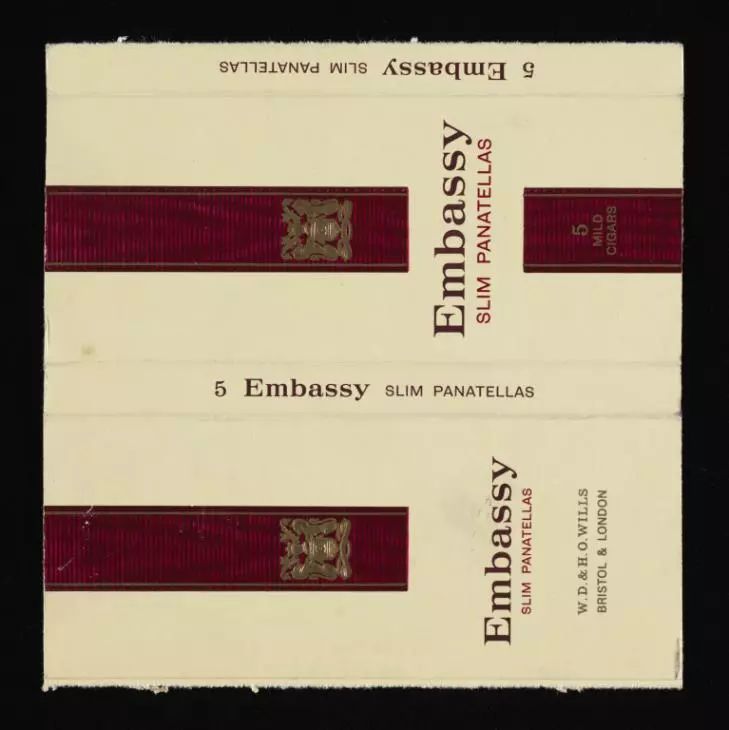
Conrad Atkinson Poem and a quote about Northern Ireland written on the back of a cigarette packet
5 抽烟是否把某个维度的“你”
调动出来了?
和不抽烟时候的“你”
有什么不同吗?
赵松:抽烟的时候,说明我在读书或写东西,而烟就是个呆在一边的伴儿。不抽烟的时候,也就是日常状态下的时候,那我也就是一个日常的我,而抽烟的时候,我觉得我是非日常状态的。另外,抽烟只是一件小事而已,抽烟的人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但根本不需要多说什么,想抽就抽好了,不想抽,就不要抽。毕竟,它不是兴奋剂或致幻剂。就我个人的体验而言,我可以把它带入到某个维度上,但它不可能反过来使我如此。
哑石:我这个人是个散烟子,常常独自走神。走神时若抽上一支烟,往往能把那个莫名所以的“我”唤回来。
孙磊:抽烟对我而言一直有一个神秘的维度,尤其在我戒烟以后,我更愿意自己进入多层的、高密度的、深度神秘的状况里,一种极其复杂多变的状况,甚至是晦涩不解的状况里。我越来越喜欢“零度”以下的暖意,也许这是北方人的缘故,但更多的是抽烟将我带入了这个维度,它让我面孔逐渐模糊,让我更自在更笃定地生活在这个不同的生活空间里,这有些玄奥,但很有意思。
孙文波:我不晓得。
6 您觉得是您在控制烟
还是烟在控制您?
赵松:所有的关系总归都是相互的作用。包括人跟物的关系。我不喜欢从“控制”的角度来看抽烟这件事。我可以一天不抽烟,也可以一星期甚至一个月不抽烟,这都有过。但这不代表什么,或许只代表我还没有那么重的烟瘾吧。这是件随时可以发生,随时可以结束的,令人轻松的事,没必要上升到谁控制谁的地步,那样还有什么乐趣可言呢?
孙磊:大部分时候是我控制烟,应该说,自觉性本身对诗人而言极其重要。烟和诗歌有时候是类似的,你必须有极强的自觉性或者控制力,才能让感受不无谓的浪费,才能更聚焦,烟也是聚焦的方式。当然,当诗歌和烟成为一种生命的自然惯性的时候,它也就成为写作的一部分了,甚至成为写作最精彩的部分了。也许这时候就是烟控制我的时候,尽管现在已经不抽烟。

Paz Errazuriz Adam’s Apple 1983, printed 2008
7您记忆中最深刻的
“抽烟瞬间”(自己或他人)?
赵松:有过不少类似的时候。要说“最”深刻,却真的不好说了。一定要说什么“最深刻的抽烟瞬间”,那肯定是跟人有关,也就意味着现场的主角其实并不是烟了。我还是比较喜欢把问题仅限于烟本身上。1995年夏天,单位里组织去兴城海边玩,后来又去了山海关那边。等往回走的时候,我们的一辆面包车的刹车片坏了,最近的维修点也在一百多里地以外,于是领导就安排我陪着司机,以每小时不到十公里的速度往维修的地方开。这是个很枯燥乏味的过程。司机师傅递给了我一包555烟,说是领导给的,他抽着不习惯,我可以试试。这是我第一次抽555烟,那种硬包的传统风格的包装。我抽第一枝的时候,当时感觉脑袋里忽悠的一下,真的,醇厚到会令你摇晃的感觉。
孙磊:那种瞬间有些残酷,我记住的都是命运中最不堪的时段,是“烟”陪我度过了那些时光,说起来还得感谢它。
孙文波:记不得了。
哑石:曾经为了好玩,含了整包点着的烟(20支)猛吸一口。结果很惨,瞬间口腔里就起了火辣辣的燎泡,大约十天都不得安生。
8 您曾和谁分享过同一根烟?
在什么情境下,有什么感受?
赵松:分享一根烟的时候极少有,有过几次,都是在野外游泳的时候,从水里爬上来,躺在沙堆上,晒着太阳,就特别想抽烟,又没带,这时候旁边有人把仅有的一根烟掰成两截,分给你一截,那是会真心感激的。但若是别人抽了几口的烟,再给我,我基本上是没法接受的。在我看来那是只有在战场上才会发生的事情。
张尔:大学宿舍里,那时候没什么钱,经常弹尽粮绝会断烟,大伙一起抽处心积虑攒起来的烟屁股。
孙文波:这种情况在年青时很多。与我同吸一支烟的人也不少。大多是年青时一起下乡的同学。

Sebastiao Salgado | China
9 有没有想要分享的跟
陌生人借火/烟的故事?
赵松:抽烟的人,跟陌生人借火借烟,是很平常的事,说平常,不是说它会经常发生,而是说,它发生是正常的,对于双方来说,都很正常,抽烟的人之间是不需要说借不借的,烟是大家的,火当然也是。印象比较深的,有两个场景。一个是在上海的,是在茂名路的一家茶餐厅里,那天晚上下大雨,我们几个人都淋湿了,我在洗手间里用干手机把头发吹干了。干爽的感觉刚一出现,就想抽烟了。可是没烟了。于是就想出去买,到在门口,发现雨还是很大,没法出去。正在那里纠结的时候,旁边有个年近五十的女士刚好在门边掏出烟来,点了一根,对着雨吹出了一个非常专业的烟圈。这我还能客气什么呢?我立即对她表达了借根烟的意愿,她立即从包里掏出那包立群,抽出三根给我,抽吧抽吧,我车里还有呢。最后连打火机也给我了。我在表达感谢的时候,她说了句让人舒服的话,抽烟的人,哪里分什么你的我的呢。还有一个场景,是几年前在美国,从拉斯维加斯到大峡谷的途中,有个中间换车站。在那个无比荒凉的地方,一座简易的办公室,建得比地面高出一米左右,侧面开门,门口还有个小平台,然后才是下来的一小段铁梯子,后面还有个院子,里面有公用洗手间,周围远近都是那种长得黑黑的有点像仙人掌的低矮的约书亚树,还有豚草,也是黑黑的感觉。风有点大,但我还是抽了烟,靠着大巴车,这样风会小一点。这时候,从对面的办公室侧门里出来一个很胖的女人,近四十岁的样子,她站在门口的平台上,点了根烟,几口就抽完了,始终都是面无表情。然后她靠着栏杆,面对着门,又点了一根烟。这次,几乎没抽几口,只是任由它夹在手指间慢慢地燃尽。
孙磊:我曾经看过一个片子,叫《跟踪》。片子的开始很迷人,讲的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闲着没事,随便跟踪人玩儿。我很想像那个人一样,倚在街角的电线杆上抽着烟,关键是抽着烟,观察所有我感兴趣的人,选择一个,把烟掐灭,关键是把烟掐灭,跟上去。一切都从这里开始,开始就足够了。
10 您有“事后一根烟”的习惯吗?
赵松:没有。
张尔:当然。
哑石:这摆谱的习惯,我当然不会有。
孙文波:有。

乐队Cigarettes After Sex专辑《 I 》封面
11 对您来说,烟和写作之间
是什么关系?
比如说会不会在写作时
大量抽烟或者几乎不抽?
赵松:写作的时候,肯定会抽烟的。但烟跟写作,其实也就这点关系,共在的关系,它们之间,其实并没有关系。有时候写东西也不怎么抽烟。有时候则会抽很多。
哑石:写东西时我抽烟要多些。可能对于我,写作的具体过程,尤其容易将自我的“无知”暴露在眼前,躲也躲不开。这需要一个仪式,或动作,来启动内在的“凝神”装置,以便穿越某种迷障,抓住一个个你瞬间觉得准确的“词语”。
张尔:写作时一定是抽的会比平常更多,经常一根烟抽两口就掐掉,但几秒钟一过又会再点上一根,如此反复,垒成一座词的拱形墓。
12 有没有自己很满意的诗/作品是在抽烟时得到的灵感?
可以分享下这首诗/作品,以及当时的状态吗?
赵松:《烟》(见文末)
孙磊:我很多作品都是在抽烟的状态下写的。这是一首戒烟前后的诗歌。(《这里》,见文末)
张尔:写过一首《造句》,是在一次猛抽烟时写下的。(见文末)
孙文波:好像没有。
哑石:没有专门写抽烟的诗,但有一首,确实因抽烟而得(旁人觉得烟味呛人)。诗说不上好,权且录下。(《经验》,见文末)

Nigel Henderson Photograph showing unidentified woman wearing long gloves and holding a cigarette holder
13 您第一个想到的嗜烟如命的
诗人/作家/艺术家 / 身边人是谁?
赵松:萧开愚。
张尔:孙文波、黄灿然,两杆老烟枪。我每次听到某个老烟枪突然戒烟了,就会心生失望。
哑石:德·昆西。
14 后悔开始抽烟吗?
赵松:一个人拿自己的爱好说后悔不后悔,我觉得挺奇怪的。
哑石:不后悔。对自己干过的所有事都不后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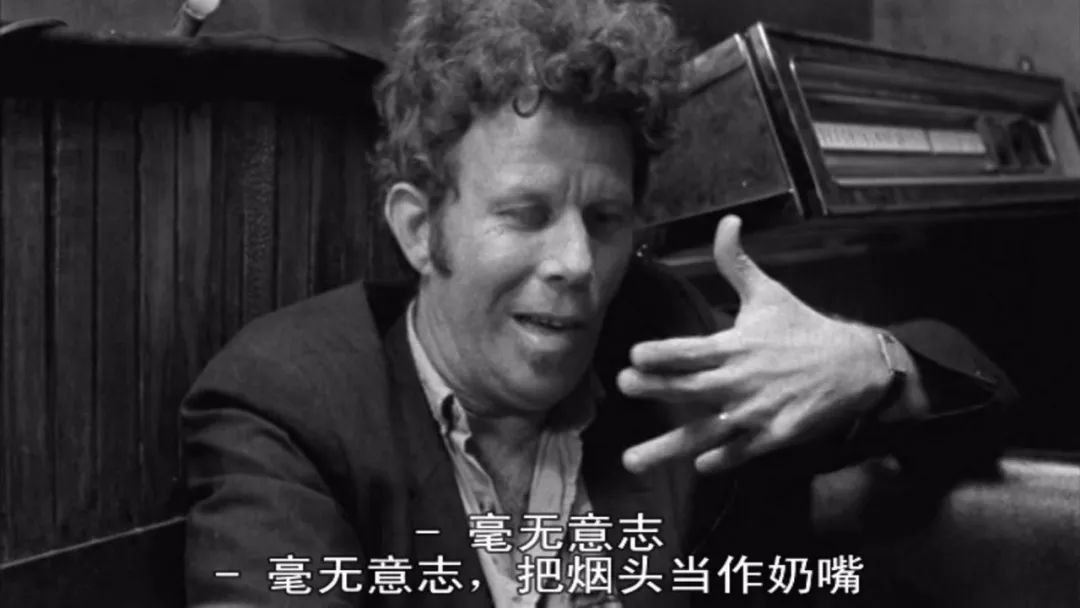
电影《咖啡与香烟》剧照,导演贾木许
15 什么时候您想要戒烟的念头
最强烈?(尽管不一定成功)
赵松:咽炎犯了的时候。
张尔:没打算过戒烟,不喜欢戒烟这样的行为。
哑石:就没动过戒烟的念头。不过我知道,一旦自己决定戒烟,就一定能戒掉。

电影《咖啡与香烟》剧照,导演贾木许
16 若您得知自己罹患疾病且病因是烟的时候,
您会怎么做?
孙文波:能抽就还抽。
孙磊:已经戒了。
哑石:千万别有这事。
17(如果尝试过戒烟)
最后没有成功戒烟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赵松:又不想戒了。
孙文波:我最长的戒烟时间是一个星期。最后复抽的原因是被一个朋友强制复吸(必须骂他几句:狗日的……)。
18 如果剥夺您抽烟的可能
您的最佳替代品会是什么?
赵松:没有。别的东西,就是别的东西了。替代品,对于抽烟的人来说,是不存在的。对于不抽烟的人,也是不存在的。所以,世界上其实并不存在替代品这种东西。
孙磊:现在更多地听音乐。
张尔:抗争。
孙文波:不晓得啊!
哑石:这个小小的恶习都要被剥夺吗?替代品,就算了。

电影《咖啡与香烟》剧照,导演贾木许
19 近年,不允许在咖啡厅/酒吧/书店等场所内抽烟已渐渐形成一种趋势,但这些场所又往往是比较适合进行创作或讨论的地点,您怎么看?
赵松:还好,目前还没发展到禁止在自己家里抽烟。庆幸吧。另外,我并不认为创作需要在咖啡厅里,更不用说能在酒吧里书店里了。抽烟总归还是需要有个比较舒服的地方的。还有就是,我觉得一大帮人,扎在一起抽烟胡侃,一年里有两次,也就够了。
孙文波:搞得抽烟变成了一件很麻烦的事。让人很不爽。
哑石:完全赞成在公共场所禁烟。这样的场所,除非征得所有在场者的同意,你才可抽烟,因为别人天然有不受烟毒害的权力。虽然,我们知道,论及同类伤害,也许雾霾比这个严重得多。
20 世界戒烟日(5.31)当天
您会象征性地戒烟吗?
赵松:这是不抽烟的人制定的日子。
哑石:干嘛要象征性地戒烟呢,除非你就此真的戒烟了。这世界,象征性的东西太多,我就不去凑热闹了。
张尔:想起来的话也许不在有人的地方吸,或者根本记不住有这天。
孙文波:不!
受访作者
赵松,作家。1972年生于辽宁抚顺,现居上海。已出版作品:《空隙》、《抚顺故事集》、《积木书》、《最好的旅行》、《细听鬼唱诗》。
孙磊,诗人,艺术家。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院实验艺术系、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实验艺术系。出版《七人诗选》(合著)《演奏——孙磊诗集》等。
张尔,诗人,策划人,出版人。2012年始,他先后创办了《飞地》丛刊、飞地传媒、飞地书局、飞地网络科技等,致力于建构内容创造与传播的全媒体平台。
孙文波,1956年出生。四川成都人。1985年开始诗歌写作。曾获“刘丽安诗歌奖”、“珠江国际诗歌节奖”、“畅语诗歌奖”。出版诗集《地图上的旅行》、《给小蓓的俪歌》等,作品被翻译成英语、德语、西班牙语、日语等多种语言。
哑石,1966年生,四川广安人,现居成都,在某高校经济数学学院任教。出版有《哑石诗选》、《雕虫》。首届“华文青年诗人奖”获得者。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玛琳·黛德丽 Marlene Dietrich 让女性抽烟成为了唯美而酷烈的镜头一幕
诗选
我要避开人群才能点燃一支饥渴的香烟
结局
韩东
抽完这支烟,我要去赴一个饭局
坐在出租车上,穿过傍晚的城市
然后来到灯光明亮的餐桌上
朋友们陆续到来,无不怀着
隐约的兴奋。一些生动的光
在他们的脸上一闪,投射到
洁净的瓷器上,然后
越来越旧
一天的落日沉没在油腻浑浊的酒杯里
这结局是我从一支烟的烟雾里读到的
在黑水
马雁
在黑水,我沉溺于琐事与眼色。
没有什么大是大非问题,零下4度
足以叫高速退化中的啮齿动物
嘘寒问暖,呵口气就成了仙。
小仙女们互相审视……能够
少穿就尽量少穿,也有的因此
一大早就倒在了白霜地上。
我没有多余的同情心,附和众人
兴奋地、尖刻地贬损那可怜的姑娘
正为自己的虚荣和孱弱付代价。
我们身体好我们吃五谷杂粮
我们无所畏惧我们得意地笑。
也是在黑水,我要避开人群才能
点燃一支饥渴的香烟。必须
在窗帘后在脏白色颤动的马桶旁,
我必须抽一支烟,我不停抽烟。
不止一个人在黑水,感到
上当、受骗。在荒凉的山谷
公路戛然而止,这分界线锋利
且毫不含糊:就让水泥的归水泥,
砾石的归砾石。从此颠簸在
陌生的山道上吧。或者,
不如归去?那些抬起无辜的头
一再张望直到天色渐暗
叹息着的人决定忍受寒冷
和一切可能的灾难,在黑水。
但我清楚,我很清楚:
根本就非如此正大,
这一切迟早都要结束。
此刻,我神情专注,敏感异常,
像伸着爪子探水的小动物。
但我正熟悉地厌倦着返回的路程。
2003年冬

电影Arizona Dream(1993)剧照
《阿特拉斯耸耸肩》节选片段
[美] 安·兰德
“火这股危险的力量,在他的手指间服服帖帖……”她想起了那个老人对她说过的话,他曾经说过地球上没有任何地方生产那种香烟。“人在思考时,心中便会燃起火花——这时,点燃的香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他的一种表达方式。”
我爱看香烟排列的形状
王小妮
坐在你我的朋友之中
我们神聊。
并且一盒一盒打开烟。
我爱看香烟排列的形状
还总想
由我亲手拆散它们
男人们迟疑的时候
我那么轻盈
天空和大地
搀扶着摇荡
在烟蒂里垂下头
只有他们才能深垂到
紫红色汹涌的地芯。
现在我站起来
太阳说它看见了光
用手温暖
比甲壳虫更小的甲壳虫
娓娓走动
看见烟雾下面许许多多孩子
我讨厌脆弱
可是泪水有时候变成红沙子
特别在我黯淡的日子
我要纵容和娇惯男人
这世界能有我活着
该多么幸运
伸出柔弱的手
我深爱
那沉重不支的痛苦

电影《母亲与娼妓》剧照
造句
张尔
柴门朝暮闭阖,反扣栓锁的双唇
任窗幔拉紧无轨独奏
幽暗尽头里一熄台灯星点孱弱鬼光
燃死的烟头云喷魔幻
垒成一座词的拱形墓
浓雾淋合,从眼角逼泪逼供造句
他脱下踢腿的缝纫镜边
晨昏中,使一枚银钱颠倒占卜
口服药剂口含的反对,
听服于不辞辩驳的绝对
和衣合被,扮半枯冷山
长眠于朽木的床板的片刻
他一翻身,遂引来父亲夜半敲门训呵
受洗于他拧紧的真理发条,
有机的脊背虚晃出一鼓坚韧耳膜
一纵深谷被病变瓦蓝捅破
2014/11/2
这里
孙磊
——给C·D·莱特
这里。总有一个平装的事实,
一种丢失。在街上,乌云
被树枝紧紧黏住。升起的建筑,
因其过剩的消费,而缓缓趴下。
曾经昂首的水泥。昂扬的性器。
在十字街头,落地窗对面的一排纱帘中
成为蕨类杂草的剧场。
尊严,沿着弧形的山岗,伸出舌头
露出饥饿的舌苔。我不确定
那些充满味觉的自由,是否
仅是一个角落,它强调最后的泪水,
最后一口烟,狠狠地,
我尝到咖啡馆之外的空旷。
而反光的湖面,涌向我的桌子。
我坐在这里,周围都是
操纵性的真理。几个学生互为爱情的上午。
几个女人互为情敌的晚上。几个老人,
互相孤立地展开审视。
我从他们的眼中看到死亡,
就像在波光中看到钻石,
那蔑视一切的力量,
再次蔑视我。
玻璃渣式的崩溃,不止一次了,
我与你有共存的平面,
而你总在我的意志上隆起。
我不得不抵住胃,
想办法让天色突然黑下来。
让更多的书,松弛。在我的皮肤上,
你是混合的、呛鼻的辣味,
一种叠句式的繁复的黑暗,让我怀疑,
死亡,从另一个角度扎向我。
这里。我是一件多孔的衣服,
为你开放一切。
开放愤怒、诱惑、讥讽。
开放雄心、自在、淤泥。
开放一个事实:“你来我就接受你。
你走我就放你走”。

电影《情歌恋曲》剧照
经验
哑石
一生中的很多时候 我们
都不太在乎绿叶背后的清脆欢笑
从那看似确切的地点(如公园的拐角)
走过 侧耳“听”上几秒
抿抿嘴 然后显得猫一样平静。
只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 我们
才突然察觉那是非常重要的经验:
黝黑、玄奥 像雷电劈开的坚硬松果。
世界以美丽的骗局孕育言语者。
你说:“月光下的青草总该很痴迷吧”
但这错了。就说公园的湖心
一对老年夫妇的游船出现轻微漏水
他们叫嚷着 满心爱意地
折腾 直到其中一人突然大笑起来。
这是另一种经验 真实 安全
几乎不可重复:其中些许冒险的快乐
像是语言伤口上的暗红花粉。
而将声音悄悄吸收的请求是可爱的。
譬如:一群诗友秉烛清谈
几小时过去了 幼波老弟突然说:
(他热爱幻象如同热爱生命中的雨水)
“老哑 把房门敞开吧 你的
劣质烟味太呛人了!”或者诚恳地:
“老哑 来 咱俩杀一盘围棋。”
这样的经验比绿叶背后的欢笑
更具隐秘性:真悲哀
因为我与世界的对弈总是黑暗的。
1996
我们确实说起过戒天才丛书
臧棣
谢谢。其实看天气,就知道
历史其实已很客气了。
云,比风更知道如何
保持距离。袅娜包括被袅娜,
摇曳最后的信任,
就仿佛我和我的影子
单独便能完成一个对话——
烟。戒了。因为吞云术
像是在表演死亡
也是一种贿赂。这么浓,
是的,轻蔑迷雾,的确能激发
一种人性的活泼。毕竟
每个人身上都有兰波的影子,
但仔细一听:天才,戒了。
还有什么好渗透的呢?
甚至提前就想到了
这一招:黑暗,戒了。
暧昧的代价当然不会小,
因为必要时:灵魂,戒了。
昨天因人而异,所以,有件事
确实可这么安排:今天,戒了。
所以,即使诗,戒了。我,戒了。
你仍然会读到这一行:沉默,戒了。
Only Until This Cigarette Is Ended
by Edna St. Vincent Millay
Only until this cigarette is ended,
A little moment at the end of all,
While on the floor the quiet ashes fall,
And in the firelight to a lance extended,
Bizarrely with the jazzing music blended,
The broken shadow dances on the wall,
I will permit my memory to recall
The vision of you, by all my dreams attended.
And then adieu,—farewell!—the dream is done.
Yours is a face of which I can forget
The color and the features, every one,
The words not ever, and the smiles not yet;
But in your day this moment is the sun
Upon a hill, after the sun has set.
只有在这支烟燃尽之后
埃德娜·聖文森特·米萊
只有在这支烟燃尽之后,
在结束的那小小的一瞬,
灰烬悄然坠地。
在炉火的光里,一支长矛被光线延长,
爵士乐摇摇曳曳,融于古怪的气息,
破碎的影,在墙上来回舞动。
我会容许我的记忆唤醒你的幻象,
那是我所有的梦造访过的地方。
然后,就是永别了,好好告辞吧!梦已终。
你的脸,我是可以忘记的
你的肤色,你的闪光之处,身上的每个地方,都可忘却,
但话语永不会褪去,微笑,至今尚在流连;
但在你的时日里,这个瞬间早已不再
就像山坡上日光仍在,而太阳早已隐没。
奕奕 译

电影《咖啡与香烟》剧照,导演贾木许
烟
赵松
二十支。撕开光滑轻薄的塑料膜,掀开崭新的盒盖,扯去封口处那一小块儿银色锡纸,经过这短暂的破坏,才终于到了这饱满的时刻,无须忧虑,抽出一支,盖上盒子,也可以就那么继续敞开着,这就是世界上最为宁静的故地之一,那缕即将来临的最初烟篆,无论你是否真的将它吸入过身体,都是关于坦然的最好信号,一闪而过。
十九支。停顿的时间由此恢复流动,了无声息的,异常缓慢的,又很具体,这第二支倒是更像第一支,前一支仿佛是额外的馈赠,这一支才是真正的开始。时间还有很多,可以随意。
十八支。跟得很快,那混合了灰白、火红与黑色的惬意的影子。烟在两端升起,烟灰纷纷坠落,火在向根部靠近,其实无需关注这一切的。它的价值里,最主要的,就是遗忘。
十七支。递给了别人。你不会去看它在别人那里如何燃起,然后如何消失。它就像从未存在过的。其实那个人对它也并无多大兴趣,纯属礼貌,他才接过了它,不得不点燃它,因为你已按着了打火机,伸到了他的面前。你知道他不会再伸手到烟盒那里,去拿下一支。无论拿还是不拿,你都会觉得有点遗憾。
十六支。发现盒子里有了顶棚的感觉,那是些密集的质地光洁而又足够轻盈的梁木,在冬天里接受着室内热气。空出了四分之一的地方。有那么一瞬间,甚至觉得你完全可以在那安稳地入睡,像在一间狭窄但舒适的木屋上方的小阁楼里,天窗是倾斜的。
十五支。然后,烟缸里有了五个烟蒂,姿态各异,躺在湿润的咖啡渣上,周围是细碎的灰白烟灰衬托着它们。这个时候,就自然而然的会有种停顿的感觉。没有任何负担,也没有任何迫切的需要,几乎是悠闲的,任由眼光飘在别的什么地方,甚至可以什么都不看。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开始,充满了可能性与不确定性。
十四支。如果真的是这样计数,那它就会忽然变成某种象征,纯属偶然,不可理喻,声音的世界里的嘲讽,泄漏的冰。
十三支。明朗的中年,其实是很多碎片。深不见底,但已是所剩无多。阳光锋利地捕捉着它的每一次细微变化,而你的每次瞬间出神都刚好成为它们的点缀,还有个并不算好用的节拍器,在脑子深处摆动着。
十二支。灰亮的光线,在弥漫。在指间,它呆了很久。并没有无限轮回的可能,因此在还有半支时就按灭了它。
十一支。忘了什么时候抽的它了。或许是下午,也可能是晚上,吃饭之前。它在指间一直很自然地燃烧着,直到那缕累积了很长时间的灰柱忽然倒塌,都落到裤子上面,伸手一掸,一片灰白。
十支。来了个朋友,递给他,点上了。他捏着它,几乎没怎么抽。
九支。抽了几口,搁在了烟缸边沿儿上,任由它自己慢慢地燃尽。燃烧到一半的时候,就给它往上挪了挪位置,还可以继续燃下去。最后,在你没注意到的时候,它终于失去了平衡点,翻落了下去,在桌角蹦了一下,掉到了下去,落到灰色的地毯上,用那点余热悄悄地烧出一了个黑洞。
八支。一个人站在阳台上,窗户留出一道缝隙。外面那些树冠在缓慢地摇动着,风有点大,不断从窗户缝里涌进来,不时扑到脸上。这样就抽不出烟味儿了。最后,你怀疑风是不是把烟吹灭了,就弹了一下烟灰,结果一小团燃着的烟丝滚落了下去,躺在花纹诡异的瓷砖上,完全变成了凌乱的黑丝。
七支。落单的一支,呛人。咽炎的症状。原因多了。
六支。过了午夜,重新开始,深呼吸。平时不会如此。
五支。阴影浮现了,它们仿佛都被某种异常幽暗的气息掠过了,稀少而冷白的脸。
四支。外面在下雨,带上它,去洗手间,在座便器上看书,点燃它,看几行,抽一口,还没看完一页,就抽完了。
三支。睡着了,然后醒来。洗过脸,看到它,忽然觉得还好,还有余地。于是若无其事地,深呼吸,想想别的什么事,看看时间,没问题,还可以再多等一会儿。
两支。令人不安的虚无感,远远超过只有一支的时候,像最后一道防线。真可惜,竟然也会没抽出什么味道。
一支。犹豫了半天,才拿起它,点燃,但很快就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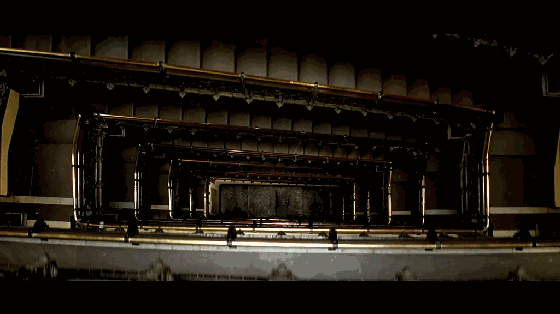
#飞地策划整理,转载提前告知#
首发于飞地APP,更多内容请移步飞地APP
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编辑:丛琪、翠羽 | 实习编辑:耿扬
点击“阅读原文”
阅读《抽烟吧:电影中的抽烟片段》
专业!有趣!活泼的!飞地实验课现已上线!
至少我们应该朝那个方向努力入门
点击下图了解详情

今日起至6月4日前,转发上文(海报跳转后的文章)至朋友圈,将截图发送至后台,编辑会从中挑选两名读者免费赠送一门课程,中奖名单将于6月4日当天推文末公布。
重 要 TIP:
进入公号主菜单点击文章索引,
输入关键词即可索引所有号内相关文章!

| 部分关键词检索列表 |
欧洲
洛尔迦 | 布鲁诺·舒尔茨 | 杜拉斯 | 塞尔努达 | 巴塔耶 | 布尔加科夫 | 卡夫卡 | 荷尔德林 | 特朗斯特罗姆 | 佩索阿 | 梵高 | 阿米亥 | 苏莱曼 | 安伯托·艾柯 | 贝克特 | 罗伯特·穆齐尔 | 让·鲍德里亚 | 保罗·策兰 | 荣格 | 辛波斯卡 | 罗兰巴特 | 波德莱尔 | 保尔·瓦莱里 | 马里内蒂 | 布罗茨基 | 卡尔维诺 | 亨利·米肖 | 艾基 | 阿尔托 | 波伏娃 | 萨特 | 圣埃克絮佩里 | 芬顿 | 希尼 | 达菲
亚洲
张枣 | 黑光 | 昌耀 | 海子 | 王小波 | 顾城 | 张爱玲 | 多多 | 骆一禾 | 姜涛 | 朱朱 | 马雁 | 也斯 | 黄灿然 | 林奕含 | 吴兴华 | 草婴 | 方向 | 沈从文 | 痖弦 | 苇岸 | 谷川俊太郎 | 夏目漱石 | 王敖 | 邓安庆 | 叶美 | 陈舸 | 白先勇 | 杨牧 | 管管 | 荧惑 | 洛夫 | 三岛由纪夫 | 陈东东 | 周鱼 | 废名 | 关天林
美洲
柯尔索 | 艾略特 | 布考斯基 | 亨利·米勒 | 金斯伯格 | 沃伦 | 卡佛 | 约翰·阿什贝利 | 庞德 | 罗伯特·勃莱 | 福克纳 | 博尔赫斯 | 科塔萨尔 | 略萨 | 马尔克斯 | 聂鲁达 | 巴列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