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
-
克莱尔·德瓦拉(
Marie-Claire Dewarrat
)
1949
生于洛桑,主要精力用于照料家庭。她的处女作是短篇小说集《野蛮的夏天》(
1985
),作品出版后获得了大众藏书奖。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斋戒》(
1987
)获得了次年的米歇尔
-
当唐奖,其他作品还有插图小说《海鸥的季节》《十字架之路》《印第安领地》以及一些回忆录。
德瓦拉是在瑞士拥有读者最多、最受喜爱的作家之一。作品的文字精当而又敏感,她的灵感往往来自于民间故事中的魔幻神奇的特性,她往往通过一些表面看来可能是最平常、最平庸的生活碎片,编造出结局出人意料的故事,把读者带入一种充满着强力的情景,却又在强力的裹胁中体验细腻的情感。这种强力与细腻的矛盾体,在短篇小说集《我的爱在地狱》这一书名中得到了很妙的体现。

玛丽
-
克莱尔·德瓦拉作
郭昌京译
又是星期日。
星期一,喔唷!她喘口气。星期二,她搞搞卫生。星期三,她作些计划。星期四和星期五,她努力去实现。星期六,她盘算一周的失误。而这会儿,又是星期日了。
怨恨星期日是如此稀松平常的事。然而又怎么样呢?她既无别样的感情,也无其他怨恨更甚于她这辈子与生俱来的对星期日的厌恶。

远溯她的记忆之路,她记得自己总是讨厌这日子,或许它们的上半天除外。直到正午,星期日还算可以。她稍稍慵懒一些,她滞留在牛奶咖啡的雾气和报纸的油墨气味中,她做饭。
她甚至回想起星期日愉快的上午,教堂钟声的所有颤动,偶尔加上堂区节日的铜管乐,特别是她十五岁的白裙子,那么开敞,那么宽大,那么轻盈,以致在它的飘舞中,她感觉自己如同一株花茎。
是的,星期日早晨尚可,至少那时如此。
然而,自午饭起,上午的兴奋和愉快就消退了。下午如同一个蓝色和金色的大洞,或者被雨弄成灰色的大洞,一个她在其中无着无落,什么都无法抓住的五六个小时的虚空。
父母们饱食过后睡着了。男孩们成群结伙儿去诱骗磨坊的鳟鱼,或者猛攻没有设防的果园。朋友们外出串门。洗刷停当的锅碗瓢盆,厌倦了而合上的书本,她不知道怎样按照自己的心愿安排生活。
她能发现的唯一愉快的事情就是躺在高高的草丛中看云彩的变幻。这样面对天空躺着,她自己融入它们的缓缓移动中,融入似乎将尖利的锋芒刺入碧空的干草的摇曳中。
起身时她感到一种不可思议的难受。在几个小时里,她变得沉甸甸的躺在地上,那么重和僵硬,以致她觉得已经慢慢地嵌入土里。这种感觉似乎令她达到幸福的极至。
然而,整个星期日既不阳光普照,也不暖和,也不绿意盎然,也不金光灿灿,其大部分只呈现一种无尽的空虚感。
当她认识了保尔,星期日的厌倦消失了好几年。
生活中的所有日子被分成两部分:她见到保尔的日子和她没见到保尔的日子。很长时间她相信同保尔一同生活则节日永驻。在她没有觉察到自己的错误之前,保尔有足够的时间让她生下几个孩子。实际上她根本来不及意识到,保尔变成了死气沉沉的节日。小家伙们在她生活中映出那么多的焰火,从而很快化作她的另外一种快乐,更粗犷,更原始,比夫妻之间的那种更温柔。但是同许多女人一样,她只是在他们远离她的时候,才真正品尝到自己孩子灿烂的光芒。
保尔留下来。
他,他还为她而容光焕发吗?
挂念着远离的子女,她能用各种新鲜的欢乐重新笼罩他吗?
这么多年之后,他们两人还会找回互为快乐的那种情趣吗?
在诸多努力之中,他们有一段时间试着相信这点。然而,习惯的共有钟摆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往复于他们的爱情史中。
就是这样。
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中的日子越来越相似,有规律地被另外的、不像日子的日子打断,那种只用于衡量比这闲散和空虚的时光更孤独的日子。
保尔呢?
保尔星期日干什么?
随便什么事情:玩一圈牌,看看书,中午睡一大觉。总之,不管他干什么,不管她想干什么,他们都可以一同干,但从未感到心照不宣。
而这次这个星期日比平常更糟。
他们的长子十点钟打来电话说放弃了来家吃饭:
“宝贝咳嗽。玛丽
-
昂日头疼。我向你保证下个星期去看你们。是的,是的,我拥抱他们。对,他们同样。不,妈妈,别担心,我们星期一带小家伙去大夫那里。再见。拥抱爸爸。回头见。”
完了,节日。
另外两个,儿子和女儿,住得太远而不能经常回来。
她把一部分肉放回冰箱里,那么,炸土豆条还吃吗?还有菜豆、烤西红柿呢?当然吃。她甚至决定把脆生生的沙拉和原来准备做甜食的巧克力木司都端上来。尽管它本来可以一直放到星期二,并让吃得太饱的胃有些遗憾。
可保尔面对装得满满的盘子一直在低声埋怨。他让她解释了两次为什么雅克没有和他的小家庭一起回来。他又提起儿子们没完没了的旅行,并拒绝喝杯咖啡。一离开饭桌,他就倒进扶手椅好把他的坏心情隐藏在报纸后面。
“我们出去!”
阳光洒在窗户玻璃上,窗框似乎难以容纳春季天空的所有蓝色。
“我们出去,保尔。”
窗帘于压在首批郁金香脆弱株茎上温和的气流中卷起。
“我们出去,保尔,天气多好呀!。
从屋前的花园传来鸟的鸣叫,在阳台的栏杆上稍事踌躇,就跳进人们会称之为充满山雀的厨房。
他们出去了。
但首先要折上报纸,掐灭吸了一半的雪茄,并为弄清楚去哪里激烈地争论。
“走着去?开车去?你有主意了,瞧瞧,因为是你要出去的!”
然后,他还要刮脸,嘟囔一会儿决定穿灰色的裤子而不穿棕色的裤子,找汽车钥匙,忘了手绢,再去一次厨房,因为不敢肯定是否关上了炉子。
总之,他们出去了,连收拾桌子的工夫都没有:面包会稍稍风干,长颈大肚瓶里的水会变得温吞吞的,管它呢。
坐车兜兜风,然后步行,“因为你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无论谁都会说这片森林里气候宜人。是的。同意。但是,这话真正的含义是什么?

洒落的阳光给树干镀上金色。微风为所有算得上有绿叶的树冠披上彩虹般的色彩。透过那下面的树枝,在淡紫色山峦的下面,湖光闪烁。
人间的喧闹隐没在矮树丛中,走兽偷偷摸摸地穿行,飞禽扑腾着,令人无法辨认披着羽毛的身体。
树荫下没有人,除了埃丽丝和保尔没有其他人。他们咔嚓嚓的脚步粉碎掉沉寂。
这就是这片林子里的宜人之处。
埃丽丝在树林中总感到幸福。
一来到树荫下,她就全身舒展,对着辛辣的气味,对着这座圣堂各种各样的悸动完全敞开自己。
保尔走;她漂。他呼吸;她品味林子的气味如同品味陈酿老酒。他穿过矮树丛前进,以不容反驳的脚步踏破枯松针铺就的地毯;她游窜于树木之间,找回了灵敏的动物般的步态。
又一次,分开他们的距离,两米多,变得无法逾越。
保尔并不品味他的散步:他投入一些时间,指望森林用清新的空气和放松还以他相应的报答。其余的对他无所谓。埃丽丝感觉到树叶、根系、淡淡的花朵和浆果的生长。当她把手贴近面庞时,似乎就是在呼吸树汁的清香。
这事来得突然。
她走在气喘吁吁的保尔后面。他对她谈论着上一次几乎不存在的秋季蘑菇的收获,就如同森林尚欠他的一笔债务。
她又感到脚掌上、沿着小腿肚子、大腿后面针刺般的感觉。
这种奇特的感觉汇集到脊柱底端,沿着脊椎骨向上爬,同时绕着她的胯部弥散,沿着腹股沟溜到肚脐。
还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她感到后背被一双热乎乎的大手推了一把,撞到保尔身上,他转过头来,惊慌失措。
“你怎么了?你摔倒了?”
她回答说:“没有,没关系。我肯定走得太快了,有点儿不舒服。会过去的。”然而,话停留在脑袋里,有条有理的,任何声音都没有从半张的嘴里出来。她的舌头僵直,有一股新鲜的苔藓味。
她想站起来,撑住丈夫伸过来的手臂,可是不但没有脱离开他,反倒俯跌进他的怀里,被仍然有效地压在她腰部的那个动物肌体的热量固定在那里。
“你怎么了?站不起来吗?”
她不再做任何解释,同时也不再做任何挣扎。这股将她贴到丈夫身上的力量,也让她的手缠住花白头发男人的后颈,让她的腿盘住灰色的裤子,并让她塞满了植物的嘴贴在保尔的脖子上。
“停下来,你疯了。人们会看见我们……停下来。这不再是我们这个岁数人的事了。”
他们靠着树干滑下去,均有些尴尬,理不清地融在一起,翻滚在两条粗树根圈出的松软的枯树叶上。
“看看,看看,你撞上什么鬼了?我们不能……”
这是保尔最后的话。
当一股腐殖土的强烈气味灌进口腔的同时,他感到他的舌头变厚,膨胀,变得庞大无比,灵巧轻浮。埃丽丝给予他一个震撼身体每根神经的吻,他所知道的独一无二的人类感受。这是一种他向来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于激情,于活力的无以伦比的陶醉。
人们对保尔和埃丽丝的神秘失踪越想越糊涂。
人们掂量,怀疑,察看,翻找他们留下的那些物品却什么也推断不出来:半截雪茄,两只脏盘子,里面凝固的汤汁围拢着剩菜豆,留在餐盘上的一条干净手绢。
他们的孩子非常伤心。不久,他们继承了遗产。因为生活在继续,同时他们的朋友和他们的邻居也不停地对他们这样重复说,他们便慢慢地重新享受它给他们带来的各种快乐。他们保留了房子和小花园,在假期中共同拥有。
他们在每年的万圣节聚到这里,公开抱怨说一直不能到墓地献花。午饭过后,他们到树林里转一小圈消食。小家伙们跑在前面,父母们庄重地沿着小路前行。
一天,孩子们聚集到一棵巨树脚下,高声喊叫让大家去欣赏他们的发现。在这棵巨树的两条粗壮的树根之间,生长着一棵那么绿,那么茂盛,其叶子那么油亮,其枝条那么茁壮的灌木,以致所有人一动不动地审视它很长时间。
然后,某人暗示植物的变异,毫无疑问是因土壤和空气的污染所至,污染可以导致,依据某些科学家的话说,令人吃惊的后果,甚至在最普通的灌木上。
人们沿着来的路回去。孩子们倒退着走,为了尽可能长地注视那棵奇怪的植物的火焰。
没人发现,在繁枝茂叶中,低处的一根枝条上,套着两枚失去光泽的金戒指,几乎被埋入大地。
原载于《世界文学》2000年第3期
版权所有,如需转载请经公众号责编授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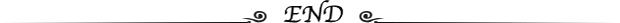
《世界文学》征订方式
订阅零售
全国各地邮局
银行汇款
户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开户行:工行北京北太平庄支行
账号:0200010019200365434
微店订阅

★ 备注:请在汇款留言栏注明刊名、订期、数量,并写明收件人姓名、详细地址、邮编、联系方式,或者可以致电我们进行信息登记。
订阅热线
:010-59366555
订阅微信:
15011339853
订阅 QQ:
3076719982
征订邮箱:
[email protected]
投稿及联系邮箱:
[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