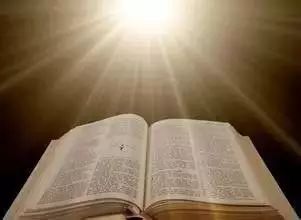5月16日,由人文经济学会主办的《
双轨制思想与中国经济改革——张维迎双轨制论文发表35周年研讨会
》在北京举行,国内近20位经济学者出席研讨会。
下文是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
毛寿龙
教授研讨会现场发言的整理稿。我们还会陆续刊发其他参会学者的发言,敬请留意。
价格改革双轨制的优势与下一步改革
毛寿龙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
1984年张维迎教授《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篇文章非常棒。一篇文章35周年之后还能开一个会来纪念,本身就说明这篇文章的价值。实际上,正是价格双轨制改革,区别了中国改革和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道路。苏联和东欧铁幕降落,但走向自由和繁荣之路遥遥无期。但中国从价格双轨制改革开始,后来相关改革以此为基础推动,保持了改革的连续性和容易度,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演化改革思路。从理论和实践角度,都有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力量。
刚才张曙光老师说,后来在很多领域,其实都是双轨制推动的,说得非常对。我现在在思考的是,从回溯性总结的角度,思考双轨制改革的成功逻辑,存在的后续问题,以及需要进一步改革的思路。
回顾中国的改革,的确是从价格双轨制改革开始的。价格放开后,商品在市场中就有了适当的价格,也就是市场价格,从而形成商品贸易的市场秩序。市场秩序是扩展秩序,从贸易开始,秩序扩展进入物流,进入投资。劳动力自然也有价格,企业家和企业也开始有价格。但后者也是双轨制到现在。
劳动力因为工资市场化,开始有价格。有价格就开始有价值。劳动力的身价开始提升。劳动力市场秩序越发展,劳动力价值越是提升,劳动力素质也大大提升。一直到现在,世界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流的产业工人,都是中国民工。中国民工走向世界,而且是高技术、高素质,工作996的好工人。甚至退休的老年人,在浙江,退休不退休,都继续工作,都有自己的身价。浙江的老板很喜欢老年的工人。但很多地方,很多领域,劳动没有市场化,体制内问题依然存在。如高校,现在连论文生产都计划经济化,大家都拿学术工分。学者和学生学习、写作与过去的农民一样辛苦,但没有生产力,做很多没有价值的劳动。
市场秩序进入企业领域,企业就有自身的品牌价格、企业家也有身价。企业家的价格,企业的品牌价格,构成股票市场的基础。潜在的项目和企业家,构成创业企业家。start-up产业,受到世界投资市场的鼓励。华尔街与中国关系最好,中国的start-up项目,很受世界欢迎。但国有企业,还是身份制的。国有企业的价值,在其国有企业的身份。市场里,首先强调自己是双轨制。
住房改革,双轨制。老房子老办法,新房子新办法。货币化分房。住房进入市场有价格,形成了房地产市场秩序,也形成了新的业主治理。业主自己付费,自己治理,委托专业化管理。小区会议遵守罗伯特规则,业主大会,业主代表大会,业委会会议,议会政治在中国生根发芽。专业的物业管理也进入市场。社会秩序和业主治理、市场治理相结合。构成新型城市治理。破除了中国古代一直延伸到现在的城、郭、郊、野的等级治理。
现在资金进入市场。货币也有价格。资金价格启动资金市场秩序。构成去中心化的货币市场秩序。人民币开始有其自身的价值。人民币不再需要回笼,而是在资金市场秩序里实现自己的市场价值。构成了货币性资产。最近十年,很多企业家都尝到了以钱生钱的好处。
但双轨制改革的问题还在继续,其核心是留下了很多利益集团。每一次改革,都形成了利益集团。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市场垄断集团,以地盘和线为基础的垄断集团。基层治理,形成了很多黑社会、黑恶势力,还有腐败势力。隔一段时间,就需要打击黑恶势力。最近扫黑除恶,有企业家说营商环境好了很多。但经常性扫黑除恶,让政府治理出现了一些问题。包括周期性,现在是长期性治理腐败,让政府的活力受到了一些影响。
在国际贸易领域,形成了国际贸易的利益集团。他们有独占权,垄断权。进口和出口配额保护,关税保护,补贴保护,形成利益集团。自由贸易,和贸易管制,双规依然存在。这一领域的双轨制,以及其他双轨制,让中国市场和国际接轨出现了问题。中美贸易战也因此而触发。
市场秩序进入政府治理领域,政治企业家开始有价格,体现在GDP的政治利益和个人利益。两者都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黑恶的。两者界限不清,让很多很有价值的政治家过早结束了政治生命。市场化的企业家官员,和身份制的非企业家官员,也就是好好当官的官员,构成了政治成长的双轨制。
价格改革形成市场秩序的改革,忽略了产权改革的意义。盛洪教授写过书说,交易形成产权。非常正确。但由此形成的产权,缺乏适当的法律和政策基础,尤其是缺乏善治的基础。产权在市场中通过边际增量元素形成。降低了市场改革的交易成本,但也出现了后续的一些治理结构的问题,尤其是法律和政策的问题。
就住房来说,南方市场化彻底。地权和住房产权结合。上海,浙江,广东,治理上都没有问题,全部商业化。但商业化后,业主的权力,业主的治理,发育比较缓慢。业主的法定治理权利,没有法律和政策的保护。
但北京地权和住房产权没有结合,其结果是治理上进入了矛盾:商业化治理不是很彻底,新兴小区。传统小区,弃管小区,或者单位继续管理的小区。后者理论上说不过去,前者政府继续主张非商业化的治理。北京市有人主张消灭业委会,走政府、居委会和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道路。但主张领导出事后停顿了,治理上出现一些问题。
就农村改革来说,改革最早,但产权改革不彻底,没有形成产权的治理。结果是土地和劳动力无法进入市场,也无法吸引投资,有投资就有产权风险。只能进入城市化当民工。农村普遍衰落,但衰落的问题,在中国更加严重。因为治理、法律和政策方面缺乏对产权的足够的支持。小产权,流转权,都缺乏保护。最近的拆违运动,给农村又造成了所谓拆违运动扩大化的伤害。农村改革双轨制,一部分市场化,一部分计划体制,市场元素外流,计划体制扼杀农村发展的活力。
企业依靠政府许可,土地产权(转让和许可、划拨)、资本市场产权(许可),企业与政府关系密切。依靠大数量来理清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但企业数量少的地方,投资环境就很差。导致中国的发展集中在几个省,很多省依靠中央政策来发展,东北中央政策发力,三亚现在是北海住房就涨价。
政府依靠复杂性来获得合法性和力量。条块关系,或者让属地化管理无力量,或者让属地化管理负担很重。企业纷纷进入大城市,与高等级政府对接。但特大企业越到高层,越受不稳定的政治的影响,导致大企业家风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