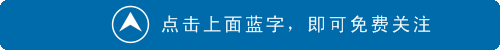
天涯微信号:tyzzz01
天有际,思无涯。
《天涯》2017年全年征订,108元六期,包六次快递。点击左侧购买。

本文来源:《天涯》2015年第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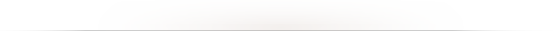
写东西的人需要在生活中成为哑巴
巫昂
有一天晚上,我去参加单向街书店的文学之夜,那天晚上是卡夫卡专场,单向街做糕点的师傅很别致地发明了变形记小蛋糕,一只方块蛋糕上趴了一只迷你的甲虫。上一场的文学之夜是茨威格,我阴差阳错没有去成,但在心里头,我是更喜欢卡夫卡而非茨威格,这种喜欢累计于年少时节,上大学那会儿,不看卡夫卡的中文系学生是不对的。我们看《城堡》、《饥饿的艺术家》、《变形记》和《乡村医生》,对卡夫卡的篇目耳熟能详,而且知道他一生跟自己的父亲搞不好,做了一辈子的保险员。
你说我有多懂卡夫卡,我不知道,我读到他写给密伦娜的情书后,才意识到他不仅是个文学天才,而且是个敏感多情的瘦削男人,像所有热恋中、通讯不方便的时代的恋人一样,每天掐着手指头计算时日,等着对方的信件或者电报,说真的,这些信让我有些吃惊,我本以为卡夫卡是个敏感然而无情的小说家,有着德奥人冷静的血统,当他全然地把自己的激情暴露在那些私人信件里,像一个不带皮肤的卡夫卡,血肉模糊的卡夫卡,毫不犹豫地将心掏出来给对方看的贾宝玉式的卡夫卡,甜蜜思念的卡夫卡,伤心不已的卡夫卡,悲观绝望的卡夫卡,在爱当中不打算有所保留的卡夫卡。爱情在他内心翻腾的波澜比外表汹涌得多,也激烈得多,爱情像块炭火将他炙烤得滋滋响,而这,可能是他单方面的感受,与对方无关。
他有一双近乎偏执的沉静的大眼睛,理着公务员一般的小平头,永远在一张黑白照片那头看着后世的我们,我们这些不安的灵魂啊,有几个能有这样的神态和执拗,这样的内心丰富而外在庸常的一生。谁能够真的除了对小说自身的爱之外,别无所求呢?我不知道,我也问过自己,但我给不出全然的答案。
我生于1974年,写诗有十六个年头,写小说有十四个年头,写文章,不算写作文的漫长历史,大概齐有20年,我们这么大的人,读大学中文系,大概齐都读了很多外国小说,诸如刚才说的卡夫卡,然后是美国文学里头的海明威、塞林格,喜好海明威的简单明了,和塞林格的个色劲儿,后来才知道那叫邪典小说。
啊,邪典,听起来就好想参与这个犯罪团伙。
邪典的经典之作还有《二十二条军规》和《万有引力之虹》,大家伙儿简直崇拜极了,话不能好好说,非得把姿态摆足,前者还算至今看得明白,后者我看了第一个字母就睡着了。再比如垮掉的一代,说起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一个字儿都没读过的年轻人,都会佩服到五体投地,青春就得在路上啊,过着动荡不安的激烈生活,抽着大麻泡着妞,跟残酷耳鬓厮磨与坏脾气共舞,当我们开始写东西,脑子里就是这些东西,都想写出那种很酷的东西,都有点儿翻译腔,都不知道平实为何物,谁跟我谈俞平伯般的平实,周作人式的冲淡,那是要被鄙视的,想要那种对生活怒气冲冲的架势,要那种突破主流价值、拿骄傲的脑壳来当作机关枪的阵仗。
得到多少岁,才能真懂得契科夫之味?有一阵子,我好像真读明白了契科夫,这个俄国老儿的幽默和心酸,那种美滋滋乐在其中的文字癖,活灵活现的人物,和讲故事的能耐,当真吸引人,看了一篇又一篇他的短篇,实在好实在感人。
而且啊,我们也是被《红楼梦》弄得神魂颠倒的一代,跟好朋友聊《红楼梦》可以聊到完全入戏,以前我觉得自己是林黛玉,后来才发现自己是没心没肺的贾宝玉,头天因为被一只小蜜蜂蛰了烦恼不已,次日看到日头好风儿轻,又兴高采烈地找林妹妹玩儿去了,忘性跟记性一样大,跟苦难啊沉重啊有仇,骨子里是排斥路遥那款作家的文风的,但会喜欢路翎那种俄罗斯范式的心理分析。
上面说的都是别人的影响,下面说说我自己的事儿。
我在年少时,也曾对先锋这个词迷恋不已,不先锋就不要谈了,总觉得讨论一切问题,都要用先锋这把尺子量一量,才靠得住,那时候认为先锋不单是出发点,也是解决方案和终极目标。所以,虽然现在觉得残雪那种非常看不懂的先锋是故意吓唬人,当年也不敢贸然非议之,还有点儿被蒙住的意思。后来发现,扎扎实实地先锋,那就是张承志跟早年的马原,以及某些余华,落实到我们自己写的问题上,他们的经验则缺乏借鉴意义了,因为我们写不出《活着》,也不乐意再写,那种灰蒙蒙的、泛着苦的胆汁儿的文学。
七零后普遍地离苦得乐,比前辈们要富裕些,我说不单是钱的问题,内心有了别的向往,想要魔幻的、离开生活五厘米、更加纯粹和直接的虚构能力,会更贴近自己有真实感受的长大后的都市生活,会爬到现今的人的心里头去抓挠出一些新鲜的事物。这是我对我们七零后一代的乐观主义。
我自己呢,这三四年来,一直在写侦探短篇小说,写了也没几个,花了打力气去刻画私家侦探以千计,我想做一些纯文学和类型文学的尝试,这个事儿做的人多了,从爱伦坡开始,到雷蒙德.钱德勒,到劳伦斯.布洛克,他们的侦探小说不像通俗小说,里面都有个精光闪闪的纯文学式样的主人公,有性格有三观,有独特的行事风格,一般不太在乎钱,但是没谈妥价绝不开工,像那种孤僻的艺术家,尊重自己的劳动,尊重自己腔子里的那股气。
以千计不是外国人,他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作为本地人,他得有自己的本地血统,也是我要注入的他独有的那口气。纯文学的父亲给予他不同寻常的性格与气质,文字的清晰度与回味之余地,无法简单定义的价值系统,以及背后支持他的广阔世界,类型文学的母亲让他有层层推进的情节,引人入胜的案件,和一些具体明朗的细节。要说,我花了很多时间在想像以千计该有的状态,他的样貌,他的行为举止,他对待他人、金钱、女人和外部世界是何种态度,特别之处在哪里,他的哀伤与软肋,他坚硬的内核与难以打败的方面,他如何带给中国小说中的男一号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中国男人普遍的软弱、迟疑和小气,如何在他身上得以克服,诸如此类。
至于语言风格,我会想联想到有如德国不锈钢的质感,那种冷与硬,那种直接、准确跟不矫情的诗意,漂浮其上的无时不刻的虚无感,简单直白,但不粗浅和浮躁,阳刚的,纯爷们的,但不是全无细腻之处。这个很难,要反复地试验,反复地调试,放弃固有的影响,放弃自己的偏见,学习,各种学习,从小说自身学习,也从其他艺术类型里边学习,我觉得甚至印象派的绘画和摇滚乐,对我都有启发,这是一个漫长的历程。
这个系列小说的技术环节其实是我更费力的地方,诸如如何让一个故事讲清楚,有层次感,推理过程充满丰富的、独特的细节。人物设置出彩,不再是农业时代和小镇的“旧人物”,而是宛如身边朋友和小朋友的新人物。对话一句顶一句,不说一句废话,对话要嘛有信息量,要嘛给说话人加分,或者体现他的内心。极少的所谓心理描写和景物描写,极少的人物容貌和衣饰刻画,干净极了,硬气极了,该舒缓的地方,也不叽歪跟抒情,豆瓣文艺腔更是时刻需要警惕的东西。
我不止一次跟我还在坚持写诗、写小说的朋友们讨论我们相要写的方向,我们会普遍认为有些题材没有必要再去碰,诸如以苦难跟艰难为起点的农村题材,诸如莫言式的农村世情题材,原因其实很简单,你不能够以当下纯文学杂志陈腐的趣味取向,去继续自己的创作。我的朋友吕约认为,当下的纯文学杂志上只能看到三种东西:农村题材、成长小说和都市的婚外恋题材,多么单调的末世场景?为之添砖加瓦简直是浪费生命。
我自己想要写真正有当代性的,中国式的硬核小说,写贴近存在现场感的诗歌,不去写让人看不懂,自己也没明白的假大空的伪先锋之作,不去装作引进的国外的文学理念,但骨子里还透着固执和土。你说,莫言先生确实学习了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然而他的世界观和价值取向依旧那么农业社会,这种文学形式和外壳上的模仿,本质上毫无意义,还有点点弱爆了。
我想,在当下要当个好诗人好小说家,首先人格需强壮,立场需独立,不做些投机的勾搭,但这都难了,愿意去好好想一想小说怎么写,跟自己较劲,抠细节的人,都难了吧。
刚才谈过美国小说家理查德.耶茨了吗?好像没有,最近因为翻译家孙仲旭的突然离世,才被大家屡屡提到孙译的理查德.耶茨的两本短篇集子《复活节大游行》和《恋爱中的骗子》,他的短篇集子还有陈新宇译的《十一种孤独》,理查德.耶茨对我的影响很大,他提供一种深刻而自然的小说写作方式,他对于诸如活着有何意义显然有自己的看法,他在小说里拒绝撒谎,直接,把生活的皮肉剥开给你看,但是用一种轻描淡写的手法,精准,确切,线条准确。
这是我自己对自己的小说理想,给予自己一个更高的要求,你说如何去刻画和剥开人性的各种层面呢?终究不是比狠,比残酷,比赛着谁更反叛,或者用诸如性乱、吸毒和暴力更可视的元素。恰恰是描写大屠杀后次日街巷飘起的雾气,洗得干干净净的地砖和人们若无其事的笑容,更像是文学要做的事情。
文学不能替代史实,不能假装哲学,文学有她的不可替代性,文字工作者乃是潜伏在生活当中沉默不语的杀手,他们必须要保持沉默的状态很多很多年,对多数事情不发表口头的演说和意见,把更多的想法写到WORD里面去,这是我的看法,你HOLD之越多,藏之越足,往内走得越深,才能够进入内在的世界,将外边的那些材料也好,人性的拼图也罢,完完整整地扔到内心的绞肉机里去,然后做出来一只新鲜的动物,它有蹄子,有角,有麟,有翅膀,它在现实世界当中是个四不像,但它会走,会吃,会思考,会飞,也会生病和死亡。
它腔子里的那口气,是你给予它的,然后它有了那口气后,你也控制不了它了。
活的文学,好像背后有无形的鼓风机在吹着它,让它膨起,形态万千,灵动而自足,放在任何时间去看,都是对的,它的恒久性就是如此,你现今看乔托的绘画,不会觉得他不好,会觉得他有时间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拙朴与厚实,是永久的美和难以毁灭的好。
而我,我们这些WORD工作者,真心里不过是追求这种美与好,美的定义多了,不能够单一定义,丑与恶亦在其中。好的定义也多了,不是众口一词的就是好,好不具备唯一的准则,好的准则甚至会有变化,跟你的意识有关,有些意识如冬眠的蛇,一直在睡,它的苏醒,跟你的人生阶段有关,经历有关,这些经历唤醒你的部分有关,也许无关。
大概如此。
巫昂,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正午的巫昂》《从亲人开始糟蹋》《春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