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陈众议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
ohistory
“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是马克思文艺思想的标识性概念。盖因文艺批评所关切的始终是内容和方法问题,即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表现、再现、反映等不同提法或取法中每每有所规约、有所偏侧。对此,前辈同人已有不少阐述,但如何结合当下、结合实际、有的放矢、由表及里,却始终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众所周知,
“莎士比亚化”是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结合,而“席勒式”则是主题先行的代名词。
这里先说情节。
一个多世纪以来,情节一度游离于严肃文学(姑妄称之),且不说生动性和丰富性。换句话说,情节的阙如曾是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即或长篇小说这种生来以故事和叙事见长的体裁也曾对情节讳莫如深,乃至给予有意的疏虞。久而久之,大作家丧失了讲小故事的能力。即使是在传统“回归”的今天,既好看又高雅的小说依然并不多见,这是不争的事实。反之,情节在几乎所有通俗文学(同样是姑妄之称)中被奉为圭臬,甚而成为当今网络小说等流行文学的主要卖点及存在方式。我这么说,并不是要重新挑起严肃和通俗之争,尽管类似的辨正无时不现、无处不在。至于不可数计的各种畅销小说中能否出现划时代的经典,则是另一个话题,难以在此展开,本人也无力独自展开。
同时,情节与主题于文学(至少于史诗、戏剧和小说)通常是一个问题的两面,相互关联。因此,它势必牵引出笔者曾经探讨的一个话题,即
情节如何由高走低,主题如何由低走高。
这在中外文学经典(尤其是小说)史上恰好表现为一种规律性反差。当然,这只是学术概括的一种方式,并不能涵盖所有文学现象及其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受众的延异和差别。换言之,文学虽然总体上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出有规律的运动;但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它又森罗万象,既不完全受制于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更非千篇一律。
一方面,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文学的确不完全受制于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以文字为介质的文学作品大都来自作为作家的个体,面对的也是作为读者的个体,因而是一种个性化的审美和认知活动,取决于一时一地作家、读者的个人理智与情感、修养与好恶等诸多因素。但无论多么特殊,文学又毕竟是一种意识形态,终究是时代、社会及个人存在的映像。从历史的角度看,世界文学(从最初的神话传说到歌谣或诗,从悲、喜剧到小说)体裁的盛衰或消长印证了这一点;以个案论,也没有哪一个作家或读者可以拽着自己的小辫离开地面。
可见,文学并非没有规律,尽管创作者每每随心所欲。为说明问题起见,本文当主要以小说和相对广义的叙事文学为例,看看情节与主题的关系。
中国小说的起源是轻松自如的故事(或谓“稗官野史”或“围炉夜话”),而事实上《左传》及《左传》以降的诸多史书也是中国小说的策源地(是谓“文史一家”),尤其是《史记》。太史公的许多章节都可以被看作美妙的段子、视作最初的小说,至少具有小说的基本因子:故事情节。诚然,由于道统对小说的轻慢,中国小说及小说史研究起步很晚。一如鲁迅所言,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且必得到20世纪),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但是,且不论《山海经》之类的神话传说,即使从唐传奇算起,中国的演义就多得很。它们不仅有史的奇谲,而且充满了耽于现实的想象和针对时世的影射。但无论如何,情节对这些演义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或可说,演义借情节的生动和有悖于正史的观念满足了受众的消遣需要、政治诉求和好奇心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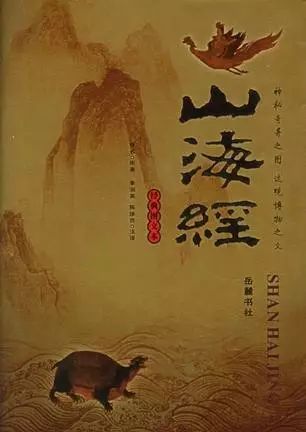
在西方,虽然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及小说史研究也是后来的事,始于晚近,如文艺复兴运动末期,但古希腊人对“类小说”如史诗、悲剧的重视早在亚里士多德时期便已露出端倪。亚里斯多德对文学(史诗、悲剧)的态度,已经体现了古希腊人对“小说”(情节)的重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情节是文学的首要因素。他甚至认为它是一切悲剧的根本和“灵魂”。他还说“情节是悲剧的目的,而目的是一切事物中最重要的”。因此,《诗学》中将近三分之一篇幅是用来阐述情节或与情节有关的。也就是说,在悲剧的六大要素中,情节位列第一。当然,情节和故事原是不同,情节或可说是经过艺术加工的故事,但绝对不是脱离故事的观念和技巧。倘以《红楼梦》为例,两者的关系显而易见。因为,我们或可视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境为故事,而家族没落、爱情悲剧或钩沉者眼里的种种影射则是其情节。诸人物的性格、形象、命运等等,在情节中逐渐演化并凸现出来,二者相辅相成。再或以《哈姆雷特》为例,故事是王子复仇,而情节几乎可以说是整部作品,其中包括人物的犹疑、梦幻,甚至“恋母情结”等等。这样,在浪漫主义之前,情节对于文学,尤其对于小说、戏剧,甚至史诗一直是首屈一指的关键元素,因而其地位十分稳固。相形之下,赤裸裸的主题和观念却是后来才逐渐显露并凸现出来的。在人文主义现实主义及其之前的文学作品中,主题是若无若有甚至深藏不露的,这也为许多经典的“说不尽”奠定了基础。荷马史诗是行吟诗人的作品,其主体意识和主题思想如此隐晦,以至于后人不得不在其归属问题上煞费脑筋。而作品中的各色人等,无论是阿伽门农、奥德修斯、阿基琉斯还是帕里斯,个个都是英雄。是非、善恶等价值判断尚非诗人(或“无我”的行吟诗人们)的主要考量。重要的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故事情节——“史传”。古希腊悲剧和古罗马神话亦如此。关于这一点,我们的先人倒似不然。他们处理史传的方式似乎比较老到。司马迁之所以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的原因,固然在其公正修史记事的抱负,但《艺文类聚》中《悲士不遇赋》所表现的悲愤和褒贬印证了他对历史及历史人物的鲜明的价值判断。
如今,主题愈来愈成为文学家首先考虑或急于张扬的要素。浪漫主义文学是较早,也较为典型的观念文学。浪漫主义把情节降格为小说内容的某个轮廓;这种轮廓可以离开任何具体作品而存在,而且可以重复使用、互相转换,可以由作者通过对人物、对话或其他因素的置换获得新生。这基本上把情节降格到了某些故事套路乃至俗套的地步。这在感伤浪漫主义尤其明显。即或如此,浪漫主义小说仍未抛弃情节。这一方面可能是惯性使然,另一方面抑或顺应了浪漫主义抒发情感、宣达观念的需要。马克思在评论席勒时,就曾称其作品为“单纯的传声筒”。相对于“席勒式”,马克思更推崇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完美融合的“莎士比亚化”。但问题是,伟大的文学又终究不仅仅是情节。关于这一点,且容稍后再说。

席勒
马克思的观点来自于他的立场和方法。他从不孤立地看问题。从文艺批评的角度看,恩格斯认为这是现实主义的基本方法,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后者关于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的辩证思想既适用于认识人类社会,也适用于观察文艺的情节与内容、内容与形式。恩格斯进而提出了典型论。屈为比附,文学中的主题和情节也有点像人类的灵魂与肉体,二者结伴而生,缺一不可,并相互作用。马克思设或赞同席勒的观点,但从艺术创作的角度看,他却并不赞赏其成为时代的“单纯的传声筒”。相反,在莎士比亚那里,情节是作品的自然条件。这是由文学的审美特性所决定的。设若文学放弃美学追求,那么它也就等同于一般的历史叙事或政治、宗教、道德说教了。退一万步说,纵使后者,高明处也往往藉文学以达到四两拨千斤的功效,即潜移默化或不动声色地使思想如盐入水、化于无形。正因为有此魅力,且颇得受众欢迎,莎氏反遭同时代作家的轻视。马克思则从历史唯物主义、从活生生的存在出发,但又不拘泥于存在本身,其所选择的莎士比亚恰好是情节和主题的最佳交汇点:文艺复兴运动鼎盛时期的文学经典。具体说来,情节和主题在莎氏笔下水乳交融,即清新的人文思想和来自欧陆,尤其是文艺复兴运动方兴未艾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故事与英国的现实需要相结合,天衣无缝地生成为美妙的艺术。但这种和谐的、水乳交融的状态迅速被日益高亢的个人主义所扬弃。先是浪漫主义,后有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夹在中间的巴尔扎克们则明显越过了父辈、投向了祖辈。这也是文学的规律之一:托古。他们对资本主义(血淋淋的现实)的批判如此自然而然,以至于模糊了创作主体(如保皇派和无产者)的界线(恩格斯称之为“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至于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是否达到了“莎士比亚化”的高度则是另一个话题,值得探讨。也许,
情节由高走低、主题由低走高,恰好在莎士比亚时代形成了最美妙的交叉,是谓人文主义现实主义。
而无论之前,还是之后,文学在情节和主题之间似乎皆有侧重、皆有偏废。

莎士比亚
且说以“科学主义”自诩的自然主义、把主题(包括人的几乎一切内涵和外延)和形式(包括技的一切可能与界限)推向极致的现代主义和反过来否定(颠覆)和怀疑(解构)一切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使观念凌驾于一切之上。这些赤裸裸的形式主义、观念主义和反观念的观念其实也是创作主体的极端外化,是资本由国家垄断走向国际垄断的必然表现。或可说,比起我们过去总结的现代主义成因种种(如科技进步与形式变化或技巧翻新、世界大战与文学宣言或先锋思潮的关系等等),跨国公司所推崇的个人主义、消费主义不是更有说服力吗?无论接受美学如何重视读者(其实这里的读者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个人),无论认知方式还是价值取向和审美作用方面毫无时代意义的通俗文学如何受到欢迎,无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审美、认知、现实意义的另类“通俗文学”(如形形色色的现实主义文学)怎样顽强地存活于我们这个世界,似乎都不能改变情节/主题的分岔及其渐行渐远的趋势。因此,曾几何时,人们似乎普遍不屑于谈论情节,而热衷于观念和技巧了。一方面,文学在形形色色的观念(有时甚至是赤裸裸的意识形态或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的驱使下愈来愈理论、愈来愈抽象、愈来愈“哲学”、愈来愈玄奥。卡夫卡、贝克特、博尔赫斯也许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而存在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高大全主义”则无疑也是观念的产物、主题先行的产物,它们可以说是随着观念和先行的主题走向了极端,即自觉地使文学与其他上层建筑联姻(至少消解了政治和文学、哲学和文学的界限)。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批评的繁荣和各种“后”理论的自话自说顺应了这种潮流。另一方面,技巧被提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到科塔萨尔的《跳房子》,西方小说基本上把可能的技巧玩了个遍。俄国形式主义、美国新批评、法国叙事学和铺天盖地的符号学与其说是应运而生的,毋宁说是推波助澜的(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0世纪上半叶西方小说的形式主义倾向)。于是,热衷于观念的几乎把小说变成了玄学。玩弄技巧的则拼命地炫技,几乎把小说变成了江湖艺人的把势。于是,人们对情节讳莫如深;于是,观念主义和形式主义相辅而行,横扫一切,仿佛小说的关键只不过是观念和形式的“新”、“奇”、“怪”,如此而已。
总之,较之于现代主义对情节的轻视(尽管有其反市场化意图),浪漫主义对情节的疏虞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经过现代主义(或者还有后现代主义)的扫荡,情节一度成了过街老鼠,以至于20世纪的诸多文学词典和百科全书都有意无意地排斥情节、轻视情节,把情节当作可有可无的文学“盲肠”。于是,观念主义和形式主义在小说创作中大行其道。于是,20世纪的许多小说仿佛专为评论家而写,成了脱离广大读者的迷宫与璇玑。
至于反向存在的通俗文学,则大抵顺应了文化消费主义趋势,譬如托尔金们、金庸们的故弄玄虚,又或好莱坞、宝莱坞和琼瑶们的缠绵悱恻甚至那些廉价地博取观众眼泪的电视连续剧和跌宕起伏、无所不用其极,却又一泻千里、如黑洞化吸的网络小说。而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只能在娱乐至上和主题-观念-机巧先行的夹缝中勉强生存。
然而,这仅仅是一种概括方式,盖因文学终究是复杂的,它是人类复杂本性的最佳表征。就拿貌似简单的“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个命题来说,我们所能看到的竟也是一个复杂的悖论,就像科学是一个悖论一样。比方说,文学可以改造灵魂,科学可以改造自然。但文学改造灵魂的前提和结果始终是人类的毛病、人性的弱点;同样,科学改造自然的前因和后果永远是自然的压迫、自然的报复。因此,无论文学还是科学,都是自相矛盾的,是人类矛盾本质的鲜明体现。惟其如此,人类也便更加需要文学、需要科学。恶性良性且不论,这是一种无法抑制的循环。问题是科学每每主动出击,而文学似乎越来越陷于被动。即或20世纪的某些观念主义和形式主义具有明显的反技术理性和反消费主义倾向,也终究在科技和资本合谋的消费主义大潮中下败下阵来。
首先,
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文学也终究是时代社会的一面有色的、变形的镜子。
20世纪的热战和冷战、社会生活的日新月异和科学技术的一日千里无不为观念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甚嚣尘上提供了土壤。但所有这些又终究不能成为文学脱离情节、脱离生活、脱离读者的全部理由。事实上,侦探小说和形形色色的现实主义文学的经久不衰一定程度上不仅有其合理性,而且多少也是对观念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一种反动。后者对人性和文学的某些共性与差异、清朗与晦暗的揭示,同样为时代建立了富有启发的认知方式和价值体系。只不过面对个人主义、物质主义和技术理性的极端膨胀,这些认知方式和价值体系无法被大多数人觉察并成为其生活的借镜。同样,新亚里斯多德主义者(如芝加哥批评派的R.克莱恩)曾不遗余力地呼吁文学关注情节,遗憾的是其声音如此微弱,以至于基本上没有引起任何反响。正所谓滔滔者天下皆是,倒是那些专靠炒作吃饭的机构、人等,一味地(或可说是顺时趋势地)把那些带有明显个人主义表演特征的作品变成了“经典”、“大作”和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产业”。于是,乔伊斯们(同时还有毕加索们)成了炙手可热的商品。这是另一个话题。
其次,问题一直存在并逐渐浮出了水面。譬如,英国作家斯蒂文森早在19世纪末就曾扬言小说行将消亡,其依据便是“故事的枯竭”。斯蒂文森认为时至斯日,引人入胜的“故事已经枯竭”。类似慨叹一直经莫拉维亚等人延续至今。20世纪的情节危机多少印证了他们的担忧,而他们的担忧也为20世纪小说的反情节倾向提供了绝妙的依据。换言之,也许正因为“故事的枯竭”(“阳光下没有新鲜事物”),小说才不得不改变方向去拥抱形形色色的观念和技巧。
及至世纪之交,小说在一片“回归”声中重新出发。需要说明的是,历史的回归永远不是简单的重复。就像一个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对情节的重视,我相信只不过是20世纪小说矫枉过正之后的一种回转。这里既有物极必反,也有小说重新找回读者的诉求,或者源自“通俗文学”的反作用力也未可知。于是,阳光下皆是新鲜事物。
但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以加速度变化的生活和缺乏高度的艺术概括能力的矛盾。用习近平同志的话说,面对崭新的生活之树,作家“既要像小鸟一样在每个枝丫上跳跃鸣叫,也要像雄鹰一样从高空翱翔俯视。中国不乏生动的故事,关键要有讲好故事的能力;中国不乏史诗般的实践,关键要有创作史诗的雄心”。此话适用于世界文学,盖因文学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而它们又无不与情节和主题、内容和形式等紧密关联。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文艺无论多么特殊,它终究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然而,文化消费主义正使脱离生活的“空手道”甚嚣尘上,以至于关于生活或文学的“戏说”、“大话”和不着边际的观念技巧、奇情异想泛滥成灾,从而割裂了文学与社会生活的血脉关联,抛弃了文艺承载良知、引领风尚的崇高使命和优良传统。
鉴于无法涵括浩如烟海的国内外文学,甚至无法窥其冰山一角,我只能谦卑地拿比较熟识的作家作品为例,聊以自表。许是身在此山中,又难以“会当凌绝顶”,我又实在想不出当今中外文坛有哪个作家“莎士比亚化”了。除了本人的局限,造成“莎士比亚化”阙如的客观原因更是不胜枚举。譬如资本和市场经济、技术理性和消费主义,它们的空前膨胀肯定是探讨一切现实问题的基础。
文学固是现实的组成部分,但在资本和市场面前,它不是顺之应之,便似折羽之鸟丧失了巧妙地俯瞰现实、改变现实的能力。
譬如“零度写作”和形形色色的“元文学”。它们何尝不是现当代外国文学观念化和形式主义化的产物?在这方面,博尔赫斯称得上是大师。国内读者,甚至不少同行拿“作家们的作家”对他顶礼膜拜。而事实上,所谓
“作家们的作家”原是拉美左翼作家对他的批评,并不指他高于别的作家、是作家们的导师;恰恰相反,那是对他脱离生活、面壁虚设、从书本到书本、从作家到作家的一种诘责。
的确,他的作品每每从另一遥远的作品切入,再形而上地演化出似新非新的意象,如迷宫、悖论等等,并大都取法抽象和思辨。
无独有偶,2006年荣膺全美评论家奖的波拉尼奥(这是该奖第一次破例授予一个已故作家)在西语文学的一片“回归”声中反向地接过了博尔赫斯的衣钵。他生前一直否认自己是智利裔墨西哥人,并素以国际作家自居。同时,他在代表作《2666》(2004)中演示了什么叫关于写作的写作。他虚构了一个被“评论家”(“作家的跟屁虫”)们杜撰的文坛巨匠,并由此生发,大谈文学(或文学语言):从走火入魔般的文学想象到冷冰冰的新闻报道,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但这显然是一个新的神话。它的“横空出世”貌似偶然,却十分必然——有资本的推动。当然,波拉尼奥并非一无是处,譬如博尔赫斯们或者更为遥远的席勒们,他们的存在为我们提供了文学的另一种维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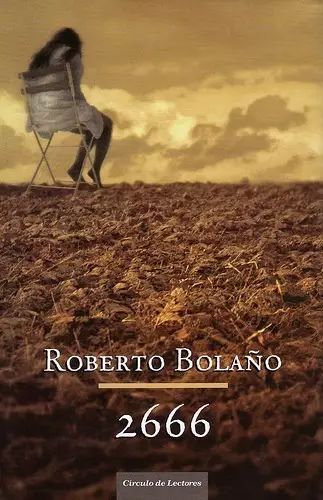
又譬如与之不同或谓相反的是丹•布朗和拉尔森们的唯情节论。几年前,前者的《失落的秘符》和后者的《龙纹身的女孩》以惊人的印数,像一颗彗星划过被金融风暴阴霾笼罩的天空;对于日趋迷糊的图书市场,则犹如一座航标,适尽其用。然而,其成功的秘诀也许惟有情节,却丧失了时代稀缺的人文精神。
且说丹·布朗将西方文学的畅销要素玩弄于股掌之间。从《数字城堡》到《天使与魔鬼》再到《达·芬奇密码》,作者炫示了各种“秘符”,而《失落的秘符》又使它们悉数登场:神秘加谋杀加惊悚加悬念加秘密社团及神秘符号,还有不可或缺的美女搭档、神秘摸测的敌人和险象环生的情景、分镜头式的描写和层层递进的情节,等等。不仅如此,《失落的秘符》称得上是一座美轮美奂的符号迷宫。秘密的主要持守者是彼得·所罗门,他的姓名便是一个典型的符号。彼得让人联想到基督的大使徒圣彼得。圣彼得原名西门,彼得是基督对他的指称,在拉丁文中意曰石头,这和小说的秘密之所在——金字塔相关联。而所谓失落的秘符比《达·芬奇密码》中的“倒金字塔”(“圣杯”)更玄奥,盖因它源自是一个古老的理念:“赞美上帝”。这个西方犹太-基督教文化核心理念的“重新发现”将一切回溯到《圣经》本身,并与现代物质文明构成了反差。而故事中的主要人物作为“意念学家”,其研究成果似乎恰好与这一发现不谋而合。反之,凶手殚精竭虑、无所不用其极的追寻结果,却是找死,即“怎样死去”。从作品本身看,丹·布朗的演绎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是继承中世纪基督教玄幻文学、骑士传说及哥特式小说的某些传统,同时将现代侦探推理小说杂糅其间;其二是大善大恶的人物和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的情节;其三是对犹太-基督教文化核心内容的诠释,尤其是对犹太-基督教文化谱系中的神秘主义传统的细致入微的梳理;其四是在犹太神秘主义的周围结集了大量可资参照的神秘主义或类神秘主义文化现象,如古印度奥义、中国易学、炼金术、占星术、纹章学、塔罗牌及中世纪以降的各种神秘修会、西法底文化中的某些神秘社团等等,却独不提伊斯兰苏菲神秘主义。而以上记点恰似“全球化”背景下NBA招揽世界球员,其商业动机不言而喻。
至于拉尔森,其在三部曲中所有意无意推行的也是唯情节论。其中,“龙文身女”以牙还牙、以恶惩恶的方式服从于原始冲动,显然既没有任何典型性,也不为现代伦理所容。但正因为如此,阅读它,使不少读者产生了某种邪恶的快感。比如沙兰德对性虐狂毕尔曼的报复,又比如她对大财阀温纳斯壮的釜底抽薪等等,犹如醍醐灌顶,让人血脉偾张。与此相对应,小说意欲打破类型界限的努力可谓显而易见。作品固然提到了古代西方玄幻文学中经常出现的塔罗牌、星象术等,却没有因循哥特式小说、中世纪传奇和神秘主义的匪夷所思,更没有明显模仿哪种现代类型小说的痕迹。正因为如此,迄今为止,还没有第二个作家能像他这样将传统畅销要素推到化境或极致。托尔金没有做到,J.K.罗琳没有做到,丹•布朗无疑也没有做到。现代类型作家柯南道尔、普佐、克里斯蒂、希区柯克等等,更没有哪一位达到拉尔森的复杂程度。于是,婚外恋、女同志、双性恋、性虐待、性报复,外加司法、媒体、骇客,乃至乱伦、密室、欺诈、谋杀,再加上各种现代指涉,如网络犯罪、新嬉皮士、“9·11”、闪电式情爱等等,小说简直是现代文明要素及其矛盾的大杂烩,而且烩得不动声色,其麻辣程度更是难有望其向背者。
这些无不让人想起我国网络文学中此起彼伏的新玄幻、新志怪、新恐怖、新宫闱,以及穿越、复仇、盗墓、僵尸等夺人眼球的诸多写法。一时间文艺市场化、娱乐化及闭门造车、面书虚构成为时尚;一些文艺工作者或热衷于天马行空、装腔作势的张冠李戴、胡编乱造,或沉溺于鸡毛蒜皮、哼哼唧唧的矫揉造作、无病呻吟。有些媒体则推波助澜,乐此不疲,以至于窥隐癖、窥私癖恬不知耻地招摇过市,“八卦”、“花边”如癞婆娘的裹脚布又长又臭;各种炒作及评奖、排名更是名目繁多、令人瞠目。
诚然,碍于我国网络小说的无比芜杂和纸质长篇小说的惊人产量,我不妨以2016年“最佳中篇小说”为例权作比附。在被有关评论家、出版人推定的六个年度最佳中篇小说中,大抵可分为两类,一类以写实取胜,二类以机巧见长。所谓写实,本无须多言,但似乎又不得不言。因为,大处着眼,真实至少有两种:一谓社会的真实、生活的真实,二谓作家的真实、心理的真实。前者是生活的照影,亦有作家攫取生活的角度和方式;后者是作家的自我表现,方法自然也随心随性。二者相辅相成,但未必等量齐观、划一齐整。因此,这种真实是双重的,有时你很难界定是作家描写的背景更真实呢,还是他攫取的角度或表现的心性更真实;但有些作品却无须界定,譬如夏榆的《像野蜂蜜一样自由》,或者孙频的《东山宴》,又或者盛可以的《福地》。这三部作品的共同特点便是真实的沉重。由于过分沉重,我们会忘却作者的角度,而去更多地关注“生活”本身。先说沉重。它当然不是用页码或字符多寡来衡量的。《像野蜂蜜一样自由》,题目相当“轻飘”,因为它来自俄国白银时代诗人阿赫玛托娃的诗歌《野蜂蜜闻起来像自由》。但是,小说负载了“北漂”者的哀痛。那是一个群体的哀痛,但也是一对姐妹花的哀痛。《东山宴》是一篇奇谲的小说,写吕梁山山沟里一个叫做水暖村的“原始部落”。我之所以称之为“原始”(当然要加引号),是因为内心深处确实掠过了几丝原始的悲凉。它仿佛一股来自远古的寒风,带着腐朽和恐怖。类似的悲凉,我在第一次读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时感受到了,早年读鲁尔福和马尔克斯的作品时也感受到了。《福地》可能是最可诤的一篇小说。它矛头直指社会腐败。作品从一个智障流浪女的视角,叙述某地下代孕基地的可怕景观。从叙事方式看,《像野蜂蜜一样自由》似乎有意先虚晃一枪,然后由浪漫进入残酷。《东山宴》从一个腐朽习俗讲起,旋即顺势而下,进入阿鼻地狱。《福地》看似平铺直叙,但很快从容地进入了地下世界的“混沌”。这是大处着眼的取法,他们之间的不同却是更多,在此恕不一一罗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