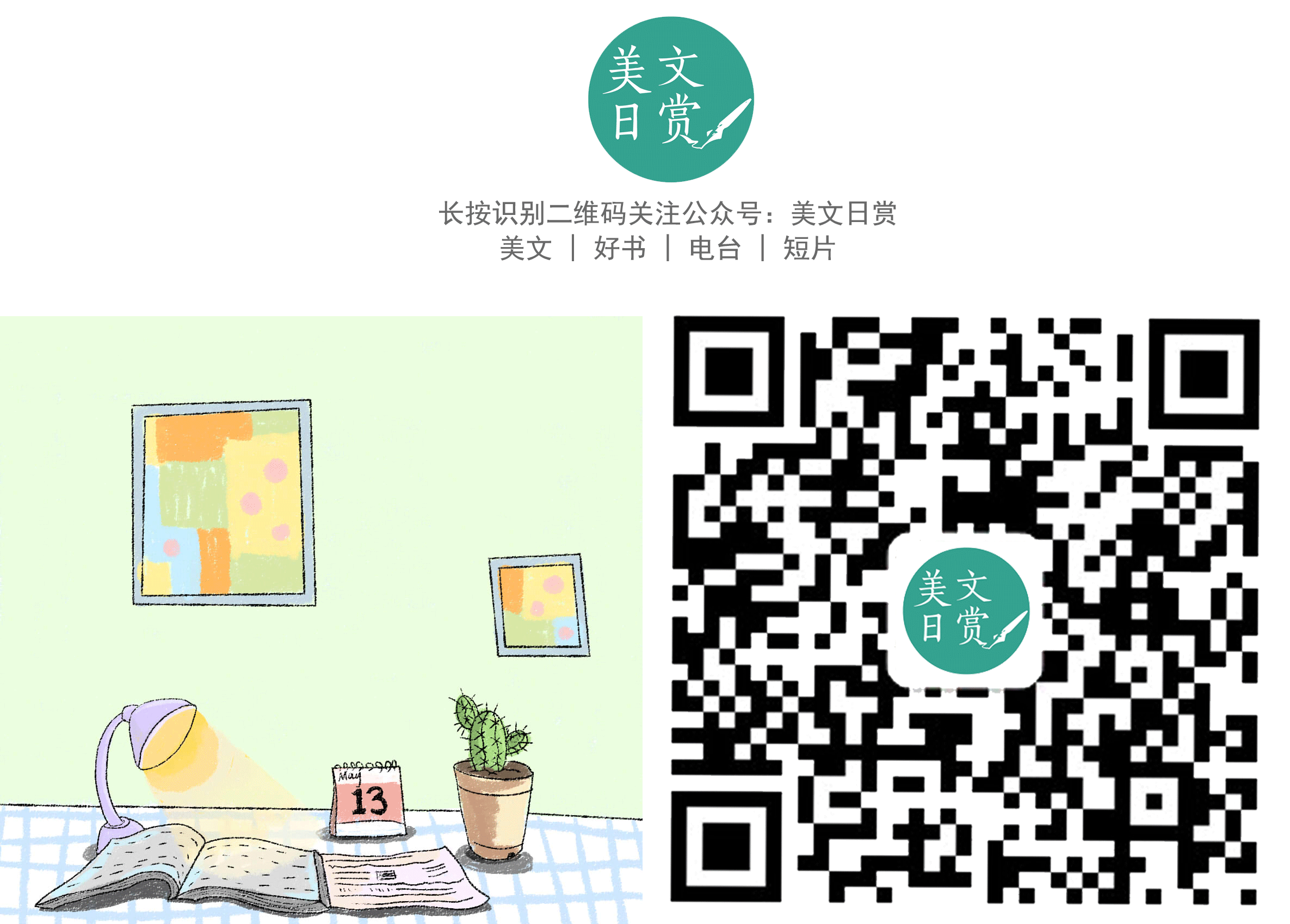文 绒绒
十多年前我跟王乌云打过无数个赌。
似乎每段应该好好享受青春的时光里,我和王乌云都在用打赌来打发时间。我们赌历史老师一节课会讲几个笑话给我们,我们赌前座的胖子早上吃的是韭菜盒子还是韭菜包子,我们赌下一节的体育课会突然变成外语还是数学课。
王乌云的头脑不够发达,她不认识历史课本中戴官帽留八字胡的那些胖官员,也不懂得为什么那么多数学习题要千方百计来证明结果等于零。
一个人不够聪明,所以会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是麻烦。
王乌云功课很烂,她讨厌每一个在讲台上滔滔不绝讲上四十五分钟的老师。
好在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王乌云唯独不讨厌面相好的历史老师。
我们的历史老师是一位从俄罗斯留学回来的大男孩。他应该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大四岁还是五岁。他喜欢穿着一件浅绿色的衬衫,留着清爽的短发,说话的声音像从留声机里传出来的一样性感又有磁性。
王乌云踏着铃声冲到历史老师身旁,踮起脚在他的耳边嘀咕了几句话,历史老师忽然笑了,想要拍王乌云的头,手在空气中停留了半天,胡乱抓了抓后脑勺。
王乌云一下子豁然,迈着轻盈的步伐朝我走来。她越走越轻,好像天空中的乌云一样快要飘起来了。
以王乌云为中心,方圆十里的人都认识她。她牙尖嘴利,嗓门极大,生气的时候眼睛瞪得很大,好像要把所有惹她厌烦的人物吞到肚子里去。
早上的时候,人们跟王乌云打招呼。
王乌云心情好,扒拉着头发,跟每个人都回一句:“早噢。”
晚上下了课,人们肩并肩,挤在各自回家的路上,有人提着菜去做饭,有人抱着球去运动。没有人有多余的时间来去理王乌云。
王乌云踢一块石头,踢老远。
石头蹦到自在飞奔的自行车轮上,人从车上跳下来,骂道:“哪个混蛋扔的石头?”
王乌云一扯书包带,脚底一溜烟,跑了。
王乌云有一头长发,她十分溺爱她的头发,每天早晨比我们早起半个小时洗头发、涂营养素、梳头发。到教室上早读课的时候,长发还没干,王乌云披着湿淋淋的头发,水珠滴答滴答地落到椅子上。她搭一本书在课桌上,脑袋顶着书本,龇牙咧嘴撕咬着一块韭菜盒子。
我很好奇,像男孩子一样生长的王乌云为什么还要留一头长发。每次我这样问,王乌云就把头发拢起来,一丝不苟地绑在后脑勺,抬起手把头发从后面抓到胸前,尽情抖着她的乌黑浓密、像瀑布一样的长头发。
王乌云矜持一笑:“我不告诉你。”
其实“矜持”两个字本应该和王乌云丝毫扯不上关系。王乌云可以大声地说出来她的三围尺寸,也可以倚在教室的门口冲我喊:“刚刚粪便排了一公斤。”
这时候如果坐在最前座的胖子发起抗议:“王乌云,你太三俗了。”
王乌云马上跳过来,扒开胖子的校服,揪着他的胸部:“谁三俗?谁三俗?这么大,是不是自己摸的?”
胖子不敢出声,也没人敢出声。
有王乌云存在的地方,世界都是属于她的。她好像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做,并且做起来毫无顾虑、勇往直前。
王乌云学习成绩不好,但总有一堆大道理。她说勇往直前就是青春应该拥有的模样。
不用管明天是下雨还是闪电,不需要理会下一秒涨价的是柴米还是油盐,人生总应该有这样的一些时间,想笑就大声笑,想哭就放声哭。
青春是一场没有预告的电影,你永远不会猜到它的过程是平淡还是离奇,是眼泪还是欢笑,有鲜花还是风雪。你也永远不会猜到,那个电影中似曾相识的主人公会不会挑选一条好看的领结扎起来,在结束的时候拉起你的手一同谢幕。
在王乌云的电影里,她自导自演了很多戏码。
王乌云攒了很多钱,买了各种各样的明星贴纸发给班里的女同学。收了贿赂的女生会在历史课结束以后疯狂地跑上讲台,把历史老师团团围起来,缠着他讲在俄罗斯留学时候的事情。
王乌云在座位上只需要轻轻咳嗽一声,挡住她视线的女同学会很识相地扎个马步,留出一张完整的历史老师的脸给她慢慢欣赏。
历史老师说话的声音十分动听。
不管他讲李白还是工业革命,王乌云可以不听内容,但对声音一定竖着耳朵邀请它走进来。
历史老师被缠着讲了很多趣事。他讲去俄罗斯读书的时候,皮箱里不装书不装衣服,塞满碎花雨伞。俄罗斯的轻工业不发达,那里的手帕和雨伞,在姑娘面前比长得好看的男明星还要受欢迎。
雨伞占据了整只箱子,开始可以装几十把。后来生意火得姑娘们因为抢伞直打架,他就换了大个儿的箱子,再多装上几把。
受冷落的书和衣服被打包好,要坐着下一列火车翻过山越过岭,拼命地被押运到他身边。不过那已经是半个月以后的事了。
所以没有书读的日子,我们的历史老师和他几个同学在清冷的俄罗斯街头铺一张红布绸子,碎花伞还没摆完,腰包已经塞得满满装不下了。
王乌云知道历史老师喜欢打篮球。
于是她在课堂上最期待的事情就是班级调整座位。我们班每周一次大调整,前后左右地调,复杂又规律,一个学期下来几乎每个学生都能把所有的座位坐上一遍。
即便这样,仍然有人近视,有人斜视,有人摘了眼镜把脸快贴到书上了也看不清东西。
王乌云掐着手指,还有三周就可以换到靠窗的位置了,还有两周就换到靠窗的位置了……
等待的日子总是被拉得长了又长。
王乌云终于可以坐到靠窗的座位了,她常常托着腮帮,神情专注地搜索操场上奔跑的身影,那个穿白色T恤和青灰色长裤跳起来投篮的人,那个曾经翘了课去俄罗斯街头卖碎花伞的人,那个讲起历史像讲故事一样生动的人……
就是王乌云自导自演的电影中的男一号。
是王乌云所有的青春。
后来王乌云认真听了好几节语文课,写了一封情书。我和胖子都不敢猜测那究竟是怎样的一封情书。
我问王乌云:“你识字吗?”
王乌云连鞋都不脱,脚底带着水和泥就来踹我的屁股。
胖子不敢问,更不敢违抗王乌云的指令,去把情书送给历史老师。他走的时候像领了尚方宝剑一样,沉重的剑柄握在手里,走路时“扑通扑通”,好像下一脚就会踩碎地板掉到楼下去。
我们看着胖子宽厚的背影,王乌云摇摇头:“他是我见过的最胖的人。”
我也摇摇头:“他是我见过最听你话的人。”
那个阳光正好的午后,我们趴在窗子口偷看。
历史老师穿了一套湖蓝色的运动装,一个又高又瘦的人把球传给他,他接过球,运着球转了个身,躲过了三个试图夺走球的人,起身跳起来把球投出去。球打到篮筐上,弹到了对方的手里。
他立了几秒钟,抓了抓自己被汗水浸透的头发。
王乌云“唉”了一声,瞬间泄了气,耷拉着肩膀和耳朵,托着腮帮子惋惜。
“不过,这画面真美好啊。”王乌云说。
没过一会儿,我们看见胖子一晃一晃地走到了这幅美好的画面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连比画带说地在历史老师跟前忙活大半天。
王乌云抻长了脖子竖起了耳朵,就快把脑袋揪下来当成篮球滚到操场上去偷听了。
我问她:“听到了吗?”
王乌云说:“嗯,没听到。”
胖子回来的时候满头满身全是汗。王乌云从窗口递给胖子一瓶自己喝过的水,胖子站在走廊里,呆了几秒钟,拧开瓶盖把水倒在自己的头上。水珠顺着胖子的头发流过他的脸,流过他被汗水浸湿的白色T恤衫,流到他宽大的短裤上,滴答滴答,落到地板上。
我被吓坏了:“胖子,你干吗呢?”
王乌云也有她关心的事情:“历史老师说什么了没?”
胖子笑眯眯回答了我的问题:“热。”
我和王乌云等待着一个结果。
等着青春的电影放映结束,有人登台谢幕,更多的人曲终人散,海角天涯,各自为安。我们不知道在这过程中我们所追求的是对还是错,不知道结果是不是我们想要的那个样子。
只是在这种勇敢又胆小的年纪不做点什么,怎么对得起稍纵即逝的青春。
夏天的夜晚,透过篮球筐往天上看,没有月亮,星星很美。王乌云仰着脸披散着湿淋淋的头发,思考她乱七八糟的心事。
我问王乌云:“你给老师的情书里,都写了什么?”
王乌云说:“我写……青春很麻烦。”
那一年,破旧的影院里上映《十面埋伏》,胖子从家里偷了50块钱,请我和王乌云去看电影。一张票20,三张票60。
我们三个人凑了好久,也凑不出来另外的10块钱。胖子很识相地买了两张电影票,给王乌云买了一桶爆米花。
电影里刘捕头因爱生恨而把小妹杀掉的场景,把王乌云给看哭了。她嘴里塞满了爆米花,张大嘴巴哭,眼泪流到嘴里和着爆米花的香甜味道一起被她咽下去。
周围的人看过来。
我说:“王乌云,你别哭了。”
王乌云哭得更大声了。
走出电影院的时候,王乌云还没从悲伤中走出来。她说:“是不是想谈一场恋爱就是这么难?现在也是,古时候也是。你看刘捕头爱小妹爱得多热烈。”
我笑王乌云电影和现实都分不清:“你爸和你妈不是挺容易嘛!”
王乌云摊开手:“我妈说她不爱我爸。”
王乌云抹掉眼泪,逼我答应请她吃韩国料理,而她作为回报给我讲她爸妈无关爱情的故事。
20世纪80年代,她爸是集乡村教师、校长、教导主任于一身的美男子。班里什么样的学生都有,从一年级到六年级,从七八岁到二十几岁。
她妈是年纪最大的那个学生,永远羞怯地坐在班级里最后一排。
据说本来村里的教师标配是两个,因为实在找不到一个认字又愿意干教师的人,另外一个教师名额就常年空着。
后来上面来视查,乌云爸就抓来乌云妈顶替老师。因为她已经读到六年级的内容了,算是认字最多的。
再说也找不出来别人了。
等视查的人走了以后,王乌云她妈找到她爸,说:“干脆就让我当老师吧,你教我,我学会了教别人。”
王乌云她爸犹豫了一会儿,说:“那你干脆给我当媳妇吧,我一天二十四小时教你。”
乌云妈没说不答应。
后来,她妈一直觉得有些后悔,自己的婚姻像一桩买卖似的。
我们穿过狭窄的长廊,看到售票台外面胖子躺在一排三座的塑料椅上睡得汗流浃背,胸脯一起一伏,打着呼噜。
我提醒王乌云:“这不比打篮球的场景好看吗?”
王乌云把吃完的爆米花桶罩到胖子脸上,使劲拍他丰满的胸脯:“真麻烦,起来了!”
我们去的那家韩式料理店的老板娘很凶。传说是老板从朝鲜边境买回来的媳妇,在家里表现得很贤惠,会热情地跪在地上捧住老板的脚,脱去他的鞋袜,给他打上满满一盆洗脚水。
其实她是厌倦了这种生活,所以把对老板的怨气通通撒到客人身上。
我和王乌云从小就来这里吃,老板娘做的烤牛肉是一绝。端上来的时候还发着吱吱的声响,口感外焦里嫩,王乌云说像小的时候外婆给炸的年糕。
胖子对我说:“你白给王乌云吃肉了,都吃出年糕味了。”
那一天天气很热,盛牛肉的铁板不断地把热气吹到我们脸上。我和王乌云龇着牙咬着肉,一边擦汗一边流鼻涕。
王乌云把肉吞到肚子里,气急败坏地叫胖子给她拿纸巾。
后来一双干净又好看的手把纸巾塞到王乌云手里,王乌云一抬头,鼻涕从鼻孔里流出来,被她狠狠地吸回去,顺着鼻腔流回嗓子里。
我们的历史老师,牵着一个女孩从料理店的一角钻出来了。
我和胖子都暂停了呼吸,不敢说话。
那个女孩的个子很高,大概有一米七的样子,长长的头发像森林里拥有神秘力量的瀑布,好看得不得了。
我们看见那个女孩转过身,柔顺的头发甩起来,历史老师温柔地摸了摸她的发尾。
王乌云噌地站起来,声音乱颤,好像舌头打了结:“老师,你把信还给我。”
历史老师问她:“什么信?”
那真是很窘迫的一个中午。王乌云吃了很多盘肉,好像流到铁板上的眼泪稀释了酱汁,明明很好吃的牛肉吃起来却无比酸涩。
胖子一直低着头,不敢看王乌云的眼睛。
我想,如果目光可以化作一把利剑的话,胖子已经可以用“英年早逝”来解释他的一生了。
我和王乌云都不知道胖子为什么没有把信交到历史老师手里,也不知道那天我们趴在窗口见到胖子递给历史老师的纸上写了什么。
胖子没说,王乌云也没问。走出料理店,胖子像往常那样,尾随着王乌云沿着一条永远走不完的街道走着,不知道前方是哪里,不知道有没有尽头。
胖子宽厚的背完全把王乌云遮了起来,把她深深地藏了起来。
其实离开料理店的那一天,我看见老板娘端着托盘来收拾我们一桌子的残羹,老板快走两步,抢先在她下手前夺下了托盘。
他弯着腰不停地挪动着抹布,她立刻到一旁擦着汗水发笑。
那笑,不是装出来的。
是谁说过北方的夏天要比南方好过一些?我真得要好好跟他辩论一场。
我会告诉他,那个夏天真的酷热难当。空气里面都偷偷躲着一颗颗小太阳,晒得我们焦躁不安,像气球一样膨胀,像焰火一样快燃烧起来了。
因为这样,王乌云剪了很短的短发,我分不清是三厘米还是五厘米长。她趴在桌上睡觉的时候,头发压在胳臂上,一抬头翘起一撮,孤傲地挺立着。
我以为王乌云生胖子的气会生很久,可是没过一个星期她就原谅胖子了。
我以为王乌云再也不会听历史课了,可是她好像听得更起劲了。
整个高三那一年,王乌云都像打了鸡血一样,对每一门功课都很卖力地听。我和胖子也受到了鼓舞,跟着王乌云做起了努力的好学生。
在一本本没有答案的习题本上,我不知道是王乌云做对了,还是我和胖子做对了。
或者我们都没有做对。
青春期的我们都有一种力量,对自己喜欢的人和事念念不忘。直到十几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把我们的青春岁月从记忆里挖出来,我们想与那时候的青涩和倔强握手言和,与那时候的幼稚和不够担当互道再见。
可是我们打算这样做的时候,发现即使那个时候那么不懂事与不成熟,回头想想我们走过的这段时光,我们还是最喜欢那个时候的自己。
那个时候我们喜欢就说喜欢,难过就说难过,开心的时候就笑,痛苦的时候就哭,每一个表情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每走一步都是我们想要去的方向。
那个时候我们喜欢一个人,尚且懂得不是占有,而是把自己变成一个更美好、配得起他的人。
高考前的一段时间,王乌云写给历史老师的情书被曝光了。一个面目可憎的男同学把它从胖子书桌里偷出来,大声地朗读给班里的每一位同学。
结果很不尽如人意,胖子痛扁了那位同学的同时被揍进医院,历史老师被停课。
我和王乌云半夜偷偷去看胖子的时候,他的右眼已经肿得看不见东西了。
我们带了很凶的老板娘家的烤牛肉,胖子吃得很大声,酱汁滴到洁白的床单上形成一道难看的污渍。
王乌云塞给胖子一张纸巾,骂道:“被人揍完了就更胖了,像一头猪。”
护士小姐看见胖子鼓鼓的腮帮,跑过来制止我们。
王乌云拉起我从窗口跳出去,我们听见护士小姐在冲胖子喊:“肿成这样还吃牛肉,是不是不想好了?”
我们应该感谢胖子住的病房是在一楼,跳下去的时候我们踩到了一块湿软的草坪。我们应该感谢青春够漫长,纵身起跑的我们奋力追逐,追逐自己的梦想与人生,不管什么时候都还来得及。
后来王乌云去教导处大闹了一场。
我们不知道她是怎么闹的,总之教导主任同意胖子可以带伤参加高考,历史老师也可以回来上课了。王乌云从教导处回来的时候,面红耳赤,意气风发,像一只从战场回来的斗鸡。
我问王乌云是怎么办到的。
王乌云告诉我,教导主任命令她写一份深刻的检讨,在全校面前读出来。
做检讨那一天,王乌云故意把头发梳得很整齐。我和胖子挤在广播室门口,看到王乌云的手和脚都在发抖。
我想冲进去,胖子拉住我:“王乌云,她行的。”
王乌云回头看了我和胖子一眼,冲着我做了一个夸张的口型。她在说:“其实我妈很爱我爸。”
然后王乌云大声地检讨起来:
大家好,我是三年级二班王乌云。
我想跟大家说对不起。
对不起我的历史老师,他没有错。
我也对不起我的同学胖子,他也没有错。
其实我想说,没有人是错的。
因为青春,无论我们犯了多少错,它都会原谅我们。
我们的青春,它就好像一场电影。我们看起来好像是默默无闻的配角,因为所有人看起来都比我们漂亮,所有人看起来都比我们活得精彩。
我们是那么胆小又彷徨,害怕走错了一步,青春就这样没了。
我们怕谢幕时的鲜花和掌声和我们没有关系,怕拉上幕布的瞬间才后悔没有演好自己。
可是,总有一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自己曾经走过的路,那个怯懦的无知的自己,那个单纯无害的自己,那个从来不会对自己和别人说谎的自己,虽然没有变成主角,但这就是我们的青春,有欢笑有泪水的青春。
那个夏天,真的好热。年轻又胆小的我们好像要被烤干了。
在那么火热的天气里,我们带着一点恐惧与希望走进考场。我们很卖力地写,咬着笔锁着眉头思考一个很难的问题。
我们想要写好每一个字,想要解答好每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每一个表情与动作都成全了我们的未来,都是我们自己上演的青春。
烤肉店的老板娘明明很爱那个头发已经半秃、露着胖胖的肚皮会冲所有人微笑的老板。她给他擦汗的时候,用了刚好的力道,不轻也不重,两个人笑起来,弧度都是相同的。王乌云的妈妈明明很享受这一场买卖般的婚姻。每当夏天很热的时候,她都会冰一只又大又圆的西瓜,一刀切成两块,挖出中间最甜最脆的部分放到乌云爸爸嘴里。
他们被人误会了青春,被人误会了人生中很多重要的东西,比如相亲相爱。
只是这场无关紧要的误会都是我们看客自娱自乐的消遣罢了。
那个夏天,胖子的眼睛消肿了很多,汗水把纱布都浸透了,他还知道把背包里的铅笔拿出来看看有没有削好。
王乌云伸着手臂摩拳擦掌,问我要不要再打一个赌。
我问她:“赌什么?”
王乌云说:“就赌总有一天我们全部会变成主角,难过了就哭,开心了就笑,走着我们自己选择的路,过着我们想要的人生。”


《我曾悄无声息爱过你》是one一个人气女作家绒绒的全新青春治愈小说集。这里有为吉他远走的少年、有我最爱的同学王乌云、有楼下摆摊卖袜子的神秘大叔,12个关于生命中那些悄无声息的爱情故事,9段让人潸然泪下的真实青春讲述,或许这些故事并不够神秘和完美,但这就是我们每个人曾经历过的暗恋和青春啊。

绒绒:
二更食堂、One一个app高人气女作家,爱做白日梦的空想症晚期患者,也曾披荆斩棘对抗生活的非十八岁少女。全新青春治愈系小说集《我曾悄无声息爱过你》倾情上市。新浪微博:@小绒绒往前走 微信公众号:绒绒和她的故事(cecaa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