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景锋或许是一个不会“复制”自己的摄影师。在他的影像作品里,有经过精心编辑的家族老照片、泛黄的出生证明,有服务家族37年保姆颜姐的翠色耳环,也有被腐蚀或布满划痕的胶卷负片。从追溯家族历史源流的《女王、主席和我》、广为传播的自梳女项目《寻找冰玉堂》,到研究中国当代祭祀用品的《假如天堂会下雨》,再到探寻自我身份认同的《唐水黄土》,在艺术呈现上,每个项目间都存在显著差异,却都不同程度地指向了中华文化的土壤。
唐景锋擅长从家族亲友的故事中寻找灵感,探讨自己对母国微妙而复杂的情感。这位出生于1977年的摄影师,成长于香港,13岁赴英读书,并在他乡成家立业。当第一个女儿出生后,唐景锋开始思考如何向女儿传授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并由此开始反思自己身份认同。在其项目《唐水黄土》中,唐景锋借由摄影探寻人类灵魂三问“我是谁、从哪来、到哪去”,并由此重新认识了自己父母家族的长辈,以及他们在时代境遇下的人生选择。
唐景锋父亲一方的家族职业与海洋有很强关联,如渔民、水手等,是为“唐水”;而母亲所属的黄姓家族则根植于陆地,如地主、建筑商等,则为“黄水”。然而,因为“唐” “黄”是作为姓氏而存在,在给项目翻译英文名时,唐景锋则采用了“Sweet Water, Bitter Earth”来对应自己寻根之旅中的悲欣交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组作品中散落着一些被海水侵蚀染色、被土壤磨损的负片,这些不完美的照片,则是唐景锋对于自身身份认同的一种隐喻——对于故土所兼具的亲近与疏离感。唐景锋的部分作品和摄影画册已于影像上海艺术博览会展出,在展览会前夕,湃客与唐景锋进行了一次交流,以下问答经过翻译和删减。
眼光:生长于香港、求学于英伦,中西方文化的碰撞给你的创作带来了哪些影响?唐景锋:我觉得我在成长过程中就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小孩,但去英国上学后,就受西方文化影响更深一些。直到我的女儿出生后,我才意识到我需要反思自身的身份认同。在完成《女王、主席和我》项目后,我觉得我的先辈产生了更多的联结,也第一次觉得自己非常的中国。至于如何影响我的创作,我可以说我处在一个不错的位置来观察中国,既身处其中、又置之事外,可以在保持敏感的同时又避免西方式的凝视。眼光:你曾在大学时就读医疗护理相关的专业,又在毕业两年后成为了职业摄影师,是什么促成了这种职业规划上的转变?唐景锋:我在19岁时,只是想要获得一个今后可以让我四处游历工作的学位。毕业后我作为一家NGO的医疗人员赴印度工作,在那时,我拿起了相机,重启了高中后就暂停的摄影创作。我感到非常幸运,我拍摄的第一个关于印度的残障儿童的项目,就拿到了Luis Valtueña国际人文摄影奖。这次获奖也是促使我转向职业摄影师的契机,尽管当时我时常觉得自己对如何成为一个纪实摄影师还需要更深入的了解。在经历了一些事件后,我意识到我需要重返校园,学习更多关于摄影伦理方面的知识。之后我就回到英国,在伦敦艺术大学攻读纪实摄影专业的硕士学位。




眼光:在《唐水黄土》系列中,你如何重建与故土之间的联结?唐景锋:在完成《女王、主席和我》这一项目后,我感觉和祖辈之间的联系更紧密了,也理解了他们离开内地乃至离开香港的决定。在了解了他们的境遇后,我也得以第一次与他们“见面”。《唐水黄土》项目的核心理念即为我能否与故土、中国重新产生联结。
我曾多次前往位于祖辈位于珠海唐家湾和广州的家乡。我父亲一方的家族与海洋有着很强的关联,他们曾是渔民、水手或是商人,一些海难也对家族造成重创。我母亲家族的一脉则与之相反,繁衍于陆地,身份为地主或建筑商等。
然而,直至我在这两地拍摄项目时,我才意识到我对这些地方不论是情感上还是身体上都缺乏关联。最终,我决定沿着父亲家族一路迁徙的水路,把与父辈相关的影像负片浸泡在海水里,让负片被侵蚀染色。与母亲家族有关的负片,我则把它们置于鞋底,在母亲家老宅旧址来回走动,让故土在负片上留下按压、刮擦的痕迹。这些褪色或损坏的痕迹,是我与家族故土关联甚微的一种隐喻。

眼光:除了父母家族的祖籍地,你还走访了很多其他省份。唐景锋:我意识到我对于中国的印象局限于童年时期的电视剧,近期则基于我摄影项目的实践。当时我深入内陆地区,去搜寻我预想中关于中国的图景。我的装备是一台80年代产的海鸥相机,并没有沿着特定路线,尝试在各地寻找自己和想象中母国的关联。对于这些景观,我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归属感和情感联结,然而当我靠近当地人的时候,我反而觉得陌生和疏离。我意识到我和当代中国和当地居民经常难以深入交流,我尚不流利的普通话又强化了这一点。因此,这个项目的照片排布也延续了我的这种体会,照片中的人物越来越大,但是当你开始关注他们的脸时,会发现他们是散漫而相互孤立的,也不会与我的镜头产生互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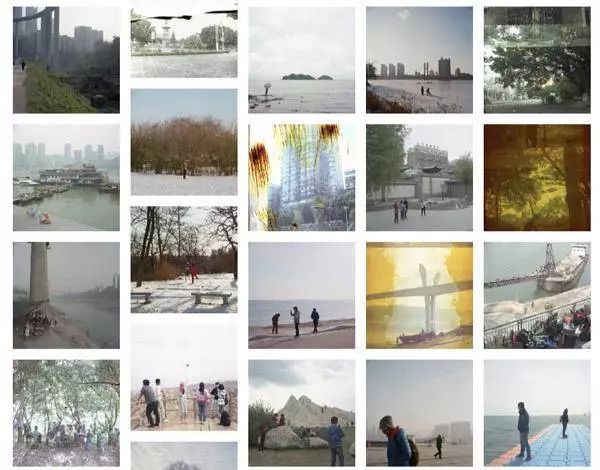
眼光:《唐水黄土》项目完成已经有两年了,你对自我的身份认同是否有新的认知?你如何评价自己的当时的作品?唐景锋:正如我所言,我仍然在寻求对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时更深层的理解。当我在不同省份游历时,我发现文化差异很大,可能广东的文化和西北、东北地区就很不一样。对于作品而言,我视之为一个让我重新走向摄影的项目(鉴于我用了两年专注于拍摄),这个项目是一种对纯摄影的回归,仅仅是一人一相机,在四处寻找适合拍摄的时刻。拍摄完这个项目后,我也更倾向于关注摄影图片,从而进行了之后的《寻找冰玉堂》(关于其家族保姆自梳女颜姐的项目)。
眼光:在一次《假杂志》的活动中,你推荐了Alec Soth的画册《沉眠于密西西比》,Soth的作品对你有何影响?
唐景锋:当时Alec Soth对我影响很大,他的作品教会我如何放缓节奏,用一种更诗意的方式思考,而不是局限于图像或故事驱动。这也使得我开始使用大画幅相机,我觉得这一器材非常适合我。眼光:在你的作品中,有许多关键词和女性相关,也出现了大量女性的家庭影像,如保姆、母国、女王(故事为女儿创作)。为何做出这种选择?唐景锋:哈哈,我不觉得这是一个有意识的决定。当我第一个女儿出生后,我开始了进入了自我探索的项目,我感觉我需要了解更多关于中国人的身份的内容,这样我也可以传授给我的女儿。之后我又有两个女儿出生,可能我经常被女性环绕,促使我选择了相关的主题。

唐景锋:我对讲述个体故事的研究项目非常感兴趣。从我的直系亲友相关的项目中抽离出来,我的下个项目暂命名为《Dear Franklin》,会采用“旧片重制”(found footage)的手法。这个项目集合了文本、视频和摄影,旨在讲述一个动乱时期的爱情悲剧,包括他们如何应对战争、被迫分离、社会流动、惨痛损失,乃至道教文化和冥婚等。



年轻人的状态:一个时代的文学切面 | 眼光
5年走了40个荒村,他用影像记录中国乡村变迁图景 | 眼光
少年变老时,他用照片化解现实中的不安与荒谬 | 眼光
老来迁徙:进城带娃,与老伴千里分居 | 镜相
他是这世上最渺小的推销员,可谁又不是呢?| 镜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