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凭栏欲言
因为重点截取了
1993
年来对比观测
当今趋势
的可能发展,我突然想起了《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的作者黄仁宇选取了历史中相对平淡的一年铺开来看
历史趋势发展的必然
。
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黄仁宇认为:“中国的过去,禁忌特多,所以说话作文时有隐晦,或指彼而喻此,或借古讽今,这在明朝人更为惯技”。
明朝以前的人
确实缺点多多,黄仁宇说得对。
回归正题,
1993
年对中国并不是一个平淡的年份,而是一个特别的年份,为什么特别?
因为它是很多改革措施的前奏,也因为它跟
2020
年有较高的相似度!
01
特别国债来了
3
月
27
日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
“
发行特别国债
”
,引起了高度关注,这是时隔
13
年之后,中国再次计划发行特别国债,这也是将是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发行。
历史上中国发行过两次特别国债,分别为:
1
)
1998
年财政部发行
2700
亿元特别国债(期限为
30
年),用于向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补充资本金。
2
)
2007
年财政部发行
1.55
万亿元特别国债(期限为
10
年和
15
年),用于向中央银行购买外汇,从而注资成立中投公司。
特别国债的资金筹集模式类似于中央财政直接向银行透支,在
1994
年之前,这个模式极为常见,
90
年代初中国多次发行
“
特种国债
”
,直接向银行透支,目的是补充财政收支缺口。一个原因在于当时中央财政资金缺口很大,迫于无奈;另一个原因在于当时的银行商业化程度不高,仍侧重于计划模式。
随着
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中央分走了六成的财权但只承担四成的事权,中央财政由赤字变盈余,类似直接向银行透支的国债模式就不再多见,两次特别国债发行历史也可以看出,其用于特别的目的,
而不用于补充财政资金缺口。
对于本次(第三次)特别国债发行的目的,似乎倾向于基建、民生建设、加大对中小微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和促进消费等。这似乎与前两次特备国债发行目的不太一致,似乎是受疫情影响侧重于
补充财政收支缺口。
02
特别国债与货币超发
为什么向银行透支的模式不再多见了呢?
在央行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中,特别国债(或特种国债)将体现为对政府债权的增加,资产等于负债,对应的负债项为政府存款同步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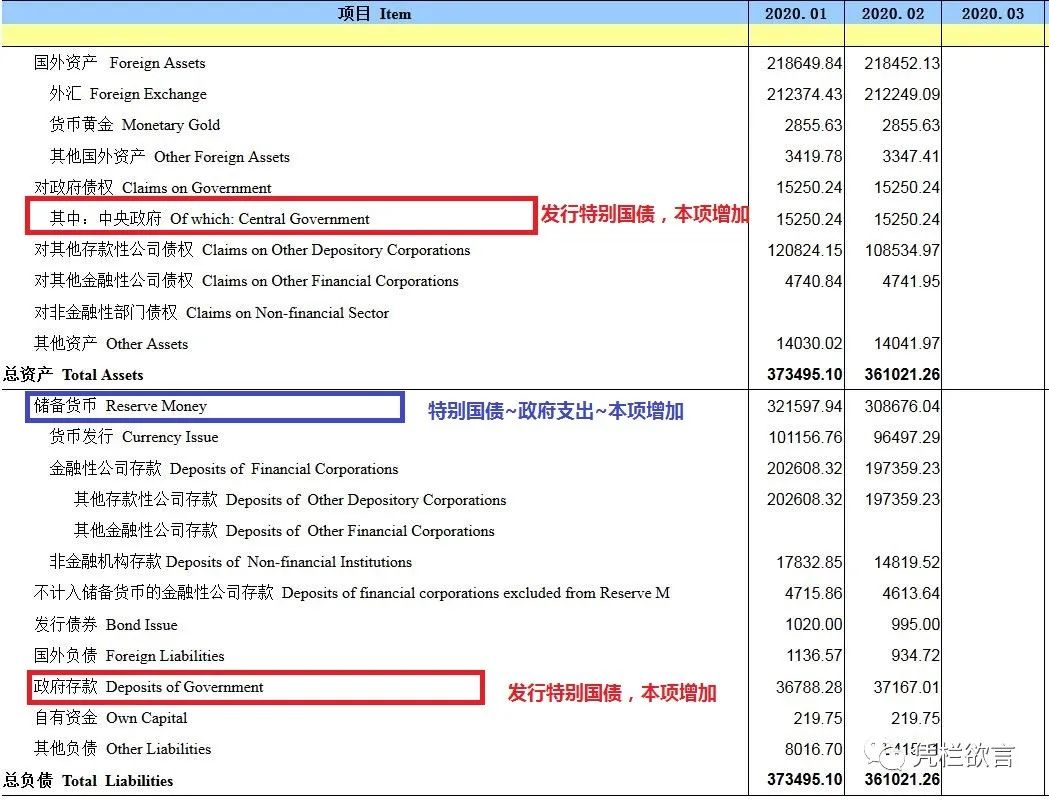
当政府存款被花掉之后,政府存款项就会减少,资金经实体流通后最终影响储备货币项同步增加,
这是高能货币,会被货币乘数放大。
经货币乘数放大后,理论上,现在新发
1
万亿的特别国债,将驱动
M2
增长
6.58
万亿,目前较高的估算口径是准备发
4
万亿特别国债,可以设想下其对货币量的影响。
虽然央行可以通过正回购或停止
MLF
等(放水工具)予以对冲,但很难完全消弭其影响。
政府对银行透支,必然会冲击汇率和通胀。
03
1993
与
2020
的相似度
专向债(不用于政府日常开支)就是基建债,
2020
年
3
月
31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再提前下达一批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带动扩大有效投资。
在内外需求下降的双重挤压之下,加强基建似乎理所当然。
这与
1993
年高度相似,当时出于一些政治原因,
1988
年开始收紧的货币与财政在一年后双双放松,激发了新一轮基建狂潮,持续到
1993
。有所不同的是,
1989-1993
年主要采取的是对银行透支的模式,而非发债,这并不影响本质——
因为基建总是需要货币超发的支持。
当前,在基建和货币的影响下,叠加疫情冲击外需订单大范围取消,基建刺激经济会具有两个副作用:
1)
刺激通胀。
2)
刺激进口而出口承压,导致贸易逆差。
历史上
1993
年,也是大基建的背景下,两个问题同时出现,
1992-93
年因基建影响进口钢材
4000
万吨,中国对外贸易由顺转逆,外汇储备由升转降,一度降至
200
亿美元以下,中国通胀率超过
20%
。
而当今,新基建虽然对钢材的需求下降,却需要进口各种电子元器件!
更为相似的是,房价泡沫!
1993
年正是海南房产泡沫的巅峰。
04
1993
年的粮食问题
1991-1992
年,连续两年粮食大丰收,农产品棉糖粮全部滞销,国家加大了收储力度,
1993
年中国国储粮正处于历史最高水平,达到约
800
亿斤。
但
1993
年
11
月,粮价暴涨突如其来。粮价整体涨价
0.3
元
/
斤,而当时稻谷的收购价才每斤
0.32
元。
事件缘起于广东等沿海工业大省,土地或建厂、或房地产占用、或产业园占用、或抛荒,人员入厂务工,粮食产量下降,就去内地抢购粮食。
而在当时高通胀的推动下,农业生产资料化肥农药等暴涨,粮价因长期工农业剪刀差压制,价格较低,农民惜售。
供需关系在货币泛滥的影响下,开始推高粮食价格。而公商(与私商)入场进一步强化了炒作,炒作赚了钱归自己,赔了钱归公家,放大了炒作胆量。万科创始人王石的第一桶金,就源自倒卖玉米。
1993
年国储粮存量有史以来新高,
1993
年粮食价格新高,戏剧化的一幕就这么突然出现。
为压制粮食涨价,国家通过国有粮店挂牌降价的办法,抛售平价国储粮(
2019
年抛售平价猪肉有异曲同工之妙),两种低标粮食(标准粉和标二早籼米)作为最基本的口粮不涨价抛售,其余品种有不同程度的上涨,粮价在约上涨
0.2
元
/
斤的幅度上得到控制,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但没过多久,
1994
年
3
月粮价暴涨又来,最终中国将多年积累的
800
亿斤国储粮抛售约半,粮食价格暴涨问题才得以控制。
从效果来看,低价抛售并不是粮价暴涨最终得以控制的主要原因,抛售只能短期压制粮价(包括现在的猪肉),
粮价暴涨问题的最终解决实际上源于
1993
年的财政与货币双紧。
价格是货币的具现,钱紧了,价格自然就得到控制了。
1993
年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