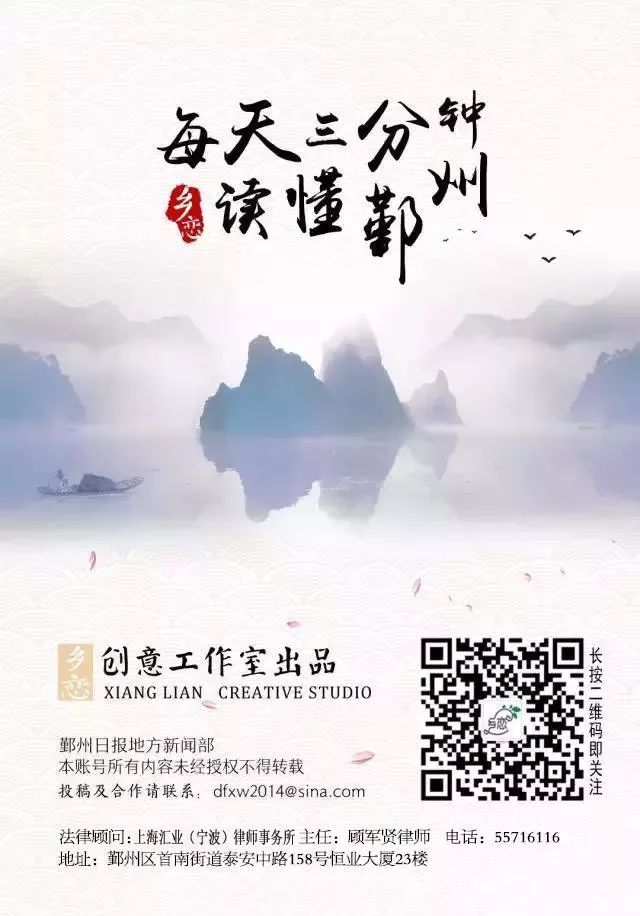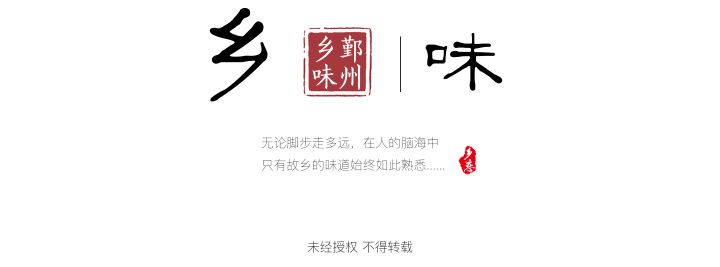
视频拍摄 叶维娜 林开艳(实习生)
剪辑 叶维娜 配音 张璐科 视频文字 叶维娜
每一次的遇见,都是梭子蟹破壳重生后的自己。
梭子蟹,俗称白蟹,因头胸甲呈梭子形,故名梭子。立秋刚过,时值开渔,梭子蟹迎来了一年之中产量最多的季节,宁波人的餐桌上,多了这道美食。

皮日休《咏蟹》写道:未游沧海早知名,有骨还从肉上生。莫道无心畏雷电,海龙王处也横行。横行一生的梭子蟹,在餐桌上的经历,成了它们最为安静的时刻。
煮熟后的梭子蟹外壳红似火,肉质白似雪,轻咬一口,蟹肉的香嫩混合着海水的自然咸味,透着浓浓的鲜味。

自古以来受人喜爱
蟹黄好吃,蟹肉更是鲜嫩无比。与蟹黄的沙粒感形成对比的是,梭子蟹的肉质洁白晶莹、口感饱满,越是新鲜壮实的蟹,吃起来越是带劲,一片片鲜滑的蟹肉从硬壳中剥离出来,卷入舌间,大快朵颐之后,内心充满了成就感。

自古以来,不少文人墨客对螃蟹亦有独特的宠爱,宋代陆游曾写道:
"
传方那鲜烹羊脚,破戒尤惭擘蟹脐。蟹肥暂擘馋涎堕,酒绿初倾老眼明。
"
意思是刚动手挖开肥蟹时,馋得口水淌了下来,持着大螯喝着酒,昏花的老眼也亮了起来,真可谓嗜蟹近痴。
爱吃蟹的人,蟹的全身都是
“
宝贝
”
。蟹的
“
大腿肉
”
,肉质丝短纤细,味同干贝;
“
小腿肉
”
,丝长细嫩,美如银鱼;
“
蟹身肉
”
,洁白晶莹,胜似白鱼;
“
蟹黄
”
,色彩鲜艳,鲜美而香。

梭子蟹的吃法各种各样,通过蒸、煮、炒、腌制等各种制作手法,表达着对它的喜爱。肥嫩长膏的母蟹最适合腌咸蟹或做蟹糊,腌制后的蟹肉晶莹剔透、蟹黄橙亮,让人垂涎欲滴。较肥的公蟹用来清蒸,趁着热气未散,打开蟹壳,阵阵香味袭来,大嚼一顿,着实味美。相对较瘦的蟹,则可用其来煮羹,最常见的莫过于丝瓜白蟹羹了。

饱腹于舌尖上的梭子蟹
八月,是梭子蟹开吃的季节,在山海小镇瞻岐镇,菜场的梭子蟹新鲜量大又便宜,是居民们最爱购买的一道菜,也是食堂师傅们最为青睐的一道菜。
早上
5
点半,瞻岐镇镇政府的食堂师傅李谟康,便早早出现在菜场里。
一大早,他便从菜场带回了两大脸盆新鲜而肥实的梭子蟹。李师傅说,挑蟹有讲究,蟹脚大而硬、肚子撑得越开的蟹才是好蟹。

说话间,李师傅麻利地将蟹捞起来,放到水龙头下冲洗,切开蟹的硬壳,挖去滤腮,随后在蟹脚中间整齐的横竖各切一刀,将切好的蟹摆盘,放入蒸箱,动作一气呵成。
在等待蒸蟹的过程中,李谟康又开始忙活起来。作为地道的瞻岐人,他所知的做蟹方法有十来种。刚才做的蟹是葱油蟹的前半部分,接下来要做的是丝瓜蟹羹,丝瓜是当季蔬菜,跟梭子蟹煮在一起,两味食材都可变得香甜鲜嫩,口感极好。
正聊着,丝瓜的外衣已被刨去,李谟康动作娴熟地将丝瓜斜切成块,在锅中倒入油,将事先准备好的蟹放入锅中翻炒,待蟹变色时,放入丝瓜继续进行翻炒。倒开水、放盐、再倒入事先调好的淀粉,才几分钟,一大碗可口鲜嫩的丝瓜蟹羹华丽诞生。

此时,蟹也已经蒸好。李谟康在蟹肉上点缀了一层葱花、姜丝,再倒入加温至冒烟的色拉油,只听得
“
哧拉
”
一声,厨房里顿时香气四溢,葱油蟹的五彩缤纷尽呈现于眼底。
茐油蟹刚好,大锅里白煮蟹的水已开,沸腾的开水中时不时浮起成块的飘浮物。李谟康说,这是蟹的蛋白质,蟹越新鲜,蛋白蛋越是凝结成大块。在捞出蛋白质的过程中,李师傅教给我们一个秘诀,如果煮白蟹当餐吃掉,那就煮到八九分熟即可,特别鲜美。但如果要等到冷却了才吃,那就必须煮成全熟,这样肉质依然是一丝一丝的。

常年在厨房忙碌的李师傅做菜的速度堪称一绝,一眨眼的功夫,葱油蟹、丝瓜蟹羹、水煮蟹、咸蟹等早已摆上了餐桌。

出没风波谋营生
“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
范仲淹的《江上渔者》,充分写出了捕鱼人的艰辛。
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的捕鱼条件与过去相比,有了天壤之别。尽管如此,出海的日子依然是辛苦的。因为要赶着潮水回落出海,因此每一天的出海时间都是不固定的,一般每一潮的时间为
45
分钟,一天涨落两次就是
1
个半小时,因此每天出海时间就要按这个规律往后延,所以每个月必定会有凌晨一两点摸黑出海的日子。
精瘦、幽黑、自信,是船老大谢忠良给人的第一印象。自
8
月份开渔以来,谢忠良便根据每天退潮的时间,按时出海去捕鱼。作为近海捕捞船只,他们一般作业时间为七八个小时,但有时候也会多达
10
几个小时。

55
岁的谢忠良,是瞻岐镇歧下洋村人,自
14
岁起,老谢就常常跟着父母到滩涂捉鱼。
因为打小便尝过渔民生活的艰辛,年轻时候的谢忠良并不愿延续父辈的生活模式。反倒在
40
岁不惑那年,他买了一艘玻璃钢渔船,当起了船老大。
8
月
5
日,他带着两名助手首次出海。根据经验适时撒网、收网,果然收成不错,密密麻麻的梭子蟹在网内不停地挣扎逃窜。谢忠良和助手们熟练地用橡皮筋捆绑一只又一个活蹦乱爬的鲜蟹,然后放入
“
腰子箩
”
,装满后将箩用绳缆拉入,浸入海水中,确保梭子蟹的鲜活。
当天清晨
6
点出发,下午
4
点多靠岸,一船透骨新鲜的梭子蟹和小鲳鱼直接批发给商贩,换回
3000
多元收入。
“
刚开渔,近海梭子蟹量大,因此价格也是最便宜的时候。等到西风一吹,蟹都躲到温暖的深海去了,那时候梭子蟹不好捕,价格也因此翻几番,甚至卖到三四百元一斤。
”
谢忠良说。

蟹的一生一般要脱壳
13
次,最多
14
次,从最初的芝麻般大小,逐渐长至成人巴掌大小。当前季节,大部分梭子蟹脱壳刚到第
10
次,因此还不是最肥美的季节。等到
10
月份,蟹完成了一生的脱壳次数,就意味着完全成熟了,再到一两个月,也就是
11-12
朋,那就是梭子蟹最肥美的季节,也是价格日益走高的时节。
那什么样的梭子蟹才是好蟹?老谢说,梭子蟹一般有黄壳和青壳两种,壳面颜色均以略深为好,越浅意味着越嫩。此外,梭子蟹的肚脐处有三根筋,越是往上凸起,表示越壮实;肚脐处与背壳的距离离得越远说明蟹肉越饱满。
谢忠良在盆前给我们讲解哪只蟹最肥,哪只又略逊色一些。突然,他拎起一只梭子蟹,说这个快要褪壳了,撕开一只角,果然见到里面有一层粉橙色的软壳,让我们佩服不已。
当下靠海吃海衣食无忧又自由自在的生活,让到了知天命年纪的谢忠良较为满足。休渔季节,老谢就一心扑在
30
亩泥塘里,那里有他养殖的梭子蟹、蛏子和虾,补充一年的收成。老谢说,今年老天帮忙,风调雨顺,养殖的梭子蟹质量也非常好,市民下半年吃蟹,可以敞开肚子一饱口福了。

几十斤蟹股吃一年
宁波人都爱吃咸蟹或是蟹糊,透骨新鲜的梭子蟹,腌在调好的盐水中,一般第二天就能吃了。那滋味,鲜咸可口,无论下饭还是下酒,都是一等一的好菜。
但几十年前,在生活尚不富裕的那个年代,咸蟹、蟹糊那是过年过节才会上桌的大菜。大多数沿海人家,都只制作蟹股或蟹酱,用粗盐腌好,每餐捞出来吃一点,一吃就是一年。
瞻岐镇农办工作人员叶海召,年近六旬,是土生土长的瞻岐人,在他的记忆中,蟹股是餐桌上永不落时的一道菜,是家家户户都需要的
“
压饭榔头
”
。农忙时节,带饭到田头,一小罐蟹股就解决了一大盒饭;芋艿、土豆、茭白、茄子上市的季节,蟹股汁又成了天然美味的最佳调料。
过去沿海人家做蟹股,不像现在只做小小的一碗,而是直接批发来几十公斤,用大缸来腌制。而
8
月份,正是梭子蟹大量上市的季节,价格最便宜,也是节约的家庭主妇们最喜欢做蟹股的时节。
叶海召十六七岁时,常被父母派到横山码头或是球山一带(那里渔民比较集中)去批发梭子蟹。渔船刚靠岸,透骨新鲜的梭子蟹,只要几毛钱一斤。在挑好梭子蟹后,如果有余钱,叶海召也会同时挑一些小鱼,好回家晒成鱼干。
梭子蟹用箩筐挑回家后,用清水过一遍,挖开壳去,用剪刀剪成大块大块的放入脸盆,撒入大把大把的粗盐。大人们拿着脸盆来回反复摇晃调匀,再依次把腌好的蟹倒入一只只的瓦罐中,用竹子壳封上口子,每天要吃的时候,用勺子取一些出来,往往能吃到来年夏天。
蟹股一到天热,容易出虫。因此,沿海一带的居民还喜欢把梭子蟹做成蟹酱。梭子蟹买回家后,剪去尖角,挖去滤腮,剪成小块,然后放入石磨细细研磨,一般
10
斤蟹放
3
斤盐,这样磨好后的蟹酱,静置在角落,可以吃上两三年。
随着生活条件的提升,在讲究养生的年代,过咸的蟹股和蟹酱已很少有人会做,但对于老一辈人来说,那滋味、那场景,已然烙印在生命的时光里。
来源 | 鄞响客户端
编辑 | 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