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气读完题目的举手!!!
最近上海没什么新的话剧可看,于是高清戏剧影像成为了最好的选择之一。
好戏几乎没写过高清戏剧影像的评论,所以很多朋友们只知道导演演员制作都很好,但戏究竟好在哪里?不如从今天这篇文章开始了解。
NT Live的
《罗森格兰兹与吉尔登斯吞死了》
是引进没多久的新戏,8月才第一次与上海的观众见面。
因为名字太长,所以罗森格兰兹以下简称“罗森”,吉尔登斯吞以下简称“吉尔”,作者有时还会偷懒写成“罗”和“吉”。
他们是《哈姆雷特》中仅出场5次、平均每次只有7句台词的小角色。

丹尼尔·雷德格里夫在剧中饰演罗森格兰兹
根据莎士比亚的设定,他们是哈姆雷特的发小、国王的臣子,也是友谊的背叛者、权力的屈从人。
回忆一下莎士比亚赋予他们的命运:
奉命来奥西诺——找哈姆雷特套话——带着信送哈姆雷特去英格兰——信被哈姆雷特掉包——被英王处死。
细想整个过程,他们听到的没有几句真话,知道的比观众还少。
编剧汤姆·斯托帕德是四度托尼奖最佳剧本奖的得主,另外还有一座奥利弗奖,以及凭借《莎翁情史》的剧本拿到的奥斯卡小金人。
这部1968年的托尼奖最佳剧本,锁定了《哈姆雷特》剧中这一模糊场域,让两个小人物成为主角,呈现两人在不祥的预感中,稀里糊涂迎来死亡的过程,并将这一沉重的话题寓于
喜剧
形式之中。
 《罗森格兰兹与吉尔登斯吞死了》剧照
《罗森格兰兹与吉尔登斯吞死了》剧照
在斯托帕德的这部戏里,他们不记得自己从哪来,又是为什么而来,对哈姆雷特也不太了解,一切都是别人告诉他们的,别人说是什么,就是什么。
“哈姆雷特是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
“那只是别人告诉我们的”
好像是被一下拽进了《哈姆雷特》这部戏里,演这样两个角色。前情不了解,结局未可知。
推动着他们行动的是莎士比亚的一纸剧本,他们无力反抗,也没有权利提前获知剧情。
值得注意的是,
原《哈姆雷特》的场景会时不时地乱入,打断两人无聊的对话与游戏,并且保留了
莎氏的风格
。两个小人物的滑稽游戏与《哈姆雷特》的诗性悲剧持续互动,由此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张力。
先说舞台动作的对比,请结合演员气质自动脑补:
 哈姆雷特和奥菲利亚的扮演者
哈姆雷特和奥菲利亚的扮演者
哈姆雷特:
大步流星走上舞台,一把抓住奥菲利亚,紧紧搂住她,然后松开,一只手搭在眉毛上,专注的审视她的脸,然后他的手臂开始颤抖,发出一声悲哀沉重的叹息,突然放开她,迅速转身,又回过头来,倒退着向后走去。

罗森格兰兹与吉尔登斯吞的扮演者(左为丹尼尔)
吉尔登斯吞:
朝两脚之间扔出一枚硬币,俏皮地接住,反转在左手上,向上一抛,又用右手接住,在两手之间颠来倒去,然后抬起左腿从腿下扔过,转身接住,最后把硬币放在自己头顶上。罗森走过去,踮起脚,把硬币拿走。
一对是罗密欧与茱丽叶,一对是没头脑和不高兴。
再说
语言
上的画风差异,汤姆·斯托帕德极其钟爱语言游戏,罗森与吉尔的对话颠三倒四,几乎没有实际内容,经常因为字面涵义与语境涵义的差异闹出误会:
(心情烦躁者慎读):
GUIL: Do you think it matters?
ROS: Doesn't it matter to you?
GUIL: Why should it matter?
ROS: What does it matter why?
GUIL: Doesn't it matter why it matters?
ROS: What's the matter with you?
Pause.
GUIL(sigh): It doesn't matter.
当然这个点对母语非英语的中国观众来说,很容易流失,我们在现场只能感到那种“颠颠”的氛围。
此外,整部戏中充满了
“双关“
,比如“You’ve get it”,既是“你说对了”,也是“东西在你那”,比如“Of(f) course”,既是“当然”,也是“偏离航道”。
于是罗森永远Get不到吉尔的点,两人的讨论永远由于无休止的误会而得不到进展。

反观皇室成员,他们出口成章,态度明确,情感充沛。当他们从四面八方突然上场时,台词画风就会瞬间切换:
Fare you well
My honored lord
hath
dost
thou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语接踵而至,莎氏台词
五步抑扬格
的韵律也开始奏起,此前罗森与吉尔啰啰嗦嗦的现代语言被突然切断。
此外,
哈姆雷特的主角光环与两个小人物的命途多舛,也形成了很好的喜剧空间。
剧中有一个场景,罗与吉看到哈姆雷特正拖着波洛涅斯的尸体走来,当时他们需要抢回尸体,于是吉尔急中生智:
这是个机会,也让他走进我们的陷阱!
他用动作示意罗森解下皮带解,把两个人的皮带绑在一起,自己拿一头,另一头递给罗森。
两人站在过道两边,坐等王子殿下被绊倒。
哈姆雷特果然拖着尸体向他们走来,几乎就要绊倒在皮带上时,他突然转向,从舞台另一侧安全下场。
——他们永远算计不到王子殿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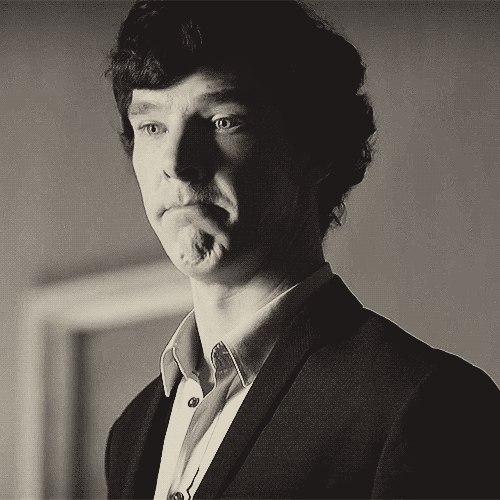
罗森气急败坏,开始大叫哈姆雷特的名字(潜台词是你给老子滚出来),但当哈姆雷特真的来了,他又犯怂,慌里慌张地问:
王子殿下,请问您把尸体放哪了?
王子一开口就是诗:
从泥土里来,回泥土里去。
整部戏里,
笑点
很多,一是罗森与吉尔滑稽戏式的语言、动作,二是喜剧与悲剧的对照。
但看完走出剧院,却觉得很
丧
。真正的喜剧就该这样。
人会笑,是因为觉得自己比喜剧角色优越,什么时候不笑了?就是觉得自己其实跟那些小丑一样,或者只好那么一丢丢。
理想中每个人都是哈姆雷特,但这部戏让我们认清自己的人设。
NT Live的这场演出是在老维克剧院,
舞台
空间
很深,呈现强烈的空间透视感,罗森与吉尔主要在前部活动。
 纵深的舞台设计
纵深的舞台设计
第二幕里,罗森与吉尔身后拉了一张幕布,那段纵深的空间被挡住,仿佛幕布后才是真正的舞台,正在上演《哈姆雷特》。
观众面前的只是舞台的一处边角,是两个小角色在幕布后偷偷窥伺。
轮到他们的戏时,不会有舞监跑来通知,而是主角们径直走进他们的地盘,“进进出出,时有时无”,偶尔给他们下一个含糊的命令。甚至有时只是匆匆经过,看都不看他们一眼,却足以把他们搞得心惊肉跳。
除了产生喜剧效果,新文本与原文本的并置,也改变了观众与原
《哈姆雷特》
的关系。
原本在看《哈姆雷特》时,观众是以“代入”的方式与哈姆雷特产生共情。而在这部戏当中,一方面,《哈姆雷特》剧作为观众心中的潜文本存在,另一方面,偶尔出现的《哈姆雷特》剧场景,在罗森与吉尔的对照下也被彻底客体化。
观众
共情的对象
变为罗森与吉尔,于是原本莎氏笔下一个个动人的角色显得脱离真实、过于矫情。

思考人生的哈姆雷特
悲剧在滑稽的对照下显得比滑稽还要滑稽,两个喜剧人物则变得真实可爱,所以当他们迎来自己必死无疑的命运时,尤其显得无辜。也正是这种被写就的宿命感,压得人喘不过气。
最后一幕,无论是屏幕上的英国观众,还是现场的中国观众,几乎没人笑得出来了。
斯托帕德还将《哈姆雷特》剧里的戏班子并入这部戏,戏班班主不断向罗、吉诠释“悲剧”,他们上演的《捕鼠器》与王室生活如出一辙。
吉尔喜欢用
三段论
想问题,大胆假设一下他的脑回路:
一、戏子的戏不是真实;
二、王室的生活是戏子的戏;
因此,王室的生活不是真实。
那么,凭什么要为这种“不真实”牺牲我俩真实的生命呢?
 剧照,左为戏班班主
剧照,左为戏班班主
通过
《捕鼠器》——《哈姆雷特》——《罗与吉死了》
,这个“戏中戏中戏”结构,
“悲剧”本身成为斯托帕德
戏仿
的对象。
仿佛这两个人畜无害的小人物来世间走一遭,经历无意义的生与无缘由的死,就是为了成就哈姆雷特的一段Drama。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像罗、吉,都怕自己成为主角们的牺牲者。
悲剧感
是人性中的固有情怀,它是人对孤独和崇高的自我肯定,我们习惯于以此为荣。
但当斯托帕德将它置于喜剧之中,使它成为被审视而不是被经验的对象,我们就不得不面对它的破坏性。这种伤害有时是对自己,有时则会伤及无辜。
不要一味喜欢或习惯性地追求崇高
——对于这个人人都是演员的时代来说,也是很切题的忠告了。
歪个楼,看看“童年”就知道自己老了:
 排练中的丹尼尔,我们的哈利·波特(捂脸)
排练中的丹尼尔,我们的哈利·波特(捂脸)
注:本文剧照、排练照来自英国剧院现场,动图来自文章
NT Live表情包 | 丹尼尔、约书亚"互怼"+卷福、米勒同唱《好汉歌》!
推荐内容:
点击以下图片即可阅读

《变身怪医》真是我今年最喜欢的中文版音乐剧!

当演后谈成为“尬聊”,还有存在的意义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