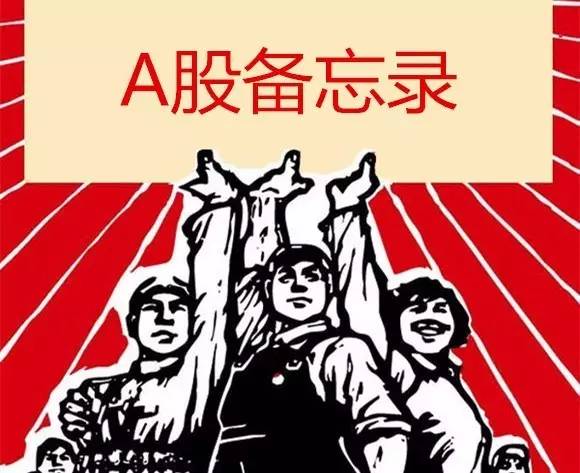左派必须正视这一基本事实。我们不能声称与巴勒斯坦同在,却又否定、忽视或是排斥哈马斯。
最近出现了大量文章批评西方左翼对哈马斯的“欢呼”(celebrate)。这些批评大多认为,把对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支持简化/还原成对哈马斯的支持,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是一种伤害,因为巴勒斯坦人代表着多种声音,具有不同的政治倾向。
这些批评呼吁西方左翼正视巴勒斯坦政治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Bashir Abu Menneh在《雅各宾》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并不是铁板一块》的文章。在文章中,作者严声斥责了他所谓“左翼对一场类似哈马斯这样的‘社会性倒退’运动的欢呼”。这篇文章与其说是在批评哈马斯,倒不如说是在暗暗对武装抵抗运动本身进行批评。Matan Kaminer撰文回应了Andreas Malm发表在Verso Blog上的一篇文章,称全球“团结运动必须处理好巴勒斯坦政治的多样性”,并质疑哈马斯等缺乏左派议程的“反体制”力量。在《波士顿评论》(Boston Review)上,Ayça Çubukçu回应了Jodi Dean的文章《巴勒斯坦为每个人代言》,因为Dean建议全球团结运动应该与巴勒斯坦内部有组织的左翼站在一起支持哈马斯现任领导集团的解放斗争。
毫无疑问,关注巴勒斯坦的政治、它的历史,以及目前它的状况与多样性,这些都很重要。
事实上,尽管巴勒斯坦人的数量相对较少,尽管河海之间的巴勒斯坦在地域上很狭小并在领土问题上极具争议,但我们可以发现,无数巴勒斯坦人对冲突抱有这样那样的幻想或意识形态——其中就有那些轻易肯定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巴勒斯坦人。
但有趣的是,那些批评哈马斯的西方左翼正是在这一点上犯了错误。他们不明白,巴勒斯坦和政治的多样性也会转化成对待“抵抗殖民主义”的不同态度。虽然他们呼吁对巴勒斯坦政治进行更加细致的认识,但他们所谓对细节的认识并没有深入到那些同时激起和回避(或是积极反对)反殖民主义抵抗的动力学关系和力量。
这种对巴勒斯坦政治的无知几乎可以说是有意为之。它对“抵抗”,尤其是武装抵抗怀有隐秘的敌意,但它又宣称自己是因为别的完全不同的理由(也许是意识形态的)而反对哈马斯。然而,若是想真正了解巴勒斯坦内部的动力学关系并揭开“铁板一块”的面纱,我们就必须切实了解巴勒斯坦的政治势力是怎样从一开始就与抵抗的理念紧密联系在一起。
巴勒斯坦人受制于以色列精心设计的各种区隔。事实上,考虑到不同巴勒斯坦人的日常生活截然不同、分散在全球各地并受制于以色列的各种治理和管控模式,如果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够团结起来,那会是非常令人吃惊的事情。巴勒斯坦人内部存在的区隔不仅有地理上的,还包括殖民宗主国家强加于其上的不同程度的特权与排斥。我指的是加沙、西岸、耶路撒冷、1948年的领土,还有巴勒斯坦离散群体(diaspora)。
此外,这一严重的支离破碎已经导致许多巴勒斯坦人开始质疑“自己作为一个民族而团结起来”还是否可能。他们开始思考,巴勒斯坦人抵抗能力的差异是否本身即显示出地理区隔和各种殖民治理75年来(after 75 years)所造成的重压。
加沙的种族灭绝战争暴露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即除了加沙之外,不同地区的巴勒斯坦人一直没有能力积聚力量、制定新战术、建立新组织或是构建出新的知识和物质大厦以应对定居者殖民主义对各地巴勒斯坦人民构成的挑战。最能说明这一失败的,莫过于一种笼罩在几乎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的瘫痪性恐惧。只有加沙以及在过去十年中兴起的一些更先进的斗争路线和新的抵抗模式免于这一恐惧,其中就包括约旦河西岸的原子化抵抗行动以及西岸北部逐渐扩大的武装自卫区域。
这种多样性不仅仅是身处不同结构性控制模式下的巴勒斯坦人的不同政治意识形态的聚会(function),而且还在不同巴勒斯坦个体的心理结构内部爆发出来。在抵抗的激进潜能与对以色列无情的军事力量的恐惧之间,巴勒斯坦人不断徘徊,在他内心深处正进行着一场激烈的对话。他们既渴望解放,又担心日常生活中的任何干扰——哪怕是由抵抗引起的干扰——都会破坏脆弱的正常生活。这就是意识形态斗争真正发生的地方。意识形态斗争不仅仅发生在公共领域,而且也发生在个体层面。
在个人那儿,崇高的自由之可能性与可能被强大军事机器消灭的创伤性现实之间存在着交锋。
每个势力,带着自己的诉求,将巴勒斯他人推向一系列存在主义选择——革命还是屈服、移民还是坚守、象征性消解还是通过牺牲行动对身份给予充分确认。这一内心深处无声的对话表现为不同的政治表述:在知识分子-殉道者Bassel Al-Araj的立场与阿巴斯这类身处高位之人表现出的更为犬儒的屈服立场之间摇摆。
前者宣称“抵抗早晚有一天会产生效果”,而后者则宣布“抵抗万岁,但它已经死了,而且哪里一旦又出现抵抗,我们就应该再次杀死它!”
不过,我们可不要被耍了。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捆绑在一起的意识形态机器声称能够不经中介地接触到“赤裸裸的显示”,但这一机器正是通过否认自身的意识形态来实现自身的运作。他们吹嘘自己看世界时没有被意识形态蒙蔽双眼,声称正因为自己多么多么清醒,所以有必要建立一个把对殖民主义的抵抗看作“闹剧”并把与殖民者地合作视作具有“神圣”重要性的威权政治体系。这种现实主义-实用主义的立场表面上将巴勒斯坦人引向一种否定——一种象征层面、政治层面和物质层面的自我否定,但又狡猾地通过化身为政治代表和建立国家来掩盖这一否定行为。
与此同时,统治阶级为了保持其连续性与控制权,长期奉行“政治现实主义”,从而轻易就忽视了自身的阶级偏见和社会偏见,而殖民地中的少数精英就从中获利。这种实用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创造一种现实,在这种现实中,抵抗的概念本身已经在妥协的现实中消失殆尽。然而,这只不过是在给与定居殖民者政权结成安保和经济同盟的行为(被殖民者就这样变成了殖民者)进行辩护的高深说辞而已。
结果就是,巴勒斯坦政治出现了一个连续体,其内部对抵抗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可以想象,马哈茂德·阿巴斯和曼苏尔·阿巴斯这样的人物站在光谱的一端,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和哈马斯这样的政治组织站在另一端,而中间却几乎没有任何严肃的政治势力。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关头,仍在坚持和领导抵抗议程的政治力量并非世俗左派。]
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巴勒斯坦各个政治派系之间的主要分界线并不在于世俗主义-伊斯兰主义之间的分野,也不在于不同社会经济议程之间的斗争,更不在于不同解放策略的优劣。这些问题当然也很重要,但真正导致巴勒斯坦政治舞台出现裂痕的原因,是“原始反抗型政治”与“包容、合作和协作型政治”之间的鸿沟。
归根结底,西方左翼在寻找哈马斯的世俗进步替代者时,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仍在坚持和领导抵抗议程的政治势力并不是世俗左翼的势力。

这一切并非偶然。以色列及其盟友精心培养和塑造了一个符合其殖民野心的巴勒斯坦领导集团,同时还逮捕、恐吓和暗杀了其他的替代势力。
这在反殖民运动中也并不罕见,身为殖民者的一员并不会自动就忠诚于反殖民运动。在巴勒斯坦,一个世纪之久的殖民主义在巴勒斯坦政治体中造成了许多扭曲,它把曾经革命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变成了一个类似法国维希的政权,法国维希政权就曾以民族的名义杀害民族。其他巴勒斯坦人则接受了新的亲缘关系和身份认同(identities),包括对以色列的认同(在一定范围内认同一个以犹太人至上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实体)。历史告诉我们,在有些情况下,人们可能也会为了让自己受到奴役而战斗。只要看看Joseph Haddad和Mosab Hassan Yousef这样的人就知道我在表达什么意思。
然而,还存在着更深层次的斗争:长期以来,巴勒斯坦人不仅为了让自己的困境得到承认而斗争,而且从根本上来说还在为让世界承认抵抗的必要性而斗争。在全球背景下,巴勒斯坦抵抗的叙事正在被操纵——被犬儒地拿来为以色列长达一个世纪对巴勒斯坦人的生存与权力做出的侵犯行为进行辩护并使之正当化。在这一背景下,抵抗之必要性以及抵抗之权利就变得更为重要。然而,我们正处在一个颇为反常的情景之中,对生存和伸张正义之可能性颇为重要的抵抗行动,竟然被扭曲成它所试图克服的压迫的正当化理由。
哈马斯在这里很容易就成了稻草人。它是一个伊斯兰政治团体,既以反抗政治为中心,又推动旨在重建巴勒斯坦主体的社会议程。批评抵抗运动的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指出哈马斯在社会经济观上的缺陷,嘲笑其“社会性倒退”的议程。但他们并不真的对批评(undermine)哈马斯的社会议程感兴趣。事实上,他们想破坏(undermine)哈马斯所选择的抵抗形式,或与之保持距离。但是,许多批评哈马斯的人在他们自己的同盟体系、斗争形式,甚至思想成果方面都无法与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积聚力量的工作相提并论,也无法与哈马斯如潘多拉宝盒般的战略库的运用相比。这个潘多拉宝盒已经被打开、使得殖民政权逐渐扭曲变形,并让我们进入到这样一个历史时刻:
巴勒斯坦解放的可能性也成为了众多可能性之一。
“Muzawada”是阿拉伯政治话语中的一个术语,可以粗略的翻译为“政治上的比谁更牛”。它长期以来一直被用作政治对手之间相互贬低的工具,而在实践中,它的主要运作方式就是通过揭露对手的虚伪、不切实际的言论或是言行不一来诋毁政治对手并打击其士气。叙利亚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Elias Murkus举例说明了叙利亚复兴党人如何在20世纪60年代利用Muzawada来批评Jamal Abdul Nasser(纳赛尔),比如指出纳赛尔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言行不一。但Murkus指出,这种批评与其说是出于对巴勒斯坦解放问题的真正关切,倒不如说是为了削弱纳赛尔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影响力。
在这种语境下,阿拉伯政治格局中的此类政治“竞标”或是“比谁更牛”行为在历史上会把巴勒斯坦当作自己的主要舞台,就不是什么很奇怪的事情了。重要的是,虽然历史上它常常被用作是“修辞上的对抗”,但Muzawada并不局限于此。在20世纪90年代的巴勒斯坦,各个政治派别通过创造和实现抵抗的能力而进行相互竞争,Muzawada也从修辞上的竞标演变为“现实中的竞标”,
这一双重表现形式——修辞化Muzawada和现实化Muzawada——对于理解巴勒斯坦内部的政治竞争而言至关重要。在第二次大起义期间,“istishhadi”形象的出现就是现实化“比谁更牛”的形式之一,因为它超越了传统的“fida’i”。“fida’i”是一种自我牺牲的形象,他与敌人交战,但或许可能回到基地,但是istishhad则体现了战士的自我牺牲精神,他不打算返回基地,而是杀敌并被杀死,从而成为一个烈士/殉道者(martyr)。
这一新生的反霸权力量在世纪之交的出现(主要是在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的倡议下出现),意味着通过创造新的反对方式和新的抵抗牺牲者形象,抵抗本身得到了新的构想。
在第二次大起义期间,“比谁更牛”意味着通过现实的抵抗来把政治对手比下去。这种内部竞争形式将抵抗行为视作将内部的政治不满情绪向殖民者外引的手段。巴勒斯坦各派在政治行动方向上保持一致,但同时也在相互竞争,试图通过采取不同的抵抗行为来把对手比下去。
然而,巴勒斯坦目前的分裂并不是一种形似于第二次大起义期间的那种“竞标”,也不是由于相互之间总想着要把对手比下去而造成的结果。相反,它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把与以色列的合作提升到“神圣”地位,并把继续抵抗行为视作一场闹剧之后才出现的一种分裂。在这一分裂的另一端,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成为了领导有组织抵抗的最积极力量。“区隔”在地理、意识形态和政治三个方面表现了出来。
在这种竞标形式中,政治等式的一方利用以色列对抵抗的军国主义反应声称:“看到了吗?这就是抵抗的后果!”它中止了对反抗政治的探索,
并且实际上是在以巴勒斯坦人民的长期抵抗能力为代价,为以色列的政治性瘫痪、停滞和迁就做辩护。
在这一目的内部,出现了巴勒斯坦左翼的三种回应。第一种左翼基于“世俗主义”和自身组织的弱小(例如巴勒斯坦人民党,其前身是巴勒斯坦共产党),选择让自己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买办阶级联姻。第二种左翼在反殖民主义问题上会愿意置身在伊斯兰势力一旁,但在社会议程层面又会与之保持距离,这类左翼的例子就是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第三种左翼将哈马斯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当成一丘之貉,希望人们认为自己这一派能够替代这两股势力。他们高喊着“这两派都很糟糕”,却又没有能力组织一个社会组织或是政治组织来替代哈马斯或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这一类左翼的例子就是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Democratic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

[抵制殖民主义本身(in and of itself)不就是一种可以增强被剥夺者能力的进步行为?而既然合作会让被殖民者处于屈从地位,那它难道不是一股社会性倒退的力量吗?]
至少可以说,在巴勒斯坦当前的政治格局中,“谁在‘社会性倒退’或‘社会性进步’”这个问题其实极其复杂。例如,我们如何理解那些支持各种形式社会性倒退与约旦河西岸的政治威权主义的左翼政党,比如巴勒斯坦共产党残余势力目前的倾向?在不断推进的定居者殖民主义企图抹杀整个社会的背景下,我们又该如何定义“社会性倒退”呢?抵制殖民主义本身(in and of itself)不就是一种可以增强被剥夺者能力的进步行为?而既然合作会让被殖民者处于屈从地位,那它难道不是一股社会性倒退的力量吗?或者说,抵抗者所宣称的意识形态更为重要?
在约旦河西岸的具体情况下,我们该从何处入手来阐述一个社会性进步的议程?在西岸,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混合使用各种威权做法、坚持银行教育形式、利用家庭和部落等传统社会结构,并把巴勒斯坦内部的敌人视为最终敌人,为持续的内战和区隔创造了条件,而与此同时,巴勒斯坦人正在试图反击殖民主义的侵蚀和蚕食。从严格的“西方”层面来看,巴勒斯坦没有整体乃至完全进步的力量,只有进步的因素或是倾向——即使是在那些被当作是倒退的政治组织内部也有这种进步倾向。
在最近发表的一连串文章中,我们遇到了一种令人费解的扭曲现象。它试图批评对抵抗(尤其是武装抵抗)的支持。在“西方”,许多人越来越认识到抵抗的必要性和有效性,或者起码可以说,在数十年来疏于解释抵抗的根源与必要性之后,人们可以开始努力面对抵抗的真实存在(reality),其中就包括在不诋毁它的情况下与抵抗进行接触。
西方左翼的这一转变并不意味着它突然就接受了伊斯兰主义,而是说明它认识到了巴勒斯坦人所处状况的本质(nature)——一个凶残的定居者殖民地,这个殖民地拒绝与那些被它视为卑贱的人进行政治对话(speak a political language),依赖于过度暴力以及外交和法律上的有罪不罚,采用了一套复杂的建筑、技术和间接控制形式。
但更令人担忧的是,武装抵抗的持存和演变违背了巴勒斯坦知识分子的一些现行理论(operative theories)、利益和政治倾向,例如迫切想要真正摧毁殖民制度、从而能够开始进行去殖民化的工作。
几十年来,这些理论一直存在,并利用一种广为接受的谈论起点(即巴勒斯坦人应该避免武装抵抗)以便在西方乃至全球舞台上树立起一个良好形象。
他们普遍认为,武装抵抗与为巴勒斯坦事业争取同情这二者之间水火不容。他们深信于对第一次大起义的下面这一解读:第一次大起义是标准的非暴力、大规模民众起义,它能够获得群众、民间社会和国际法律机构的支持,因此能够迎合主流西方社会的自由主义情感。
当然,这种解读也掩盖了巴勒斯坦人在第二次起义后所面临的心理和意识形态冲击,这种冲击试图在巴勒斯坦人的意识中灌输这样一种观念:抵抗是徒劳的,武装抵抗只会带来灾难,由于力量的不对称,巴勒斯坦人不能也不应该与以色列进行军事对抗。然而,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一样,围绕“民众抵抗”或 “和平的人民抵抗”建立起来的反抗性替代方案(defiant alternative)只是被用作一种意识形态和心理工具,以维持阿布·马赞(Abu Mazen)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所谓“神圣的安保合作”。组织民众抵抗的尝试寥寥无几,而且大部分尝试遭到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及其安保系统的打击,并且在加沙和西岸都遭到了严重的暴力对待。
那种以为西方左派摇身一变成了哈马斯的啦啦队队长的观念可谓极不切合实际情况。Jodi Dean并没有为哈马斯庆祝过,但也许她在反抗行动(为打破包围加沙的殖民政权所进行的游行)中确实找到了某种鼓舞人心的东西。她与参与抵抗行动的部分巴勒斯坦左翼人士站在一起。在那一天,大多数巴勒斯坦人都与Dean有着同样的感受,这些人当中也有许多人后来逐渐感到失望或是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或是出于道德考虑,或是由于以色列的地毯式轰炸行动以及种族灭绝战争(有些人因此得出结论说,不值得去进行抵抗)。

[正如Bassel AL-Araj所言,如果巴勒斯坦左翼想要与伊斯兰主义者竞争,他们就应该在抵抗中进行竞争。]
的确,在加沙、约旦河西岸和整个巴勒斯坦政体(polity)中,有许多人出于各种原因憎恨哈马斯。其中就有许多巴勒斯坦“左翼”,他们打着意识形态差异和伊斯兰主义-世俗主义分歧的幌子完全拒绝“抵抗”。不过,正如Bassel AL-Araj所言,如果巴勒斯坦左翼想要与伊斯兰主义者竞争,他们就应该在抵抗中进行竞争。用行动来进行Muzawada。
哈马斯归根结底是悠久抵抗历史在当代的体现,这一历史包括了Nakba前巴勒斯坦农民、巴解组织早期流亡的巴勒斯坦革命者和80年代及以后采取大规模主动行动的伊斯兰主义者。
世俗左派中的许多人已经变得苍白无力。他们拒绝哈马斯的抵抗,不是因为相信其必然失败,而是因为他们对哈马斯成功的可能性感到深深的焦虑。
他们并不只是出于道德的考虑而反对使用暴力,而是还带着一种恐惧,恐惧伊斯兰主义者或许真的比他们自己那套目前相当忧郁且反动员化(demobilized)的政治立场更加有效果。同时,巴勒斯坦精英中的某些派别将以色列视为现代化的灯塔,并对自己眼中的“倒退型”社会(‘regressive’ society)深感恐惧——这也充分说明了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倾向:
被大他者(the Other)所诱惑,对巴勒斯坦群众的解放力量感到恐惧。
与哈马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有分歧、在战术上有分歧——认为在目标选择上存在道德问题或是怀疑其战争能力——这是一码事。但是,反对(undermine)在最低限度上尝试去理解巴勒斯坦人为什么会在所有意识形态形态和历史表述中将一切武装/非武装形式的抵抗都看作是必要的,这是另一码事。实际上,这完全是一种傲慢粗鲁的行为,而且再考虑到教授们一旦对巴勒斯坦抵抗运动表示任何情绪或象征性支持就要遭到解雇的情况,这一行为就更显得自以为是了。
人们确实能够承认抵抗的必要性以及个体为争取并夺回他们所失去的东西做出的努力。去承认这部分内容,就超越了“受害者”的概念,然而巴勒斯坦的许多自由主义者和部分左翼就只是希望我们把斗争局限于“受害者”的概念——一种只会引起人们怜悯遗憾(pity)的巴勒斯坦主体性。
在西岸,虽然没有正式的武装运动或是严格的意识形态组织,但也出现了非正式的小型团体——信任圈、友谊圈和超越意识形态界限的小规模武装单位。这意味着任何分析都应该从现实出发。将理想化的、僵化的框架投射到政治团体身上,不仅没有帮助,而且是智力上的懒惰,也是在对这一代人将继续抵抗的事实置若罔闻。
[抵抗是一种必然,即使在军事化的过程中,它也是在实实在在的物质现实中成长起来的,而不仅仅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选择。]
抵抗是前-政治的。它有机地存在于这一代巴勒斯坦人中间。这一代人继续被从自己的土地上抹去,继续失去他们的朋友和亲人。正是那些势力很好地组织起这种潜在的抵抗,并最终成为巴勒斯坦社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抵抗是一种必然,即使在军事化的过程中,它也是在实实在在的物质现实中成长起来的,而不仅仅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选择。
和往常一样,人们普遍担心的是,在重大意识形态分歧的掩盖之下(我也与这些势力存在这样的分歧),我们对抵抗的批判恰恰会成为对抵抗之可能的摧毁。

哈马斯只是众多为冲破以色列强加的铁墙而发起的政治项目与历史尝试之一。它可能失败,也可能成功,但它做过的事情是其他巴勒斯坦社会进步力量都曾尝试做过的事情。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加沙的哈马斯并不只是什么外部势力或是什么进口品。它与广泛社会结构有着内在的交织。至少,它不应该因为什么在用“倒退”对抗“进步”而轻易遭到否定。
哈马斯不会在巴勒斯坦政治中消失。它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政治实体。从其前身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战争和谈判中的错误中,哈马斯敏锐地吸取了教训。它已经将智识、政治和军事资源精心投入到对以色列及其心理重心的了解中。无论我们喜欢与否,哈马斯现在都是领导巴勒斯坦斗争的主要力量。
左翼必须正视这一基本事实。我们不能把声援巴勒斯坦建立在否定、忽视乃至排斥哈马斯之上。这种立场未能把握巴勒斯坦斗争固有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若是拒绝这一点,左翼就会忽视(与以色列进行)合作与抵抗之间的分界线,最终使得抵抗岌岌可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