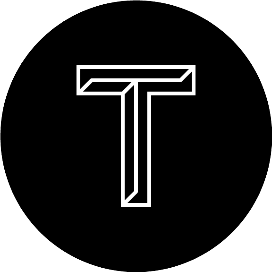2023 年 10 月,行为艺术家、独立导演张维离开常居地上海,前往拉丁美洲开启长达近半年的旅居。12 月,她在古巴旅行了 21 天。从哈瓦那(Havana),特立尼达(Trinidad)到圣克拉拉(Santa Clara),她边旅行、边创作,结合影像记录与即兴写作,整理了例如「我拍了 50 栋带躺椅的古巴房子」「我在古巴拍的 30 杯咖啡」「古巴街头家庭『小卖部』」「我可以给你拍张照片吗?」等趣味观察。
她的古巴梦始于音乐。1988 年,导演 Wim Wenders 跟随音乐伙伴 Ry Cooder 来到古巴拍摄乐队 Buena Vista Social Club(远景俱乐部)。这是一群早已被遗忘的民间艺人,他们大多出生于 20 世纪初至 40 年代,有嗓音独特的歌者,也有技艺精湛的钢琴师。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寂寂无闻,为谋生而焦虑,但从未放弃音乐。随着同名电影《乐士浮生录》(Buena Vista Social Club, 1999)上映,乐队及古巴音乐逐渐被世界看见。
2020 年,张维一边进行个人创作,一边撰稿谋生。她在手记中写:「很多个日夜,我循环着『远景俱乐部』的音乐。旋律响起,身体便感到自由。我想知道:古巴人为什么这么快乐?」
「古巴的音乐贯穿在大街小巷,在卖菜的手推车上,在兜售廉价面包的自行车上,在破烂不堪的门洞里。」音乐把张维引向了古巴,但由此展开的,已不仅仅是音乐。「又爱又恨」是张维对古巴旅居体验的总结。在她眼中,「21 世纪的古巴仿若加勒比海中的一叶扁舟,它似乎还停留在半个世纪以前,人们都去古巴寻欢作乐,但又纷纷想要逃离。 」
自 1492 年被西班牙探险家哥伦布发现后,古巴经历了 400 多年的殖民史。1902 年,古巴正式独立。1953 年,Fidel Castro 发起古巴社会主义革命,领导古巴走向 21 世纪。尽管具有相似的社会制度,人们对其印象依旧充满想象。抛开想象,张维的写作打开了一个认识古巴的视角,她称之为「始于音乐,止于食物」。以下是她的写作。

「我通常让客人带一些食物来分享,像干水果,杏仁,开心果之类,既然你从墨西哥来,可以带点玉米饼吗?」看到 Patti 昨天晚上发的信息时,我已在墨西哥坎昆机场,准备飞往古巴。「机场没有玉米饼,」,我很抱歉地回复她,「但我会找到一些其它的食物带过去。」
Patti 是我在古巴哈瓦那的「沙发主」。出发前 3 天,我打算先预订哈瓦那的第一晚住宿,但打开 Booking(国际旅行住宿网站),输入「古巴」,结果一片空白。于是我打开了沙发客 APP,在其中看到了大量的古巴房东。
沙发客是一个为全世界旅行者提供住宿的软件,任何人都可以作为沙发主或沙发客,为他人免费提供或申请住宿,女性沙发主数量通常不到男性的十分之一。Patti 是哈瓦那较活跃的沙发主,头像中阳光漂亮的她仰面躺着哺乳孩子。她强调,优先接待独自旅行的女性。我毫不犹豫地发出申请,她很快回复了我。她有一个独立的房间,但房间没有门和窗户,她发来视频,让我考虑一下,「你在这里很安全。」

2023 年 12 月,我从墨西哥抵达古巴哈瓦那。从哈瓦那机场到市区,只有一辆公交,需要走约一个小时到车站,再等一两个小时挤上公交。那时已晚上 10 点,我决定搭出租车,费用从 30 美金还价到 25 美金。一路上既没有路灯,也没有别的车灯,仿佛进入另一个世界。半小时后,它在市中心横纵交叉的小街道里绕绕转转,停在一栋殖民时期的老房子前。昏暗的街灯亮着,街道两边的人兴奋地起哄,一种亲切感生起,就像你在深夜抵达中国的某个村庄,还未睡着的人们都会从窗前张望,是谁来了?
一个棕色皮肤的矮壮男人在门口接待了我。他热情地接过我的背包,迎我进屋,从里面将大门关上。那是一扇老旧的深色木门,上面挂着一把旧锁。门顶部四分之一处破了个洞,被用一块木板堵住。客厅只有一张破旧的圆木桌和三四把椅子,墙皮脱落,露出底部的灰土。古巴男人兴奋地招呼我坐下,告诉我他的祖先有中国血统。他的妻子和八九岁的女儿也出来看我,前者有一种病态的瘦,表情平淡,总是坐在 2 楼的走廊对着天井发呆。我后来知道,他们在这里等待时间。
Patti 来了。25 岁的她瘦瘦高高,眼睛深邃,笑起来一口白牙。她的怀里抱着一个不到两岁的孩子。Patti 带我去了 2 层房间,地上有一张用旧海绵块拼成的床,一个电风扇,一个旧衣柜,这便是我将入住的房间。迎接我的古巴夫妇和他们的女儿住在我隔壁。我们的房间都没有门窗,只用一块布遮挡着。Patti 和家人住在 3 层的小屋,屋内设施也很简陋,两把椅子和一张桌子,地上的床同样是用旧海绵拼成的。小屋外有一个宽阔的天台,墙上布满着彩色的人体墙绘。

在古巴,门前有蓝色标记的房子可以出租,一晚 10 美元到几十美元不等。近几年,古巴人开始把自己的房子放在 Airbnb 上,但游客只能在古巴之外的国家进行预订支付,且租金将先进入政府账户,之后由政府分发给每个房东。当然,古巴也有针对游客的酒店,可以在境外预定,只是价格昂贵,100 美元一晚很常见。因此,很多古巴房东在沙发客平台租房赚钱。但 Patti 的房子太简陋,又没钱修缮,难以出租,所以她想通过免费接待沙发客,认识世界各地的朋友,并且交换一些在古巴买不到的食物。
除了我,Tony 也是这里的沙发客,睡在 3 层小屋的地板上。他刚结束 3 周的古巴旅行,从西边回到哈瓦那,计划前往阿根廷。我把带来的食物都给了 Patti,她马上拆开零食,和大家分享。她为我做了晚餐,给我热了一根中午剩下的羊排和一点米饭。她端着这份稀有的食物对我说,古巴的羊排很好吃。

第二天早上,我在街头的叫卖声中醒来,和 Tony 一起出门。清晨的哈瓦那很热闹。街上林立着一排排上世纪殖民时期的建筑,多已褪色,颓圮破败。在破损的古建筑上,斑驳墙绘呈现出一种奇怪的张力。有动物,女人,也有政治明星 Raúl Castro 和 Che Guevara。尽管在漫长的殖民史中,900 多幢巴洛克和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大多保留原状。但直到 20 世纪初,独立后的古巴仍受独裁统治和美国干预,经济持续疲软,导致这些建筑年久失修,破败不堪。Tony 像个向导,他指着一栋只剩下黑框架的老建筑,对我说:「很可惜。」
Tony 在街角买了两块披萨,又在路边买了两根廉价雪茄,边走边抽。一个个高、头发凌乱的黑皮肤女人盯上了他,身着的黑色长裙更缩窄了她的纤细体型。他给了她一根雪茄和一块披萨后,她才离开。喝完最后一杯咖啡后,Tony 把最后一张皱皱巴巴的 15 比索给了我。他身上有着一直在路上的疲惫感,但也有一种轻快 —— 旅途快到尽头,他很开心马上要离开古巴。
但古巴于我仍是新鲜的,我开始配备古巴货币和电话卡。先是换汇。官方汇率显示美元对古巴比索(CUP)是 1:24,但当地黑市的汇率比是 1:270 或 1:260。哈瓦那街头到处都有人喊着「换钱、换钱」,但安全起见,我决定跟 Patti 的朋友以 1:260 的汇率换 100 美金。我们坐在客厅的桌子边交易,她从包里掏出一堆零钱,5、10,最大面值是 100,Patti 数了半小时。这些钱握在手上足有砖头厚,根本无法塞进我的小旅行包。换好钱,我去国营电话公司买了一张本地电话卡。保安极其礼貌地领我到柜台,一个女职员帮我安装了电话卡,却无法使用,她耐心地将我的手机重启调试,半个多小时后,终于调试出微弱的 3G 信号,她无奈地耸耸肩。
重新走在哈瓦那的街道上,看着路边极小的家庭杂货店,马路中间高高堆起的垃圾,门洞里坐着的古巴老人。有几个瞬间,这里让我想到中国上世纪的农村或县城,又或是广州的城中村,亲切,可接近。但转念一想,哈瓦那多了点什么。一辆载着音乐的三轮自行车小贩经过,年轻的黑皮肤男孩对我举起剪刀手,露出白牙齿 —— 多出来的,是我渴望的音乐。

音乐是古巴人的魂。到古巴的第 2 晚,Juanma 和 Patti 把房间清空,策划了一个黑人艺术家的展览和乐队演出。演出过半,突然下起大雨,人们搬到室内继续,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身体挨着身体,忘我地扭动。有天早餐,Juanma 放起音乐。吃着吃着,一首「远景俱乐部」的歌响起,快活、开阔的嗓音让我兴奋不已,Patti 情不自禁跟着唱起来,她举着面包,站起来跳舞,Juanma 抱住她,两人随着音乐摇曳。
又一天,我被楼下一种非洲的祭祀音乐吸引。进去一看,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很小的临街客厅里,墙边祭台上,粉色的布折成了坐佛模样,两根红色的粗蜡烛摆在两边,4 个乐手即兴演奏,乐器有非洲鼓,和一些我说不上名字的。询问后得知,他们每周六都会有这样的祭祀活动。一个买菜路过的女人、一个提包的男人也被吸引进来,他们站在狭小的空间里扭动身体,臂上还挎着包,跳了很久后,又默默离开。

很长一段时间,古巴音乐被世界忽视。18 世纪,为了补充劳动力,西非黑奴被贩卖到古巴,他们结合西班牙殖民者的天主教信仰,创造类一种名叫 Santeria 的新兴宗教,随之出现了各种舞蹈和音乐。现在的古巴音乐正是西班牙殖民音乐和黑人歌舞文化结合的产物。古巴革命后,政府对音乐的支持有限,古巴传统音乐日趋势微,直到 1996 年的英国独立唱片公司 World Circuit 到古巴录制专辑「远景俱乐部」,它的成功使得古巴音乐重回世界乐坛。
在古巴,每个人都是歌唱家,每个人都是舞者。「远景俱乐部」的大部分成员很长时间都默默无闻,歌手 Ibrahim Ferrer 生于圣地亚哥的一个小镇 San Luis,父亲早逝,12 岁时母亲去世,成为孤儿。他一生贫穷,以卖唱、擦鞋、捡破烂为生。Wenders 的镜头跟随音乐家 Cooder 在街头寻找那些珍贵的古巴艺人,他们有的已经去世,有的可能还在,但无人知晓,Cooder 说,「我们要继续找,他们可能就在街上,在某个角落。」

音乐把我引向了古巴,但来到古巴后,由着音乐展开的已不仅仅是音乐。一天凌晨两点,我被古巴邻居外放的音乐声惊醒,但却不忍让他们关掉音乐。男人曾是电工,刚把房子卖了,一家人租住在 Patti 家,等待当月 23 日的航班去洪都拉斯,再偷渡到美国。我在深夜听到他们在隔壁大声讨论如何离开。
在所有充满血与泪的革命史中,古巴革命被形容为「诗意的」。法国导演 Agnès Varda 受「古巴电影学院」之邀前往古巴访问,制作了电影《向古巴人致意》(Salut les Cabuins, 1963),她在影片开头便提到,古巴革命太诗意了,因为他们在跳伦巴。
生于阿根廷富人家庭的 Guevara 坚信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拯救经受长久殖民和贫穷的拉丁美洲,他从阿根廷一路北上革命。1958 年,Guevara 和 Castro 等 82 个人带着理想主义的愿景,从墨西哥登上一艘小船,在加勒比海漂泊了 8 天,登陆沼泽,解放古巴。抵达时只存活了 12 个人。故事在被 Varda 重新叙述时,披上了浪漫主义色彩。Castro 成为古巴领导人,深受古巴人民崇拜。Guevara 则从古巴革命走向世界,成为了传奇的社会主义革命者,他的肖像出现在建筑和年轻人的纹身上。
理想主义过后,古巴人面临的是具体的生活。古巴政府开始实施计划经济,自 1962 年实行配给制至今。类似的配给制度曾在中国、越南和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存在过,但目前仅在古巴和朝鲜保留。政府发给每个古巴家庭一本类似上世纪中国粮票的配给小册子,人们可以到国营配给店领取食物和日用品,为了领到配给品,需要排队至少半小时。一家如中国公社模样的小店,橱窗里摆着稀疏的食品日化,人们在门口排着长队,这样的队伍在古巴处处可见。每个月的配给通常只够吃一周,不够的要自己购买。古巴人的平均工资在 20 美元左右,最受尊重的职业医生月薪 50 美元左右,工资相对比较高的是旅游业。幸运地是,古巴较早便实现了全民教育和医疗,人们念书看病不花钱,几乎 90% 的古巴人都识字。
古巴物资匮乏,街头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商店、超市,大型超市更是想也不敢想。反之,家家都是「小卖部」。一只牙膏,一根蜡烛,一个马桶,任何东西,你都可以摆在门口,或是窗台,标上价格。古巴的商品种类极其有限,除了没有坚果这样的零食外,卫生巾、尿不湿、止痛药等日常必需品也很难买到。
古巴的经济为什么这么差?当我在 ChatGPT 输入这个问题,得到以下答案 ——完全依赖旅游经济的古巴,在新冠疫情期间,经济完全停摆。如今在哈瓦那,大部分人都没有工作,他们成天坐在破败的房子门口发呆,刷手机。老人住在一堆垃圾里看路人。每当我出去或回来,古巴邻居都会带着笑脸来给我开门。我不清楚他的快乐是不是真的,但毋庸置疑,笑容背后,是他离开古巴的决心。他努力工作,存了一笔钱,卖掉房子,买到一家人飞去洪都拉斯的往返机票。每天晚上如果没有音乐,他们该如何打发那些漫长的夜。
「他疯了。」50 岁左右的 Juanma 这样评论古巴邻居。Juanma 是墨西哥城人,已在古巴生活了 8 年。他从 6 岁开始和叔叔一起旅行,住过英国、捷克、波兰和葡萄牙等 6 个国家。我问他为什么最终留在古巴?他说,20 年前他第一次来古巴就很喜欢,但如果那时让他在古巴定居,他做不到,现在他觉得自己不需要太多物质,只想看看电影和书,古巴很适合他。最近,他跟一个意大利导演,在哈瓦那郊区拍一个关于非洲宗教的电影。3 岁的 Marco 赤着脚跑来跑去,大部分时候,他捧着手机躺在地上看动画片。我问 Juanma:「他们也想留在古巴吗?」他思考了一下说:「Patti 年轻,她还想旅行。等 Marco 再长大一点,他们也许会一起出去旅行。」

加勒比海岸的建筑断壁残垣,海堤上有人在钓鱼,几米高的海浪浇在那人身上,而他纹丝不动。哈瓦那是分裂的、复杂的、矛盾的,不管是「理想主义的天堂」,还是「极权制度的地狱」,都能在这里看到。
从哈瓦那最东边到西边,从繁华的旅游区逐渐过渡到贫民区、中产区,再到郊区的富人区。我整日走路,一步步丈量这个城市带给我的冲击。距 Patti 家两条街之外是著名的普拉多大道,1920 年修建的铜狮子塑像和大理石长凳依然存留。跨过大道,就来到哈瓦那古城旅游区。这里给游客提供了「自由古巴」的浪漫想象:复古老爷车、风情音乐、200 美金一晚的酒店和 100 美金一顿的餐厅。一家海明威去过的酒吧,无论白天还是夜晚,都挤满了人。游客们到此打卡,尝 5 美元一杯的莫吉托。
而在另一边,是贫民区街头窗口递出来的 Cafecito,西语 Cafecito 是「迷你咖啡」的意思。浓浓的黑咖和糖一起煮成,两三口就能喝完。在哥伦比亚的街头也有 Cafecito,但没有古巴的迷你。迷你咖啡通常由街头的古巴家庭出售,价格便宜,10 到 20 古巴比索不等,人民币三四毛一杯,每个人都喝得起它。我迷上了这种咖啡,最后 6 天 ,我在 30 个不同的店里,用 30 个不同的杯子,喝满了 30 杯。
在经济下行的古巴,TikTok 变得流行。人们晚上不睡觉,在阳台上刷手机。网络让古巴人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也看到了自己的欲望。那是 2023 年 12 月,我走在街上,常常感到自己像一只行走的钱包。很多人跟我聊天,接着跟我要钱、衣物、药品,但我只有一些仅够维持我日常生活的衣物。
在哈瓦那夜晚的步行街上,一个女孩陪着我并肩走了几个街口,我为认识新朋友感到喜悦,但她突然问我,要买雪茄吗?我说,我不抽。她马上转身离开,留我在街头。在特尼李达,几个男孩在爬一棵树,征求同意后,我给他们拍了照,他们追着我喊「钱,钱」。一个妇女在巷子尾热情得跟我聊了很久以后,问我有没有药和衣服。
作为当地罕见的亚洲人面孔,我频频受到路人的注视。他们隔着马路对我喊:「Japan?Korea?China?」当他们知道我是中国人后,总要问我很多问题,其中最直接且频繁被问到的是:中国人很有钱吗?我不知如何回答。同是社会主义国家,古巴人对中国人感到亲近。曾经,哈瓦那的中国城是整个南美洲最大的华人城,最多时有 5 万中国人,但现在只有 50 人不到。中国城里,依然保留着一些仿华建筑、武馆和孔子学院,年轻的古巴人在那学习中文,期待来中国工作。

作为甘蔗殖民地大量产糖,中国的糖也曾从古巴进口。自 1840 年起,便有大量沿海一带的中国人远渡重洋来到古巴,从事甘蔗种植,与此同时,他们也带去了美食和文化。导演魏时煜拍摄的纪录电影《古巴花旦》(2018)呈现了一群从小在哈瓦那唱粤剧的古巴女孩,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华侨方标收养了古巴女孩何秋兰,并教她唱粤剧以解思乡之情。在方标组建的剧团里,15 岁的何秋兰当上花旦,巡演古巴,与来访古巴的小燕飞等伶人同台演出。但 Castro 的革命改变了这一切。这些在时代中沉沉没没的古巴女孩,用嗓子消弥国界。
旅行时,我喜欢去本地餐馆体验本地人的生活。在特立尼达时,我发现一家从外面看不错的本地餐厅,但走进去时,店员告诉我,没有食物招待。第 2 天,我再去,店开着,也依然没有食物。直到第 3 天晚上,店里才愿意接待客人,我是唯一一个。许久不营业的年轻厨师匆忙地一边系皮带,一边准备。服务员拿菜单给我选,但只有一个菜有食材。我边等待边观察这家位于街角的餐厅,两扇大门面向街道,空间宽敞,墙绘缤纷,这本该是家吸引人的餐厅,但现在,铺着的红桌布看起来像很久没有清洗。独自坐在那等待时,我感到自己和这个餐厅一起被遗忘了。
在我到达的头两天,一个从加拿大过来的中国人,跟我说了整整两小时,在古巴待了十天的他,说再也不会来古巴了。游客走在路上,常常被要钱,被兜售雪茄,也常常被骗。我遇到一个比利时人,被骗以 1:32.5 的汇率换了 200 美金。一个正在墨西哥的朋友让我给他一个来古巴的理由,我不知道。来寻找快乐的我,前半个月还乐在其中,但之后,我也开始厌倦于被要这要那。我渴望食物,在街头餐厅门口问:「有没有 tortilla(墨西哥薄馅饼)?」如果能吃上,我便感到满足。

古巴的吃住行基本都得用现金。在圣克拉拉,我盘点自己剩下的美金,发现很难撑到第 4 周。我又查询了通往古巴东边的汽车,接连几天都没有车票,时值圣诞节,很多欧美人来古巴度假。想了想,我决定 12 月 31 日晚离开古巴。
我要先返回哈瓦那。房东的儿子用电动车送我到汽车站。电动车在古巴是罕有的交通工具,人民币 8000 元左右,极少家庭才买得起。到达汽车站后,我拿出准备好的钱付给他作为感谢,但他拒绝了。这让我产生一种意外的欣喜和轻快,但同时也让我感到惭愧。很多旅行者在古巴很紧张,因为任何一次热情都有可能转变为潜在的消费,虽然不多,但常常让人感到不舒服。
当我和比利时朋友在山谷徒步时,在一个小驿站喝椰子水,喝到一半时,主人突然给我们倒酒,付款时,我们发现比原先点的东西要贵,才明白主人给我们倒的酒也是消费。这样的事发生多了,导致很多旅行者变得警惕。一次,我和路上遇到的日本女孩一起在餐厅吃饭,一个古巴男人过来要给我们演奏,拒绝无果后,日本女孩马上跑出了餐厅,她不想被迫为演奏付费。
当我再次回到 Patti 家,古巴邻居夫妇和他们的女儿已离开,我想象着,他们可能已经北上跨过河流、走过森林、爬过高山,作为难民去了墨西哥南部城市,正在等待获允去往美国,而在那之前,他们不能移动去往墨西哥其它地区。但在墨西哥,他们有丰富的食物和商品。我和 Patti 一起用发黄的旧海绵铺床。Patti 很快乐地告诉我,她很喜欢把海绵拼成床的过程。我们一起参加了哈瓦那沙发客聚会,认识了其他在古巴的沙发主,一个女沙发主在学校工作,她去过中国深圳。
在哈瓦那的最后一个晚上,我来到华人街吃晚饭。餐厅里,一个中国男孩一直在骂脏话。我点了一碗番茄鸡蛋面,吃到一半,餐厅停电了,我在黑暗中吃完面,又在黑暗中返回沙发主家里。深夜独自走在哈瓦那的街道上,地上到处都是污水,黑暗中有人在说话,我小心地走路,心里生出对这黑夜的熟悉感。
离开前,我把一些衣服、止痛药和创口贴等送给了 Patti 夫妇,他们很开心,他们需要这些。第 2 天上午,他们邀请我一起吃早饭告别,Juanma 说需要一些面包和鸡蛋,我出门去买鸡蛋,他去买面包,但是我在街上走了快一个小时,都没有找到鸡蛋,等我回来时,感到很沮丧,这时他们已经做好了早餐,以为我出了什么事。他们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但网络太差,我都没接到。

当我离开古巴后,依然有人问我,古巴怎么样?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它的复杂性让我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我总是回答:「爱恨交织。」有的旅行者会在游玩一圈后否定它,他们再也不想回来了。有的旅行者则盲目地热爱它,但如果你问他最长想在古巴住多久,他们会说:「不超过一个月。」
在我离开古巴两个月后,由于粮食短缺和停电,古巴圣地亚哥等省发生了抗议运动。我问候 Patti 一切可好,她说一些地区发生了动乱,但她那里还很安全。4 个多月后,我离开拉美回到中国,途径迈阿密机场,在那里遇到一位在传教的美国老太太,聊天发现她是古巴人,40 多年前来到美国,再也没回去过。
同拉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古巴是难得的被描述为「安全」的国家。在街头闲逛的时候,我总是抱着相机,遇到想拍的人,就问「我可以给你拍张照吗?」当我重新回看相机里的那些照片时,被镜头前那些毫无顾忌对我举起剪刀手的普通人打动。从老人到小孩,他们站在那,看着镜头,自信且自然。有时她正在收衣服,就停下来让我拍,一点也不紧张、不装饰、不着急。
在回到中国后,我在上海重新看《乐士浮生录》这部纪录片,情绪更加复杂。在影片最后,这些老乐士破例获邀进入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演奏。演唱完毕,Ferrer 第一次走在纽约的街道上,仰望着资本主义世界的高楼大厦和物欲横流的都市,发现世界另一面是这样的,他一边走一边感慨地说,希望把妻子孩子也带来,看看这些美丽的东西。
撰文 - 张维 编辑 - 吴嘉敏 图片承蒙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