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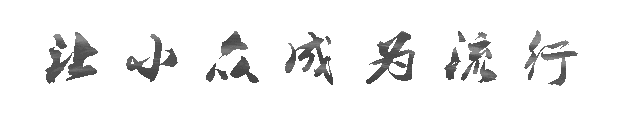
九十年代,在台北、高雄两地,有人曾用四年时间逐页讲解《红楼梦》。
在台北,听他讲《红楼梦》的成员大多是台湾政经大佬的太太或儿媳,名媛贵妇。
林青霞也是台北班的一员。
那时候,她母亲刚跳楼不久,父亲重病,每周五都需要从香港飞到台北照顾病人。重压之下,听这个人讲《红楼梦》成为了她一段特殊的修行。
在媒体采访时,
林青霞把他比作自己的半粒安眠药
,说他可以让自己在不许她胖、不许她丑,到处有人拍她哭、拍她笑的世界里找到坦然自在,和容易一些的睡眠。
这个人,就是蒋勋。

蒋勋与林青霞
台湾综艺大姐大张小燕说,那时她先生病逝,她痛苦地日夜难眠,林怀民跟她讲,要从黑洞中走出来。
她也想,但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痛整团凝结在心里,哭都哭不出来。
后来看到一首诗,诗的末尾说:
当你埋葬土中,我愿是依伴你的青草,你是灰,我便成尘,如果你对此生还有眷恋,我就再许一愿,与你结来世的姻缘。
那是一份有声读物,当听到作者温润清朗地念出这几句话,她大哭一场,终于从压抑的黑洞中走了出来。
几年后,这个作者上了张小燕的节目,小燕姐不无动情地说,是你救了我,让我如今变得这么从容平和。
这个人,也是蒋勋。

蒋勋与张小燕
1947年蒋勋出生在西安古城,那一年出生的还有侯孝贤,林怀民,陈芳明。
时间往前两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往后两年,1949台湾大迁移。特定的历史背景,造就了这一批人。
蒋勋是满清后裔,贵族出身,母亲是正白旗,外曾祖父是西安的最后一任知府,但他最初的记忆并非富贵繁华而是颠沛流离。

1951年他们一家逃到基隆,才得团聚。在母亲主张下,他们没有落户眷村,而是搬去了大龙峒。那里除了他们一家外省人,全是土生土长的同安人。
大龙峒民风淳朴,相互信任,关系紧密。没米了就去陈妈妈家借,邻居们拉着母亲一起做年糕,念书时有人会对他加以保护,这些记忆都深深地烙在了蒋勋心里。
多年后蒋勋把《红楼梦》讲给高雄的贵妇听,讲给菜场做咸菜的大婶听,菜场的大婶们听得很感动,给蒋勋递过来一条红内裤请他签名,蒋勋也就乐呵呵地签了。
读蒋勋的书可以了解到,他颇具人文关怀,不以上帝视角做评判,常常换位思考,尊重每一个人,这让很多人觉得,蒋勋的文字跟话语能走进他们的内心。
蒋勋说这源于大龙峒,那里的民风教给他很多。

年轻的蒋勋(左一)和丁玲(中)合影
大龙峒的清贫生活教给蒋勋的,不光是待人处事,他对美学的概念也是在这里建立的。
那时的庙口是文化的中心,他在这里听南管,看人家画吕布戏貂蝉。
有时流浪戏班开着破烂的小货车演戏,满头珠钗的千金小姐在幕后奶完孩子又匆匆整好衣衫在台上继续花好月圆。
这些经历让蒋勋觉得,艺术最重要的,
是背后的生活哲学。美学的教育不需要以富有为前提。

大龙峒保安宫
后来蒋勋念书了,初中念得是很有名的师大附中,之后
却
去了当时最差的强恕中学,但蒋勋觉得那是他这辈子的好运气。
强恕的老师大都不在体制内,玩得很疯。
蒋勋在那里自由地野蛮生长,看《等待戈多》,读存在主义,那时的他才15岁。
毕业时,英语老师陈映真给了蒋勋八个字:
求真若渴,爱人如己。
这成了蒋勋的人生信条,日后的讲座,他没有猎奇,不会过度解说,所讲内容富有人性,带着温度。

蒋勋幼时(左一)
1972年,25岁的蒋勋第一次离开台湾,前往巴黎留学。
蒋勋在巴黎的第四年,和一个法国朋友在街上走,突然闻到一种气味让他想哭,他跟朋友讲,那是他在凤山当兵,太阳把泥土晒得发烫,暴雨落下,土跟青草整个翻起的味道。
朋友说,那个叫乡愁。那一年的十一月,蒋勋飞回了台湾。
蒋勋这样写自己:在闹市的繁华中,忽然被一名算命的男子叫住,先生,我跟你说句话,你和出生地无缘啦。
妈妈的乡愁在西安,父亲的在福建长乐,他的在台湾。

回到台湾后,他用三十几年的时间,用自己温暖平静的声音让一个又一个躁动的灵魂静下心来感受和触摸这个世界。
他讲共生的孤独
“孤独是不孤独的开始,当惧怕孤独而被孤独驱使着去找不孤独的原因时,是最孤独的时候。”
如果“孤独”曾是一种不得以而为的状态,那么蒋勋先生的叙述中,它成为了使生命饱满的要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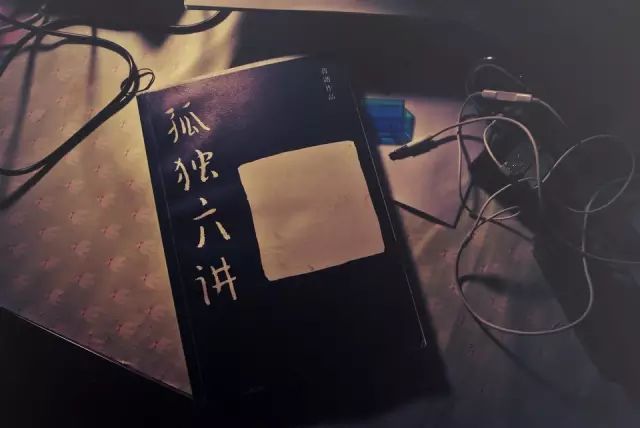
《孤独六讲》蒋勋著
“《红楼梦》的作者通过一个一个不同形式的生命,使我们知道他们为什么‘上进’,为什么‘洁癖’,为什么‘爱’,为什么‘恨’。
生命是一种‘因果’,看到‘因’和‘果’的循环轮替,也就有了真正的‘慈悲’。”
曹雪芹用十年写了一部未完的小说,而蒋勋在三十年里,将它放在案头,反复咀嚼研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