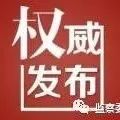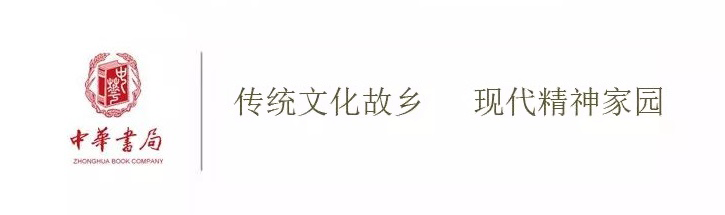
傅璇琮先生(1933—2016),著名学者、出版家。浙江宁波人。1951年至1955年,先后就读于清华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助教。1958年3月调至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后因出版分工调整,进入中华书局工作,历任中华书局文学组编辑、古代史编辑室副主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总编辑。2008年受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秘书长、副组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特聘教授,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等。
今年是傅璇琮先生诞辰90周年,《傅璇琮文集》已于近期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较为全面地呈现了傅先生在各个方面的成就。
今日节选《驼草集》中收录的傅先生撰《我和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一篇,以表达我们对傅先生的深切怀念之情。
1958年初,因所谓办“同人刊物”,当时北大把中文系的八个年轻助教、研究生打成右派反动集团,其中有乐黛云、褚斌杰、裴斐、金开诚和我。我即于当年3月从北大贬出至商务印书馆,六七月间又分配到中华书局,至今整整四十年,除了“文革”十年,及1987—1988年有半年时间去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讲学外,没有离开过编辑部。
我自己一直认为,我真正进入研究工作,并在学术领域作出一定的成绩,是在出版社,我的学术研究,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这样有历史文化传统的出版社是分不开的。

我进商务的时候,商务有一古籍编辑室,室主任为辞书编辑专家吴泽炎先生(即商务出版的新修订本《辞源》实际主编)。吴泽炎先生打算在由云龙旧编的基础上重编《越缦堂读书记》,他可能觉得需要一个助手,也或许看我刚从北大贬出,得收收心,就叫我帮助他做这一项事,步骤是将由云龙的旧编断句改为新式标点,并再从现存的李慈铭的日记中补辑旧编所漏收的部分。
李慈铭是绍兴人,也可以说是我的浙江同乡,小时读《孽海花》小说,对书中所写的他那种故作清高的名士派头,感到可笑,但对他的认识也仅此而已。现在是把读他的日记当做一件正经工作来做,对这位近代中国士大夫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及其坎坷遭遇了解稍多,竟不免产生某种同情。那时商务是在东城北总布胡同10号,整个布局由几个四合院组成,都是平房。我们在的古籍编辑室正好是北屋西头,面对的是一个颇为典雅幽静的小院子。
我是住集体宿舍的,住所就在办公室后面一排较矮的平房,起居十分方便。一下班,有家的人都走了,我就搬出一张藤椅,坐在廊下,面对院中满栽的牡丹、月季花,就着斜阳余晖,手执一卷白天尚未看完的线装本《越缦堂日记》,一面浏览其在京中的行踪,一面细阅其所读的包括经史子集各类杂书,并在有关处夹入纸条,预备第二天上班时抄录。真有陶渊明“时还读我书”的味道,差一点忘了自己罪人的身份。(《热中求冷》,《濡沫集》页96—97,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我就这样细细阅读了当时被人漠视的李慈铭日记,这在大学恐怕是不大可能的。正因为如此,使我对晚清社会及文人生活有了具体的了解,开始有兴趣读近代人的诗文集和笔记杂著。那时商务的古籍编辑室人虽不多,但专业空气很浓。赵守俨先生特地把由他整理的俞正燮《癸巳类稿》、《癸巳存稿》给我看,后来他又起草写《唐大诏令集》出版说明,在编辑室内传阅。我觉得这篇出版说明把《唐大诏令集》成书经过及文献价值与某些缺失,说得清楚实在,我当时就感到,这篇文字,在当时北大,恐怕是很难有人能写出来的,这确是专业编辑的实功夫。

赵守俨
这年六七月间,商务的古籍编辑室取消,成立《辞源》编辑室,吴泽炎先生留下来专职主持《辞源》的修订工作,我们大部分人则转移到中华书局。当时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为金灿然同志,他在延安时曾与范文澜先生一起编写过《中国通史简编》,应当说也是一位行家。我刚到中华,他就告诫我:要在工作中好好改造,把工作做好。他确实是爱惜人才的,并不像当时流行的动不动把右派放到农村中去劳动,而是把我圈在书稿中。他与一般职工一样,中午也坐在食堂吃饭。一次他与我同桌,问我:“你们北大中文系像你这样的,还有没有?”我就举出几个,他随手就记下来。
后来,褚斌杰、沈玉成就从北大调来,他们当时都是戴着右派帽子的,从西郊斋堂的劳动场所调来读古书。

金灿然
我到中华,最初是在古代史编辑室,当时室主任是姚绍华先生,他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老中华书局留下来的。我印象很清楚,我刚来到,就交给我明末李永茂于崇祯十五、十六年在兵科给事中任内的两件疏稿:《邢襄题稿》和《枢垣初刻》。这是抄本,由河南开封孔宪易提供,中华书局得到后请人整理断句,已排出校样,但尚缺一篇出版说明。不知怎么,这篇出版说明竟叫我这个二十五岁的戴帽子的年轻人来写,而我在学校时又不是搞历史的。但我当时还是硬着头皮写了三千字,开头一段是这样写的:
崇祯十五年松山战役以后,清军对明的包围形势已经形
成。皇太极曾说:“取北京如伐大树,先从两旁斫,则大树自仆。……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四围纵略,北京可得矣。”就在这年十一月,清兵分道入关,先陷蓟州,深入畿南,直趋曹、濮,连下山东八十余城,鲁王以派自杀(见《明史》卷二十四)。明朝政府面对这样紧张的局势,一面派人督师抗击,一面遣六科给事中分别察理近畿各府城守情形,李永茂当时即奉命视察顺德府(府治在今河北邢台市)属的城守,并以其察理所得的闻见及对防守的意见,奏报朝廷,结集成为《邢襄题稿》。永茂后以崇祯十六年正月事毕返京,上奏对待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和清兵的攻守策略,约三十几疏,为《枢垣初刻》。
我之所以抄录这一大段,是我当时有一想法,就是
一部书的出版说明,尤其是较冷僻的书,应当在一开始就要用浅近明白的文字交代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书,不管你在写作之前已查阅过多少资料,但不能把这些资料堆积出来,而应当将这些资料,经过理解、概括,用自己的笔写出来。
这也是我第一次用我自己所学的中文某些优势来处理历史文献资料,也从而克服我对历史的畏难情绪,并培育我文学与史学相结合作综合研究的兴趣。
大约8月份又把我调到文学编辑室,一起搞《新编唐诗三百首》(此书后在“文革”中受批判,说是邓拓为此书所写的序言借机反对1958年的三面红旗,实在是无稽之谈)。此后当时文学室主任徐调孚先生又交我一部稿,即经顾颉刚先生校点的清人姚际恒《诗经通论》,叫我写出版说明。《诗经》我只在大学上文学史课时学到一些,那时只看过一些选本,从来没有通读过。这次为写出版说明,我几乎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不但通读《诗经通论》,还参读郑振铎《中国文学通论》一书所论毛诗序,以及朱熹的《诗经集注》,清代的其他几部所谓疑古之作(如方玉润等)。我觉得,关于《诗经》,我是在中华书局补了北大所未学过的几部名著的。
就在这时,王国维的次子王仲闻先生被临时雇用到中华书局来。这位王先生本在邮电部门工作,说是1957年划为右派,又有国民党的问题,于是右派加反动派,开除公职。他对唐宋诗词极熟,不知是谁介绍,来中华作临时工,具体是作清修《全唐诗》的点校工作,作了两三年,作得极细。印行时,1959年4月,徐调孚先生又叫我写一篇《点校说明》。我在说明中论述了《全唐诗》的问题:一、误收、漏收;二、作品作家重出;三、小传、小注舛误;四、编次不当;五、其他(多处讹夺,如《唐诗记事》误为《诗话总龟》,《唐摭言》误为《北梦琐言》,“来护儿”夺为“来护”等)。最后下一结论,为:“可见这部《全唐诗》实有重新加以彻底整理的必要。但这尚待进一步努力。”这时我还不过二十六岁,在此之前没有研究过唐诗,而此时也正在作宋代作家作品的资料辑集,但我还是根据王仲闻先生的点校材料,作了一定的概括。这也算是我今后研治唐诗的意料不到的开端。
徐调孚先生新中国成立前在开明书店就是名编辑,并且作过《人间词话》校注,翻译过《木偶奇遇记》,很有名气。他看稿极认真,而对人极宽厚。写这篇《全唐诗》的点校说明时,我与王仲闻都还有政治问题,但他还是在篇末署了“王全”,王即王仲闻,全即璇,因徐先生是浙江人,又长期在上海工作,那边是把璇念作全的。由此可见徐调孚先生在当时政治环境下也并不没人之功的气度。(附带说一下,王仲闻先生在1962年说是经调查,在档案中没有1957年划右派的材料,就不算右派,而他过去在邮电部门,是集体加入国民党的,因此也不算什么问题。此后几年在为唐圭璋先生《全宋词》加工过程中,著有三四十万字的《读词偶得》一书,中华曾请钱锺书先生看过,钱先生誉为奇书。但王先生在“文革”中又被街道红卫兵迫害,出走不知所终,其《读词偶得》一书也随之亡佚。)

徐调孚
我之所以在这篇介绍自己治学经历的文章中写这些年轻时旧事,是想说明一个情况,一个人,即使长期在出版社工作,不在大学或研究所,也能学有所成的,我记得那时我就立下一个志愿:我要当一个好编辑,当一个有研究水平的编辑。
我那时就想尝试一下,在出版部门,长期当编辑,虽为他人审稿、编书,当也能成为一个研究者,我们要为编辑争气,树立信心:出版社是能出人才的,编辑是能成为专家学者的。
我想,编辑当然首先要把本职工作做好,审读稿件,把住质量,开阔视野,组织选题,但同时还要提高本身的文化素质和学术修养,尽可能使自己在某一专业领域发展。学术研究与审读书稿,是互为影响、互补互长的。中国的出版社,与外国一些纯粹商业店家不同,它还带有一定文化学术机构性质。我曾说过,回顾20世纪的出版史,凡是能在历史上占有地位的出版社,不管当时是赚钱或赔钱,它们总有两大特点,一是出好书,一是出人才。我们一提起过去的商务,总会自然想起张元济、沈雁冰、郑振铎、傅东华;一说起开明,就会想起夏丏尊、叶圣陶、徐调孚、周振甫。50年代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有冯雪峰、周绍良、顾学颉、王利器、舒芜;而中华书局五六十年代则有张政烺、陈乃乾、宋云彬、杨伯峻、傅振伦、马非百、王仲闻。出版社要具备文化学术意识,就得在编辑部门中有专门家、学者,他们可以不受某种潮流的冲击,甘心于为文化学术事业而执着一生。
(上文节选自《驼草集》,原标题为《我和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傅璇琮文集》收录傅璇琮先生著作七种,包括其个人著作《唐代诗人丛考》《唐代科举与文学》《唐翰林学士传论》《李德裕年谱》,合著《李德裕文集校笺》《河岳英灵集研究》,另将其1956年至2016年间发表在报刊杂志和收录于文章专集的单篇文章,包括学术论文、杂文、随笔,以及所作序跋、前言、说明等三百六十馀篇,依时间为序结集为《驼草集》。
本书对初唐、盛唐及中唐前期32位诗人的生平事迹及著述情况作了详密考证,或填补空白,或订正错误,资料翔实,论证严密,多发前人所未发。本书还对所考诗人的创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以及当时的诗坛和诗歌流派,作了宏观的考察,力求总结出文学史的发展规律,特别是对大历时期南北不同诗人群体的分析,开启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唐代文学研究中群体研究的新风气。本书初版于1980年,学术界认为这部著作的出版“一下子便把唐文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

《唐代科举与文学》(全二册)
傅璇琮 著
本书在梳理唐代科举制度有关文献的基础上,考述唐代取士各科,如明经、进士、制举等的情况,考察了唐代科考的科目设置、内容沿革、贡举、举子行卷、放榜宴集等活动,探讨了科举制度对当时文学风气、社会风尚等的影响。其以史学与文学研究结合的办法,综合考察古人在历史记载、文学描写中的有关社会史料,研究唐代士人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心理状态,并着力重现当时部分的时代风貌和社会习俗,在研究史上开一时风气之先,影响深远。

《唐翰林学士传论》(全四册)
唐朝翰林学士是文士参预政治的最高层次。在盛唐设置的这一颇有文采声誉的职位,一直延续到清朝末世。作为社会政治文化的一种重要现象,作为封建时代文人的必然就仕之途,科举制与翰林院,进士与翰林学士,是研究唐至清一千二三百年历史文化所不可回避的。本书为有唐一代二百余位翰林学士一一立传,尽可能扩大史料的辑集面,除两《唐书》及《全唐诗》《全唐文》等基本材料外,还较广泛地涉及诗文别集、杂史笔记、石刻文献等,既可纠正史书中的某些误载,又可从这二百余位翰林学士经历中获取值得思考的历史文化现象,为整个中国古代翰林学士研究提供一个文史结合的实例。

《河岳英灵集研究》
本书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有关《河岳英灵集》及编选者殷璠的评论、考证,后一部分是《河岳英灵集》的整理点校。《河岳英灵集》是唐人所选唐诗的一种,在中国诗歌史和文学理论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它不仅保存了若干唐人的诗,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其提出的兴象说、音律说,还鲜明地反映了盛唐时代诗歌高峰期的创作特色和理论特色。本书对《河岳英灵集》的价值和特色作了探索和研究,并进行了清本正源的整理,恢复其两卷本的本来面貌,又结合明代流传的几种版本加以汇校,以期为理论探讨提供较为扎实的材料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