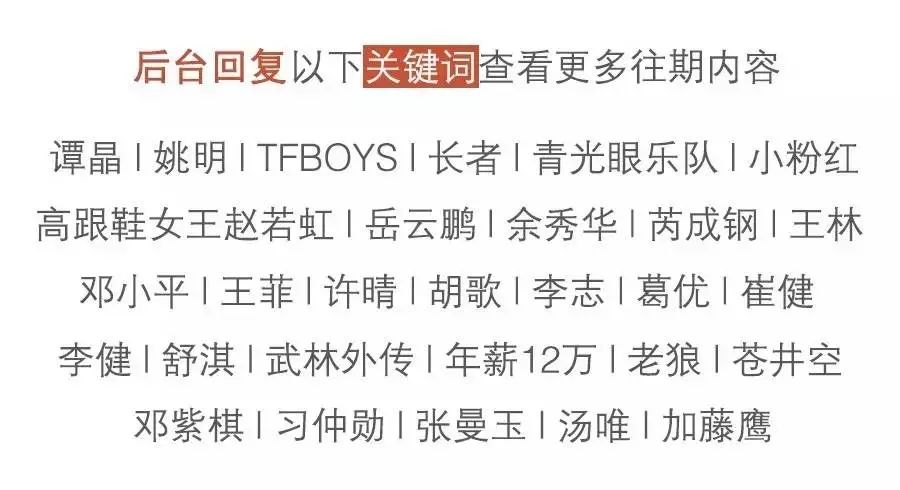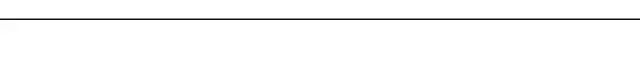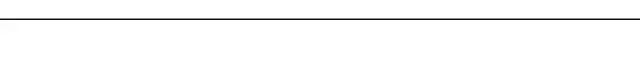文
✎
丁雪
图
❏
袁蓉荪
编辑
✎
卜昌炯 王唯一
1982年春,重庆大足石刻。梳着偏分戴着黑框眼镜的袁蓉荪没来得及掸去白衬衫上的灰尘,在31米长的宝顶山卧佛旁留下了一张与大足石刻里最大一尊佛像的合影。
他搭着雅马哈125摩托车,一大早出发,沿着成都到重庆起起伏伏的山路,颠簸了一天,风尘仆仆赶到大足宝顶山。
景区人很少,冷冷清清。满山栩栩如生的石刻闯入袁蓉荪的眼帘。他在佛像前伫立了很久,用海鸥4B拍光了两个黑白胶卷。
这是他第一次长途跋涉与佛像发生连接。此后30多年里,袁蓉荪带着他的林哈夫4×5页片机,背着大摄影包,走遍中国的东西南北,拍摄了成百上千个石窟造像。
佛,在人们印象中,通常是高大、神圣、庄严的存在。在袁蓉荪的相框里,它展露出自己温柔的一面,看起来更像是信众生活的背景,慈眉善目地端详着人间的日常。
佛与人的关系,在袁蓉荪的镜头里被重新建构。
开始的原因并不复杂。
2005年,袁蓉荪从四川广安到肖溪,古道间一截树枝从灰色的石刻中爬出来。石刻上残存着朱砂、石青,石纹和石花也斑驳可见。这种“生命轮回感”让他感动。
“那一瞬间,感觉千年古老的石刻又长出了新的生命。”袁蓉荪对《博客天下》说。
他觉得,“这就是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之后他辞掉了在部队企业的工作,专职拍摄佛像。
佛教提倡遁世隐修,印度的僧侣们常选择幽僻之地开凿石窟,观赏修行。伴随着佛教从印度传入,石窟这种艺术形式也逐渐在中国开枝散叶。
袁蓉荪不仅拍佛像,也拍佛像注视下的芸芸众生。找寻天南海北的佛像并不容易,但有时也充满惊喜。

2014年12月,四川安岳县高升乡三仙洞,明代佛龛。信众自发在这里做仪式。
2007年,袁蓉荪在资料上发现孔雀明王像,想亲自去看一下。按图索骥,沿着坑坑洼洼的路,他找到了四川安岳县,却什么都没有看到。
他又找到孔雀村,在传统安放佛像的寺庙,依然毫无所获。
“孔雀洞在哪儿?”“孔雀明王像在哪儿?”不知问了多少人,袁蓉荪才问到一些线索。翻过山坡,按照村民的指引,他在一个破败的瓦房外停了下来。一个50多岁的老人开了门,他就是周世夏。
穿过黑乎乎的走廊,灶台下闪烁着点点火光,炉火映照中,一尊高大精美的宋代孔雀明王像就在周世夏家的厨房里,地上散布着玉米秆。
土改时孔雀明王庙分给了周世夏的爸爸,一家人世代在这里劳作生活。后来因为需要厨房,他们在旁边搭了一个棚,避着风口生火做饭。
“‘文革’的时候,红卫兵要炸孔雀明王像。炸药包都带来了,但因为造像在厨房里,没办法下手,只好把炸药包又带走。”周世夏像一本尘封多年的书,不断向来来往往的人打开自己,津津乐道自己和孔雀明王像的故事。
为了不被人发现,他一度用柴火、玉米秆把孔雀明王像遮住。
如今,因循古迹的人们再也不会有这样的奇遇。为了更好地保护,厨房已经被拆除,孔雀明王像露了出来。周世夏以文物管理员的身份,住进了旁边不到一百米远的砖瓦房。
一些佛像散布在荒山野岭里,拍摄意味着艰苦地跋涉。
2009年9月,四川安岳县茗山寺庙会的日子,20多个老人,从四面八方的村子赶来。他们从离大路很远的地方走到山脚,再从山脚爬上1000多米的高山。芳草萋萋,6尊佛像倚在苍茫的青山里。
狭窄的山道上,老人们一个挨着一个,排着队烧香拜佛,祈求五谷丰登,风调雨顺。
被这样的虔诚感动,袁蓉荪站在坡底,靠着一棵小树,架着相机按下了快门。
他流连于山间的石窟,不知不觉夜幕降临。因为山路难走,只能在山里留宿。从山顶下来十多米,有一个小房子,里面住着文物管理员。袁蓉荪被临时安置在这里。
一张小床、两张椅子的小屋容纳不下更多的人,当晚文物管理员回了自己山下的家。
担心精美的佛像有所闪失,袁蓉荪一晚都没敢合眼。几个月前,这里发生了一起佛像偷盗案。文物管理员听到声响,盗贼扔下佛头,落荒而逃。
雨断断续续地下了一夜,这给第二天的离开造成了很大麻烦。山上都是黄泥路,下过雨后,像淋了油一样。走到山脚下,袁蓉荪的车停在那里。车一发动就开始滑,方向完全失控。他只好配合不听使唤的车轮,小心翼翼地沿着陡峭的山路下行。十几公里的路,越野车滑下去4次,后来直接滑到了沟里。
同行的居士婆婆叫来了住在周围的大爷大妈。十来个人垫着扁担、绳子、木头,把车推了出来。
这不是袁蓉荪第一次碰到这样的麻烦。2015年去甘肃东部拍石窟时,他也有过类似经历,最后不得不找拖车把车拖走。

2015年12月,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麦积山石窟,隋代一佛二菩萨。这是东崖第13窟,麦积山最大的造像“华严三圣”窟,隋代开凿,后经宋代重修。
更经常的时候,他需要面对的是狭窄的山路。每当迎面驶来摩托车时,袁蓉荪都要一点一点儿往后,退到路稍微宽一点儿的地方。旁边是陡峭嶙峋的山峰,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坠下。这些都是袁蓉荪跋山涉水拍佛像时再寻常不过的日常。
2016年9月,广西桂林漓江边伏波山下。临江喀斯特山崖下面有一个天然的洞穴,几个游泳后的青年人在里面换衣服、放东西。洞穴上面,是青褐色的唐代佛龛群,一座连着一座。

2016年9月,广西桂林市伏波山,唐代佛龛群。桂林人早晚间常在此跳水、游泳,佛龛下的古洞即是人们的天然更衣室。几个游泳后的年轻人在里面换衣服、放东西。
“佛像在上面,这样会不会觉得尴尬?”袁蓉荪问其中的一个人。
“我们爷爷生活在这里时,它们就是这样的。后来人们把这里弄成公园,才修了栏杆和围墙。这过去就是在泳地里。”
不必毕恭毕敬,不必小心翼翼。在袁蓉荪看来,“佛像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他拍乐山大佛时,焦点不在大佛,镜头对准了江边一个洗菜的妇女,她聚精会神地把装满鲜绿青豆的竹篮浸到水中淘洗。江水浩荡,冲洗着青豆。远山郁郁蓊蓊,大佛就坐落在江对岸的山岩上,目视着江水的流淌。
大人围着佛像打扑克,小孩靠在佛龛上玩石头剪刀布,男人在佛像的注视下插秧打谷子、耕地劳作,女人在佛像对岸洗菜、聊天……人们以这样方式和佛像建立连接。众生因信仰而造佛,佛又穿越悠长岁月,见证欢喜和伤悲,伴随着一方众生。

2011年5月,唐代小佛龛,四川省丹棱县双桥镇刘嘴石窟。散落在果林菜地边10余个石包上,
当地人习惯称为大石包造像。在漫长岁月里,当地村民把它当作晒场,在佛像旁,晒种子、晒豆子。
如今,袁蓉荪经常会回到过去拍摄的地方去观察当地的变化。多年行走,他也会感慨,山野田间、村舍路边,朝圣者渐渐稀疏,承接千年乡土习俗的一代代人渐渐逝去。仿佛只有佛像,越来越平静,越来越沉默,无声地注视着世间的时光荏苒、斗转星移。

2011年9月,唐代小佛龛,四川省乐至县回澜镇马锣村睏佛寺。佛、菩萨已被百姓新塑,贴上金箔纸,
刷点黄蓝油漆,敬了块红布披上,就是佛的样子。佛龛终日在厨房烟熏火燎,饱食人间烟火。

2012年9月,重庆市潼南县崇龛镇薛家村千佛崖石窟,唐代佛龛群。2011年8月,有人在此取碎石,石刻重见天日。发掘后,文管所请乡民看护起来,
山崖前的平坝,铺了两张晒席,被村民当作晒场。

2011年3月,重庆市大足区棠香街道三合村大石佛寺,明代韦陀龛。多年前人们给佛像妆新彩,韦陀此身色彩即是。为了保护文物原貌,如今已不允许上色妆彩。
袁蓉荪
四川省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1982年开始从事设计、舞美、编辑工作,
历经工农兵学商等职业。
出版有《云朵上的羌红》《空山——静寂中的巴蜀佛窟》
《空谷妙相——时光里的中国佛窟》等摄影作品。
文章首发于《博客天下》第237期
欢迎转发到朋友圈
转载授权请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