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人都有故事,
这是[有故事的人]发表的第534个故事

缅甸,图片来源于网络
李方明
果敢兵
走在缅北果敢的每一个城区,每一条街上,甚至每个坝子山寨,都会遇见果敢兵。但你分不清那是正规军,那是散兵游勇。所谓正规军,就是果敢同盟军,所谓的散兵游勇,就是那些有钱人家养的家丁式的兵。
在果敢,无论是正规军,还是散兵游勇,他们穿的服装都是一样。草绿色军装或迷你服军装。他们的军服只有帽徽没有领章,一般情况下,很少看见他们穿戴整齐,军装底下时常趿拉着一双拖鞋。唯一能显示自己是一个兵就是在腰间别着一把手枪和倒背着一支半自动冲锋枪。再说,果敢人不论老中青都喜欢穿兵服,但许多人穿着兵服,却不是兵也不像兵。
果敢兵不分年龄大小,也没有军龄期限。十一二岁就去服兵役。我曾在政府里就经常见到那些娃娃兵,背着枪站岗放哨。据了解,这些娃娃兵,大多是战争时留下的遗孤,有的是家里太穷养不起。其实在果敢当兵,除了吃住,津贴很少,一般是二十至五十元不等,还要按级别分。果敢兵有文化的凤毛麟角,大部分是文盲或接近文盲。由于没有文化长不了见识,就处处显露他们的劣根性和愚昧来。
我在《新果敢报》做记者时,就亲眼见过在某副司令家门口站岗的兵对来访人员的无礼,甚至拳脚相加,枪托相向。我想,这个兵也许看见这人穿着破烂,瞧不起他。所以他们面对这样的人,都是一味的回答:司令不在家。如再问就不答理,甚至用枪托赶你。我还亲眼见过在赌场门口,那些保安式的兵,二话不说就用脚踢翻在赌埸附近摆摊农妇的食物。还听说,前些年有二个兵上街,见两人在街边吵架,就上前问何原因,一人抢先指着那人说,是他的不对。二个兵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用皮带抽打他。当被打的人指着那人说,是他的错,兵们又回过头来抽打他,直打得二人不吭声为止。
在果敢,这些事经常发生,所以在果敢的中国人是不愿和果敢兵打招呼的。他们深知在这里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看见在街上或在路上行走的兵,就早早地躲开,以免招来麻烦。
当然,果敢兵不全是这样,他们在外面张狂一旦回到营房或回到主人家,就惟命是从,毕恭毕敬,服服帖帖了。我曾去过几个副司令家某区长家,就目睹过这些兵们的两个样。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近几年来,果敢文化教育的不断发展,有大量的学生入伍当兵。我所教的许多学生就入伍当了兵。他们有了文化,有些入伍不久就升了职。从零二年开始政府创办的干部学校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德才兼备的兵。我们相信,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果敢的军队建设与经济建设将会得到迅速发展。
毒枭刘铭
刘铭是毒枭已盖棺定论。但关于刘铭的死,却众说纷纭,各有说辞,连媒体报刊也说法不一,有的说是泰国警方干的,有的说是中国便衣干的,也有人说是缅甸方面干的,最后一个说的也让人深思的是果敢方面干的,说他们杀刘铭主要是为了杀人灭口,怕牵涉到果敢方面的其他人物。这种理由其实很难立脚。但可以证实一点的是刘铭确实死了,于2002年1月28日也就是春节前在东城学校大门口被人击毙。
刘铭死前,曾是特区开发部的副部长,虽然官职不大,却在果敢也是个权倾一时的人物。
刘铭来果敢十几年,做毒品生意赚了不少的钱,已是多少多少亿的主了,在当时来说,果敢除了彭家声,恐怕没有第二个比他更有钱的了。刘铭早在好几年前就上了国际缉毒组织的名单。但他为了寻找保护伞,就投靠了果敢老大的名下,出钱买官做“事”,他投资几千万元建设开发东城区,又出资几百万元建果敢禁毒馆。
2001年,我在果敢做记者时,曾在东城禁毒馆广场举行中秋佳节联欢会上见过一次刘铭,并和他说了一会话,就是关于办报经费一事,请他支持。他当时回答很爽快,并说一定支持。可过后,我去他家两次都不曾与他谋面,可以说是无法见到他。问仆人,就是一句话不知道。另外,他家戒备森严,豪宅内,除了做事的仆人外,就是那些别着枪的兵丁。去两次,只和他的夫人照过一次面,也不曾说什么。再说刘铭的电话号码根本就问不到的,没有人会告诉你。据说刘铭的手机号码经常换,他的号码在果敢恐怕只有“果敢王”彭家声和其他几个厉害人物知道。
要说刘铭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就从中国云南耿马县进入缅甸果敢。在他离开中国前,就是个罪身。在来果敢之初,还是个落泊之人,但凭着年轻风流又会转动的头脑,很快就认识了一个当地有名望的女子。此妇人名叫罗秀菊,比刘铭大几岁,是个寡妇,有三个小孩,后来和刘铭结婚又生一女孩。
关于罗秀菊这个人物,也颇有些传奇色彩。早些时候,也就是刘铭死后的第二年,我去刘铭家想做一次探访。这一次探访我是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去的。虽然这次探访没有成功,但多少有些收获。那天是下午四点多,我一个人来到了刘铭的豪宅前,刘铭家紧邻去东城的公路旁,豪宅外建有三米多高的围墙,紧锁的镀锌铁门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看着这围墙和铁门,真有点固若金汤之感。要是平常,也只一小门半敞开着。我以前去过他家两次,就是从小门进去的。可这次大门小门都紧闭着,也听不见里面的动静。我不敢贸然前去敲门,我只好在刘铭的豪宅前驻足了一阵。然后,我来到与刘铭对面的一幢用竹片做的屋墙,用毛草盖的屋顶的人家。虽然同在一条路上,差距却如此之大,但你却不能不信,在果敢这地方,富的,富得流油,穷的,穷得家徒四壁。我来这家房子前,这家的男主人正在补织着一张鱼网。这时,他也望见了我,我赶忙喊他:“大哥,能让坐会儿吗。”“行行。”他说完,赶忙为我搬来了一条凳子,我坐定后,给他发了一支烟。他还在摆弄鱼网。我说:“大哥,你家养了鱼塘?”“呃,就是上面那口塘。”接着我话题一转,明知故问:“大哥,对面那座房子是谁家的,大白天也关着门。”他说:“你不知道呀,刘铭家。”我故作吃惊状:“刘铭家,是不是去年在东城学校大门口被打死的那个刘铭”。
“是呃”,他声音不大。
“大哥,现在他家的房子是不是没有人住了”。
“有啊,他老婆孩子还住在这里。”
“不是听人说,他老婆去了泰国而且又找了老公吗?”
“不是的,那是别人乱说,她一直住在这里,没有去泰国,我和她们虽然没多少来往,但还是了解的”。
我听后有点喜出望外,也有点迫不及待。说:“大哥,你能不能说说刘铭的老婆。”
他开头不肯说,以为我是便衣。后来我给他说明情况后,才简单地说了一些,但始终不谈有关毒品问题。
他说,罗秀菊和他一起长大的,他们也是一个寨子的。罗16岁时,就在彭家声部下当了一名女兵,在缅共时期,她也是在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也算是个女中豪杰。但后来她慢慢地发达了,从此来往少了。
他说了许多,就是不愿谈罗涉及毒品一事,我想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位大哥也说了他自已有五个兄弟,现在有三个兄弟在同盟军里当兵,他和三兄弟在家务农。他说他们家原住在西山区大水塘的一个山寨里,靠种大烟(鸦片)维持生计,现在政府不让种了,才搬到坝子上住。现在靠养鱼、种玉米、甘蔗一类的作物为生。
最后,我要他谈谈刘铭的一些情况,他就用手打住了。他说:“你们知道他是什么人就行了,何必要那么详细呢。”最后他告诉我,“没事千万不要在他家门口逗留,他家还养着十几个兵呢,另外在老街灭一个人容易得很呢。”
我一听心惊肉跳。这时,对面大门“吱呀”一声响,大门慢慢打开,紧接着一辆崭新的“护卫车”开出来了,透过车窗玻璃看见里面坐了一个稍胖的女人,后座还坐了两个荷枪的兵,这时我赶紧偏过头。车过后,大门又关上了。大哥告诉我,刚才车里坐的那个女人就是刘铭的老婆。
这时天色已晚,我和大哥道了别,就一路惊魂地回到住地。
关于刘铭,真正发迹还是靠他的老婆。当初是她给他启动资金,给他引路,到后来刘铭的毒品生意越做越大,甚至超过了罗秀菊。
但到今天为止,我们无法说清他做毒品到底赚了多少钱,恐怕只有天知道,还有现在已归于尘埃的刘铭知道。
在果敢被关押
刚去缅北的头一年,我曾去过一次某特区的一个监狱,采访了一名关押了一年多的牢犯。
这个监狱设在离口岸不远的一个治安大队内。监狱四周开阔空旷,给人看去,所谓的监狱只不过是一般土牢而已,看不到高墙电网,也没有什么重兵把守。围墙只有一人多高,一个铁门。在铁门的旁边,有一平房,并有几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在来回走动。此牢房虽然看去并不牢,但从来没有发生过越狱事件,如果越狱,后果只有死路一条,因为这里是军事管制。
这名牢犯是我的一个同乡,据他自已说,他被关进来是因一次吃“麻黄素”,被查夜的士兵抓个正着。
那次采访,并没有得到我要得到的东西。因为当时有看守兵在场,他不敢说什么,他每说一句说话,都要望一眼看守的眼色。我知道在这样的场合下,从他的嘴里肯定得不到什么。而真正了解监狱内幕是他从监狱出来后的一次交谈。
据说这位老乡曾在国内也犯着事,也蹲着监狱。来到这里又不学好,因吃“麻黄素”被关押。但他说,同时坐牢,却有天壤之别。在这里关押一个人,只有犯一点事,说关就关,有的犯人关进来,根本就没有什么审判,也不量刑也不宣判,就是说根本没有那套法律程序。关进来也不知要关多久,何时才能出去。但是如果有人出钱保你,或上面有人关照,只有你不是十恶不赦的杀人犯,你随时可以出去。他在里面就亲眼目睹了许多这样的犯人,特别是本地犯人,在家人和亲朋说情出钱就可以放出去。我这位老乡由于家人没钱保他,所以因吃几粒“麻黄素”就关了一年多。他说刚关进去的时候,惨遭了一顿毒打后站立不起来,又加上每天要戴着十几斤的脚镣去地里劳动,真是生不如死。他说,监狱经常发生死人的事件。一是饿死,二是病死,三是打死。在这里根本就吃不饱,有病也不给治,人死了就像死一条狗,抬到山坡上挖一个坑掩埋了事。
在缅北四个特区,由于高度自治,一些王法至今还没有根除,也奈何不了。听说有些特区把犯人关进土洞,基本上是活人进去死人出来,有些还设置了水牢,犯人在里面关不了多久,双脚就会腐烂直至死亡。
我在缅北金三角,就听说某区的水牢里曾关死过许多犯人。象特区的执法处,特警队,你如果一旦关进去,就别想好着出来。他们那种对犯人的残酷折磨,令人发指。有些犯人,如果按中国的法律,最多也是治安拘留或劳教,在缅北却不同了。
而前些天,我还亲眼目睹了一名死于本地兵的拳脚之下的同胞。
我常为这里的愚昧与落后感到悲哀,也为那些不守法的同胞感到悲哀。
但我相信,这些愚昧和落后的行为,在文明与发展的今天,将会得到改观,那些丧失人性的东西将会得到根绝,正如在缅北根绝罂粟一样。
杀年猪
杀年猪在缅北果敢像做喜事一样隆重。
果敢的传统,杀年猪都是在每年的冬至前后,所以在这些日子里,每天都有杀年猪的,少则几家,多的那天一个寨子就有十几家。
杀猪的那天,寨子里青年小伙和姑娘们都来相帮。这天像过节一样热闹,放鞭炮,一派喜气洋洋。而且杀年猪是要请全寨子人吃饭,至少一户要来一个,一般情况下要摆上几桌甚至十几桌。那天,郭校长杀年猪请我们老师去做客就摆了十几桌。后听说,光请客就用了一头猪。好得郭校长是个殷实人家,杀年猪就杀了三头。如果杀一头也就摆不了排场,用于请客后,也就留不了多少。但是,也有一些人家没有年猪杀。我在满乐村就见过不少,特别是崩龙族人,或没有田土的人家,就喂不起猪。再者在这里不管杀几头年猪,都不把肉卖出。
我想起我小时候,家里杀年猪都要到腊月二十几,并且自已只留少许过年用,其它都卖出,因为我们姊妹几人过年的新衣服都得靠它。现在好了,过上了好日子,大多农民也不喂猪了,什么都方便了,市面上什么都有,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买到。然而,在这里市场不繁荣,寨子又离市场很远,要翻几座山,去一次来回要一整天。所以一般人家平常是不去的。除了路远,关键的是贫穷落后,贫富不均,富的看不起穷的,穷人在富人面前抬不起头。于是,在这里富人家一年到头有长工(佣工)做事,赚取他们廉价的劳动力。所以穷人家是没有年猪可杀的。
异彩纷呈的果敢打歌
早年在缅甸果敢生活过一段时间,而最早看打歌是在果敢老街的清水河。我刚来果敢时,是在政府的一家报社做事,后来又到了清水河区的一所汉文学校做老师。
任教的时候,学生杨国兰,别看她年纪小,但在打歌方面却在行。如某某家结婚,她也要把我叫去,一同观打歌。开头她边看边给我讲解,后来她也情不自禁地把我拉入打歌的行列。她不但会唱打歌调,步子也走得很好看。一前一后,一摇一摆,伴随着三弦琴的旋律,很有节奏地舞动着。每次打歌回来,她还余兴十足,哼呀唱呀跳呀。我常常被她感染着。
在清水河观看打歌,一般是在普通人家的婚礼上,而真正观看大场面的打歌却在老街的一位朋友的婚礼上。我这位朋友在老街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他结婚时,给我送来了喜贴,还特意要我为他的婚礼拍照。
果敢人结婚,打歌是婚礼上的重要内容,没有打歌的婚礼,可以说既不隆重,也不热烈。同时,打歌也是果敢人的一个传统的节目。在果敢几乎每个区乡都有打歌队,清一色的青年男女,统一着装。有一次我从西山区大水塘乘车回老街,在车上遇着一群要去老街表演打歌的青年男女。他们在车上也不闲着,男的弹奏三弦琴,女的唱着打歌调。当时,我真有点如痴如醉的感觉。
朋友的婚礼是隆重的,许多特区领导也来参加他的婚礼,他们的到来,更增加了婚礼的喜气和热闹场面。婚礼是在他家落成不久的豪宅里举行。果敢人的婚礼一般是三天连期,这是果敢人的结婚风俗。第一天是迎宾,第二天才是婚礼的高潮,第三天是送客。
我是在朋友婚礼的第二天来的。在他家门前,停放着许多各种各样的豪华小车,进进出出的亲朋,脸上都洋溢着喜气。
在进入豪宅大门边,穿着盛装的少男少女,阳光般的笑容写在脸上,他们手捧着糖果,香烟在迎接客人。
我进去的时候,刚好遇见穿结婚礼服的新郎新娘。我和他们的握手寒喧,并说些祝福一类的话语。然后安排我入席。等宴席散了,也临近夜晚了,婚礼也将开始了。
在隆重而又热烈的婚礼场上,在五彩斑斓的灯光辉映下,新郎新娘,神采奕奕,款款步入婚礼场上,并向主婚人鞠躬致意,接着主婚人讲话,宣布结婚仪式开始,致谢词。
待礼仪完毕,接着进入婚礼的另一个高潮——打歌。这时,被请来的打歌队入队排好,领头的就是打歌队的队长。他怀抱三弦琴,当他哨子一吹,弦子一响,后面的队伍就一起摆手动步。开始时,参加婚礼的来宾一般都在观看,待进入打歌的高潮时,男女老少也就自发地加入打歌的行列。
果敢的打歌是一种集体性和男女均可参加同乐的活动,不过不能随随便便举行。除了过年过节和婚丧外,一般情况下是不能随便乱弹弦子的。果敢的打歌调,大多是过年、贺喜、结婚、丧葬等多种。歌词有老词和新词,老词一般是传统的,新词有填词,自编的和即兴创作的歌词;调门有软调、硬调和快速调之分,软调为慢步,硬调为快步,而快速调则为跳跳调。歌词大多没有什么文采,也不怎能么押韵,但表达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主人的热爱之情。
“一条藤子甩过江,藤子结果桂花香。桂花藤子结桂果,多挂你娘少挂我。小小蜜蜂飞过江,阿哥阿妹翅膀酸。细细想来慢慢飞,细想慢飞过长江。大海大江过江龙,玩开玩开又玩拢。不会打歌学打歌,阿哥咋摆妹咋摆。小妹在家好好睡,阿姐去打两转歌。三打两转马上回,阿姐拿带糖果来。”
婚礼上,那欢快的打歌调回响着。参加打歌的人越来越多,队伍也越来越长,围成的圈儿也越来越大。他们伴随着三弦琴的旋律,脸上荡漾着幸福的笑容。许多青年男女通过打歌,相识、相恋,结成百年之好。
这琴声,这歌声,这舞步,既有历史的余韵,又有今日和平安泰的喜悦,既有邻里乡亲的拳拳之情,又充分展现了民族大团结的友好情怀。
在婚礼上,我拿着相机,“咔嚓咔嚓”拍下了这一个个美好而幸福的瞬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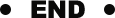
作者:李方明,男,湖南省攸县人,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攸县作协理事。曾先后在报社杂志社任过编辑记者。9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有小说、散文、纪实文学散见于《湖南文学》《湖南工人报》《长沙晚报》《作家园地》等省市各类报刊,著有长篇小说《生存》,中篇小说《苏紫的幸福生活》等。
责编:糖糖
版权为有故事的人所有,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去看看我们的有味微店吧
点击“阅读原文”
或长按识别下方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