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则消息震惊了学术界。多家媒体报道,
“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出生了。
报道称,11月26日,来自中国深圳的科学家贺建奎在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召开前一天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这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经过修改,使她们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
这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也意味着中国在基因编辑技术用于疾病预防领域实现历史性突破。
据悉,这次基因手术修改的是CCR5基因(HIV病毒入侵机体细胞的主要辅助受体之一),使用的基因编辑技术为“CRISPR/Cas9”技术。
刚刚,深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官方微博@健康深圳 发布声明称,
深圳市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已启动对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伦理问题的调查。
消息引起轩然大波
后续难道要对双胞胎继续实验?
伦理问题怎么办?
人类的历史就此被改写了吗?
消息一出,质疑声不断,科技日报对此提出了四点疑问——
1.CCR5这个靶点是不是已经公认的会感染HIV?敲除这个靶点有没有其他潜在威胁?会导致其他疾病?
2.如何能够证明这对双胞胎婴儿能够天然抵抗艾滋病?因为也不可能现在就让婴儿接触艾滋病传染,这是有悖伦理道德的。如果这对双胞胎一生都没有经历过可能感染艾滋病的环境或行为,又如何证明她们天然抵抗艾滋病?
3.对试管婴儿进行基因编辑是否有悖伦理道德,经过什么部门审批?一个民营医院就能做这样的实验吗?
4.此前我国有没有过基因编辑手段用于人体的实验?
业界声音:
此事后果不可预测
“这事件已经远远超出了技术问题的范畴,后果不可预测,一定是伦理争论的焦点。即使技术是100%可靠,人类是否可以或应该编辑自己的生殖细胞和胚胎,(看到这个消息)绝大多数人肯定大脑一片空白,包括我自己。”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林琦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会有什么后果?果壳网用更通俗的话语做了表述:
CRISPR作为基因编辑工具虽然强力,但是会有很多“脱靶"——错误地编辑了不该编辑的地方。它的脱靶率依然是一个争议中的话题。
在有些领域,脱靶不是大问题,比如如果我要编辑一个农作物,那很简单,编辑完了之后养养看,不断检测各种指标,如果出了问题,扔掉重来就是了。
但是在人类胚胎编辑里,脱靶就是大问题了,因为你只有一个检测窗口——那就是胚胎早期。等到胚胎发育起来再发现问题那就晚了,你总不能把一整个活人给扔掉。
而且,这个人长大成人之后还要结婚生子的,脱靶带来的错误编辑还会传给后代。
当然研究者肯定知道脱靶的风险,相信他们一定尽了一切努力来测序筛查防止脱靶的出现,但是目前的技术毕竟是有限度的,对人类胚胎进行操作,风险还是太大了。
“
现在贺教授不接受媒体采访,过几天统一回应。
对于此例研究,更多信息不能透露,这个实验不是因为母亲有艾滋病,也不能透露婴儿是在哪个医院出生的,因为个人隐私不能说太多。”负责贺建奎媒体的负责人陈远林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来源:麻省理工科技评论
据报道,这次编辑峰会于2018年11月27—29日由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医学院、英国伦敦皇家学会和香港科学院在香港联合举办。贺建奎将在峰会现场展示他领导的项目组在小鼠、猴和人类胚胎的实验数据。在50枚人类胚胎基因测序结果显示,未发现脱靶现象;而所有人类正常胚胎里面,有超过44% 的胚胎编辑有效。贺建奎还展示此次基因手术婴儿脐带血的检测结果,证明基因手术成功,并未发现脱靶现象。
他表示,结果仍然需要时间观察与检验,因此准备了长达18年的随访计划。
网传百余科学家联合声明
:
疯狂!谴责!
@知识分子
微博发布百余科学家联合声明,表示这项所谓研究的生物医学伦理审查形同虚设。直接进行人体实验,只能用疯狂形容。作为生物医学科研工作者,坚决反对!强烈谴责!
南方科技大学回应:
贺建奎已停薪留职,研究工作学校不知情
南方科技大学发布“关于贺建奎副教授对人体胚胎进行基因编辑研究的情况声明”:
今日,有媒体报道贺建奎副教授(已于2018年2月1日停薪留职,离职期为2018年2月—2021年1月)对人体胚胎进行了基因编辑研究,我校深表震惊。在关注到相关报道后,学校第一时间联系贺建奎副教授了解情况,贺建奎副教授所在生物系随即召开学术委员会,对此研究行为进行讨论。根据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我校形成如下意见:
一、此项研究工作为贺建奎副教授在校外开展,未向学校和所在生物系报告,学校和生物系对此不知情。
二、对于贺建奎副教授将基因编辑技术用于人体胚胎研究,生物系学术委员会认为其严重违背了学术伦理和学术规范。
三、南方科技大学严格要求科学研究遵照国家法律法规,尊重和遵守国际学术伦理、学术规范。我校将立即聘请权威专家成立独立委员会,进行深入调查,待调查之后公布相关信息。
深圳市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
已启动调查
刚刚,深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官方微博@健康深圳 发布声明称,
深圳市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已启动对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伦理问题的调查。
11月26日,有媒体报道《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引发公众对该项研究的安全性与伦理性的热议。原国家卫生计生委于2016年公布的《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明确规定“从事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的医疗卫生机构是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工作的管理责任主体,应当设立伦理委员会,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伦理委员会独立开展伦理审查工作。医疗卫生机构未设立伦理委员会的,不得开展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工作。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伦理委员会设立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机构的执业登记机关备案,并在医学研究登记备案信息系统登记”。
深圳市参照该《办法》对省级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的相关职责要求,建立了“深圳市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并已开展“从事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的医疗卫生机构已设立伦理委员会的备案工作”。根据“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伦理委员会设立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机构的执业登记机关备案”,经查,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这一机构未按要求进行备案。
深圳市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已于11月26日启动对该事件涉及伦理问题的调查,对媒体报道的该研究项目的伦理审查书真实性进行核实,有关调查结果将及时向公众进行公布。
深圳市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
2018年11月26日
按照常规,一种新的遗传治疗技术,会首先在患有遗传病的人身上使用。
把病治好是一个毫无疑问的收益,这个收益可以和新技术的风险相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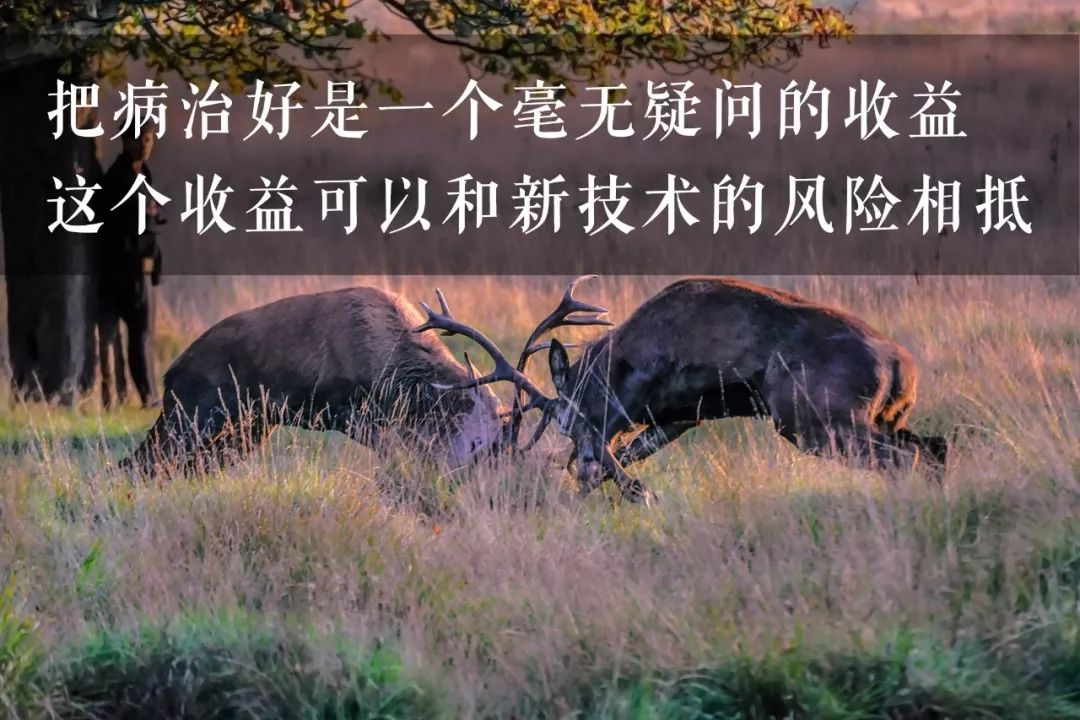
但这次基因编辑不是治好遗传病,而是获得对一种疾病的抗性,同时小幅增加另外一些疾病的风险。
虽然HIV眼下是很重要的威胁,但并不见得对每个人都是如此,也不能预测未来如何。
毕竟,已有的HIV阻断疗法效果已经非常好了。所以,这个收益本身就很不明确。
更糟糕的是,根据美联社的报道,这次的双胞胎里,至少有一个没有完全编辑成功,换言之这个孩子没有获得真正的抗性。没有抗性,却还是遭受了编辑过程以及它伴随的脱靶风险,这个场景就很不好了。按照常规,没有编辑成功的胚胎就不应该允许它长大才对。
所以,这次的这个实验还是有相当的安全和伦理问题。
王立铭
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
《生命科学50讲》作者
为什么基因编辑婴儿
在今天不可原谅?
在实验室利用一种基因编辑技术,在至少七对夫妻的受精卵上修改了一个名叫CCR5的基因。并且其中一对夫妇的一对双胞胎女儿已经在这个月出生了!
必须说明,这让我个人非常愤怒。
用修改CCR5基因的方法来对抗艾滋病,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主意。就在几年前,美国圣加蒙公司还在研究这一技术,也确实发现病人体内的病毒水平明显降低。
如果科学和临床研究只到这个地步,我相信大多数人会毫无障碍地接受它。动用某些技术手段让患者重获健康,是非常正当的目标:首先,相比去除CCR5基因可能带来的风险,治愈艾滋病的收益要大得多得多;其次,就算治疗出了问题,也不会遗传给后代,或者扩散给其他人。
但是,顺着这个逻辑稍微多想一些,你会意识到这项技术还有更大的想象空间:从治疗到预防。这也是这个新闻击中我的地方。
如果在没出生的孩子身上提前把CCR5基因破坏掉,不就能让它从一出生开始就不必担心艾滋这种疾病了么?
这种思路和打疫苗差不多,但却是非常不妥的,不可原谅。
这两个孩子的母亲根本不是艾滋病患者,孩子他父亲虽然是艾滋病携带者,但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控制,母亲只要做好孕期的防护措施,孩子100%不会感染。即便是艾滋病母亲生的孩子,用上已经很成熟的阻断疗法,孩子也有99%的可能不会感染。
也就是说,
这个基因编辑的操作,收益小到可以忽略不计,而风险却极大,
最主要的就是“脱靶”,并因此破坏人体中原本正常的无关基因,并且遗传给所有子孙后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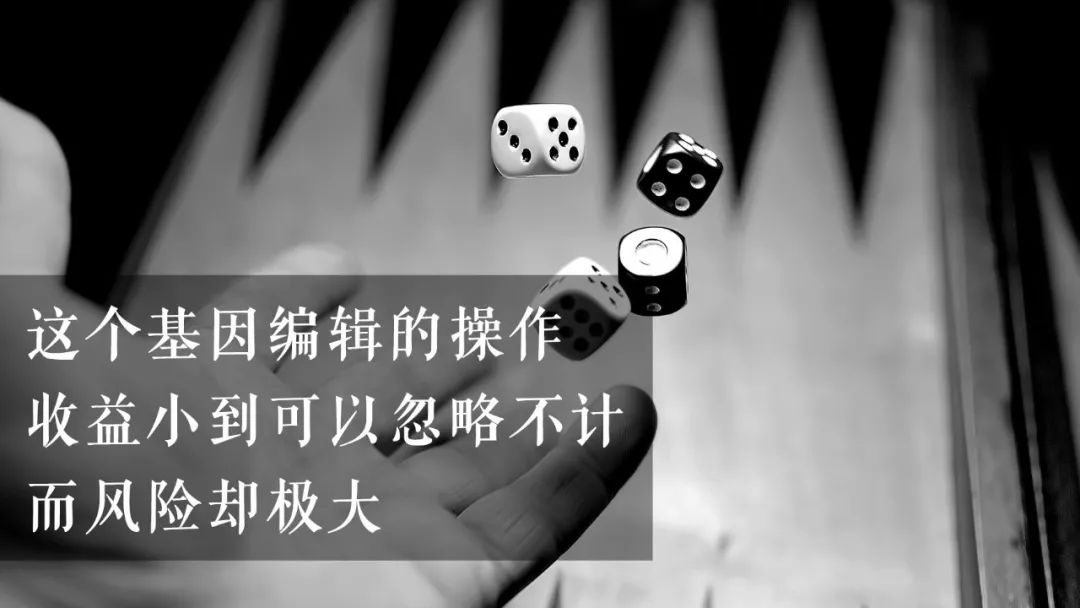
基因编辑还需要有更多现实的技术性考量。
比如,在这次试验的审批过程中,是否暴露了相关法律法规的空白或灰色地带?现在的流程是不是能尽到监管责任和确保监管质量?受试者有没有被明确告知自己接受的是一项什么研究,有什么风险?这项研究在正式接受学术界评审之前就急急忙忙诉诸媒体,出于什么动机……
同时,我还有更深层次的担忧:当基因编辑技术的边界难以明确划定时,对人类这个物种未来命运的担忧。一旦“治疗”和“预防”的边界被打开,“预防”到“改善”的窗户纸更是一捅就破!
*摘自王立铭发表自“得到”的
《为什么基因编辑婴儿在今天不可原谅?》
魏武挥
天奇阿米巴基金管理合伙人
科技专栏作者
技术大潮滚滚而来
是不可阻挡的
在事实含混的情况下,不是很确定这件事是不是真实发生了,毕竟我不是这一行的。有科学家表示这不是创新,只是过去没人做,也不敢做(基于伦理底线考虑)。从他们的言论来看,这件事似乎是成立的。
所以,我接下来说的,都基于假定基因编辑婴儿这件事的确存在。
目前来看,我个人以为,也谈不上从制度到伦理道德的全面崩塌。基于伦理的考虑是有道理的,但这只是对未来的一种忧虑。而未来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尚无法得知。
五年前我在知乎上提了一个问题:如果这个世界人的正常寿命是400岁会怎么样?这里的400就是个虚指,也可以说成500、600岁。
我自己的答案是:这会引起从制度到伦理道德的全面崩塌。但是,如果是渐进式的,比如每年人均寿命都提高个几岁,等真到了400岁的时候,人类社会其实一切如常。
我们要相信一件事,制度、伦理、道德也会进化的。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伦理道德。
用今天的伦理道德去推想未来的情况,不得不说,有那么点“刻舟求剑”。
关键是社会的适应度。而从科学技术本身来看,有几点是需要提请注意的:
①
有一部分人信奉这样一件事:能发明/发现出来的就是好的。这个观点不是所有人都认同,但有一部分人就是这么认为的;
②
基于上面这个观点,自然而然就会出现:总有人会发明/发现一个新的科学技术;
③
新科技出现后,一旦越过创新扩散点,它的扩散速度就非常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