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aine
一
多年前谭咏麟曾出过一张新专辑,叫《迷情》,整个马来西亚大卖。当时我就读于英迪学院,正为赴美留学发狠用功。可犹豫几天,到底还是买了卡带。时至今日,别的曲子我早忘了,唯有那首《Elaine》,还是会在不经意间,在不知何处,如风一般轻轻撩起。
英迪学院的费用在马来西亚算是高的,但头两年学分被美国大学承认,比起傻呼呼地跑到美国读大一,还是便宜很多。于是爸妈把我从老家新山送到了吉隆坡。
当时大姐和姐夫好不容易在吉隆坡找到工作,租了一栋三千平方英尺的大房:上下两层,楼上卧室两间,夫妇二人睡主卧;楼下另辟一间卧室,租给一个叫阿轩的男生。所谓以租养租,在吉隆坡打拼的年轻夫妇大抵都这么做。
英迪学院附近聚居了很多像我这样的外地生。夜夜笙歌固然谈不上,但午夜的马来茶档或印度小吃,却对我和新认识的同学小梅有着百分之五百的杀伤力。大姐知道我爱热闹,怕我耽误学业,便把我接进她家的大房,住楼上另一间小卧室。
这样一来,大姐便少了一份收入。我不知该怎么办,只好打电话跟母亲商量。结果被训了一顿,才心无旁骛住了下来。
大姐家这小区看起来很新,据说过去曾是大片大片的油棕园。刚搬过来那阵子,与大姐共事的潮州人还责备她"也不在门口烧烧纸拜一拜",因为"这地方没人气太久了"。
少了人气,便多出鬼气?又是潮州人的那一套。大姐在早餐桌上嘻嘻哈哈地讲出来,我就当玩笑去听,再讲给小梅听。
小梅也是潮州人,瞪圆了她那双小杏眼,一本正经告诉我:"是啊是啊,不要说大姐,连你这个租户都要拜一拜的。"
我自然一笑了之。彼时三四月份,地势盆洼的吉隆坡已是一大屉蒸笼。每天放学都很晚,我和小梅吃过夜宵,便匆匆道别。赶回大姐家第一件事就是冲凉,趁头发干透前的一点点凉快,跑去楼下客厅做功课。客厅有张大桌,我和阿轩对面坐着,却很少看他,只顾忙着眼前的书本。如今他的模样自是模糊了。只记得他戴了副好大的眼镜,大到整张脸似乎就剩下眼镜。再有就是他的书本总是规规矩矩,而我的就很散乱,好像我很用功,其实背不下多少单词,我就又跑回楼上冲凉了。如此这般,便到了后半夜。我倒在床上,翻着金庸,听着谭咏麟,任凭自己的二十岁就这样黏糊糊地滑过去。想想几个月之后就要飞去美国,倒也不觉得难熬。
二
谭咏麟这张专辑其实是老歌新歌混搭,一副很耐听的样子。听了一阵,才知这卡带配上索尼牌录音机,再加上竖排版的金庸,委实胜过任何安眠药:每一面收歌七首,结结实实的三十分钟,没等读完一节《鹿鼎记》,我肯定就能睡去。
索尼录音机是小梅借给我的,很小,灰色,放在我床前,伸手便能触到播放键。每面卡带放完,录音机便自动停下。所以在"Elaine"造访我这间小屋之前,我都没太听过卡带每面最后的那首歌。
之所以叫它"Elaine",是因它第一次来,我刚好就在听这首《Elaine》。当时已过了午夜,我放下《鹿鼎记》,熄了灯,一边帮韦小宝算着娶到第几个老婆,一边伴着谭咏麟撕心裂肺的歌声准备入眠,却有一阵风从窗子闯了进来。
彼时大姐和姐夫还很拮据,所以家里不装空调,只能开窗避暑,挂帘防蚊。屋里灯虽熄了,但因着外面的光亮,我还是依稀看见绿色碎花纹的布质窗帘被那风一下顶起。
二十岁的我睡觉总是嫌热,薄被都不盖。所以刚被那风吹过,还觉得爽快舒服。可连接吹了好多下,身上竟凉了起来,心里便冒出疑问:蒸笼般的吉隆坡,何来如此怪风?
"问我怎去再忘掉共对风中那黑发飘渺--"谭咏麟还在索尼录音机里卖力唱着,怪风再次将窗帘猛烈顶起,那顶起的高度让我觉得骇异:不要说是吉隆坡,在马来西亚我都从未见过这样劲道的风,更何况窗外根本就不是突然起了风暴的样子。
我越发不安起来。那风也越发肆虐,就像个大盗,翻窗而入,在屋里乱撞乱碰。谭咏麟的歌声已被它盖过,连背景音都算不上。这不是风,是鬼吧?
从小看过很多鬼片,其实都在啰嗦一个道理:人无法和鬼一争高下。我能做的只是紧闭双眼,但愿这鬼只是路过,没有发现我察觉到它,闹一闹就离开了。
多年后我在阿拉斯加州的冰河湾国家公园游玩,安全手册上说遇到灰熊必须躺在地上,因为你根本不是它的对手,只有放弃抵抗,在熊面前装死,才可能捡回一条性命。看着手册上灰熊出没的黑白图标,我一下子想起了那怪风,我当时虽用尽气力紧闭双眼,但还是觉得那怪风已化为人形,立在我身旁,弯腰窥探我,往我脸上吹着森然的凉气,吹得我浑身僵硬。
它在我屋里停留不会超过两分钟,因为那首《Elaine》还没唱完--"Elaine,Elaine,Elaine,YesILoveYou"--它一离开,谭咏麟的歌声便又占满了整间屋子。我还是不敢睁开眼,一直等整整一面卡带都唱完,也不敢睁眼。
《情凭谁来定错对》,我头一次把卡带A面最后一首听完,却是因这怪风。早上,我强打精神,冲了凉要去上学。大姐一边刷牙一边问我是不是生病了,气色这么差。我能告诉她家里闹鬼么?新租的大房子闹鬼?阿轩若知道是不是就搬出去了?
我说这两天考试太多,熬过去就好了。大姐把牙刷放在嘴里,胳膊搭我肩上,也不知是要抱抱我,还是拍拍我。她打仗一般洗漱完,就匆忙上班去了。白天遇到小梅,也只说贪读金庸误了睡眠而已。
到了夜里,伴着谭咏麟的歌声,窗帘再次被顶起,我慌忙合上眼,侧身对墙,"Elaine"又弯下腰在窥探我。脸上,耳边,都是它呼出森森凉气。我极力控制眼皮的肌肉,不让它睁开。若看到"Elaine"的本相,我猜我这辈子也就毁了。
"当一头半吨重的北美灰熊在你脸庞呼着沉重而腥浊的气息,你最好也别睁开眼"--冰河湾国家公园的安全手册如是写道。
三
一直等到卡带放完A面最后一首《情凭谁来定错对》,"Elaine"才掀开窗帘离去。我不知何时才睡去。究竟有没有睡过,其实也未可知。反正再睁开眼,这小屋的摆设依旧,规规矩矩,安安静静,就像此前的每个早上,什么都没发生过。
半个星期下来,我体力透支,没法去上课。眼看到了上午十点,大姐肯定出去上班,阿轩也去上课了,楼下却传来一阵声响。难道又是"Elaine"?还不放过我?白天是我们人的,不是你们鬼的!
恐惧和恼恨一起在脑海中炸开,我一骨碌起来,拎着花瓶就下楼了。
楼下只有姐夫,坐在桌旁抽烟,身上是郑重其事的领带和衬衫。
"你……没去上学?"他惊诧地问我。
"你也没上班?"我把花瓶藏在身后。
姐夫说他最近丢了机电师的工作。这很奇怪,因为机电师听起来就像那种机电般牢靠的工作。
"找到新工作之前,我都去车行打工。别让你姐知道就是了。"他掐灭香烟,变戏法儿似地从厨房里翻出个帆布包,里面是破旧的牛仔裤。
不消说,这肯定是他在车行的工作服了。藏在厨房也蛮聪明,大姐最近可能会有升迁,每天加班很晚,都是姐夫烧饭。
我把花瓶放在桌上,告诉了他家里闹"Elaine"的事。
"你白天上那么多课,晚上还听什么谭咏麟,把自己搞得太累了。"
他这反应竟是家长式的敷衍。我心里有点凉,本想等晚上大姐回来再提,他却继续说道:"哪里有什么鬼呢?又不是找工作,鬼来找我们干嘛?这房我和你姐找了好久,租约签一年,这才三个月不到,谁能赔得起抵押金?还有阿轩怎么办?依你姐的脾气,到底是退房还是不退?"
难道你不怕"Elaine"撞开你们主卧室的窗子?不怕自己老婆被吓到?可看着他郑重其事的衬衫领带,还有帆布包里的牛仔裤,我又说不出什么。
姐夫从我的表情猜到了我心里。这位印尼华侨、虔诚的天主教徒过了我一副十字架项链:"不要吓自己了。晚上要是再怕,把它放在枕边。你看看你姐,阿轩,还有我,连工作都没了,却什么事都没有,睡得很安稳。"
让他这么一说,我又觉得自己在添乱了。其实后来母亲又给我打电话,让我专心做功课,不要顾虑大姐这边,因为房租她都已经付过了。母亲深知自己大女儿家的境况,尽量不让我再造出什么负担。
我接过那银质的项链:十字架上垂悬着受难的耶稣。
"千万别告诉你大姐。"
临出门前,姐夫又重复一遍。我也不知道说的是他失业还是"Elaine"。
当晚,十字架链躺在我枕边。灰色的索尼录音机,深情款款的谭咏麟,怪风又来了,更强,更猛,以致于窗帘紧紧贴在天花版上。临闭眼之前,我却瞥见窗外芭蕉树叶一动不动。屋内风声大作,像是一头兽,又像是一个歹徒,在桌上在地上踏来踩去,躁怒不安。十字架拿它毫无办法。
早上,大姐见我脸色憔悴,问到底怎么回事。姐夫打好领带在等她。我含糊其辞说和小梅吃错东西了,拉了几天肚子。大姐叹口气便和姐夫匆匆赶公交车去上班了。
四
我被"Elaine"折磨一个多星期。身上明明瘦了不少,脸和眼却都是肥肿的。终于熬不住了,周末的时候告诉了小梅。
"你又不信耶稣,放十字架只会惹恼它!"小梅又瞪起她那双小杏眼,责备我为何不早说。
小梅也正迷谭咏麟。我说那怪风叫"Elaine",居然把她逗笑了。笑完后她又皱起眉,极认真想了想,决定带我去见她在吉隆坡的大姑,一位七十岁的潮州老人。
听完我的遭遇,小梅这位大姑摇头叹道:"可怜,还在读书就撞了鬼!"
大姑虽然驼背,但刀功了得,厨房里转了一会儿就给我和小梅端出几样潮州菜。吃完就要领我去见"阿公",一位跳神的,此间颇有名气,据说曾请神下来在一碟米上接连划出过三个字。小梅也有点想跟着去,犹豫一番,终究还是不敢。
"阿公"其实是一个黑瘦的中年男人,戴墨镜,扎马尾辫。若不是面前摆着那碟著名的白米,简直让人觉得是黑帮片里的人物。
大姑在毕恭毕敬地赔笑,可不等她开口,"阿公"竟指着我怒道:"你看看你!"
他的嗓音沙哑,浑浊,沉重,猛然砸过来,仿佛一个大椰子从天而降。我正吃惊于如此富有爆发力的声音竟出自他那枯瘦的身躯,姑姑在背后推了我一下。
我才明白过来:原来"阿公"是在骂我胆小怕事,把自己吓得神情恍惚夜夜失眠。
"那业障每次进屋都要推窗帘,对不对?""阿公"甩了甩马尾辫。
我点点头。
"那不就是了么!连墙都不会穿,你怕它做什么!从头到尾有碰过你一下么?有叫过你名字?有动过屋里的东西么?"
我的心怦怦跳着,连连摇头。
"那不就是了么!你们这些年轻人啊,没出息!有什么好怕的,睡你觉就是了!"
大概是我真的很脓包,"阿公"已显得颇不耐烦了。
姑姑在一旁小声问到底是不是鬼。"阿公"气得摘下墨镜:"什么鬼不鬼的?这种小业障到处都是,人死了赖着不走,芭蕉树成精了不愿挪,到处都是嘛!有什么好怕?走在街上连阿猫阿狗都对你叫呢,这个样子怕下去还有脸活么?长点志气吧!你越怕它,它越欺负你,跟阿猫阿狗一样……你这样还要去留洋留学,说出来不怕人笑话?"
"阿公"的辫子花白,双眼却枯黑,戴不戴墨镜委实差别不大。他恼怒地赶我和大姑走,不知是我坏了他的修行,抑或门口还有好人在排队。我只好跟着大姑讪讪地往外走,回头看一眼"阿公"那碟被神划出过字的白米,小声问大姑要不要给阿公钱。她也拿不准主意,因为这次"阿公"好像真生气了,连张符都没给我画。
好在"阿公"的门口摆了一个香火盒,大姑到底往里投了二十块。
二十块,我和小梅可以开开心心吃上几顿夜宵,却只换来"阿公"一顿好骂。我很懊恼:跟大姑初次见面,老人家这么热天带我出来,还让她破费,结果这些麻烦却只是因为我没出息胆子太小?
不过仔细想来,"阿公"还是有些法力的。不然他如何知道我准备出国?
我心下又觉得他骂得有道理了。"Elaine"也确实没动过我一下。再想想自己住大姐家这么久,没帮过一下家务,反倒还告诉姐夫有鬼,也实在说不过。更何况自己天天睡不好,肯定要坏了成绩的。想来想去,我自己都要替"阿公"骂我自己了。
可小梅听说"阿公"骂我没出息,却忿忿不平:"什么鬼阿公?哪有第一次被撞鬼就有出息的道理?"
我突然被逗笑了,下定决心,不再理那个"连墙都不会穿"的"Elaine"了。
五
可"Elaine"不依不饶,每夜每夜来闹。好像除了我这小屋,诺大个吉隆坡它找不到个去处似的。这么一想,做鬼也没什么意思。我只是闭上眼,任凭它在屋里飘来荡去。有时仔细听去,倒不像只它一个,好似又从黑夜拉进屋几个。它们轮流下来窥探我,对我呼着只有它们才会呼出的森然凉气,在我脸庞,在我耳边。它们还不停地说着它们的话,很吵,听不出来什么,像是被煮沸而相互乱撞的水分子,又像是电影院或商场里嘈杂无序的人群。
我想比起我来,似乎谭咏麟对"Elaine"更有吸引力。因为我一打开索尼录音机,放到那首《Elaine》,"Elaine"便不请自到。哦,不过是一只爱听谭咏麟的鬼,仅此而已。时日一久,我就丢了恐惧,只有因失眠而累积下的烦躁。小梅说不如把谭咏麟换成陈百强,"Elaine"就不闹了。我坚决反对,因为一旦做出变动,"Elaine"肯定会觉得是我不堪它的袭扰,定然变本加厉。
姐夫的十字架项链虽没什么法力,还是被我留在枕上。姐夫再没问过我这事。他找到了新差事,也许是忙忘了,也许笃信那圣物已发挥出效力。他和大姐早出晚归地赚钱,为了能早日买到属于自己的房子。我也替他们辛苦,就彻底断了跟父母还有大姐提这事的念头。
有时我也会想:"Elaine"生前到底是个什么人呢?难道住在过去的油棕园?如果是这样,那他或她一定是个很恋旧的人。又这么爱听谭咏麟,说不定是一个像我或小梅这样的女孩子。她到底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她每夜每夜地来,到底是为了什么?除了那了无踪影的油棕园,这间屋子里到底还有什么让她割舍不下?是我破坏了她的恋旧么?还是她只想作弄作弄我而已?
有几次,凉气在我耳边和脖颈来回拂动。一定又是"Elaine"在凝视我。我很想猛然睁开眼,既看看她到底什么样,也狠狠吓唬她一下。可我从来没那么干过。论害怕,自然还有那么一点。更重要的是,我要去美国,她要留在她的油棕园,人和鬼不固然不必有什么交集,过去和未来更不该眉来眼去。
在英迪学院的班里,倒有那么几对恋人,天天徘徊在悬梁刺股与生离死别。我没法理解他们。就和小梅约好出国再谈恋爱。还有两个月,我一边发狠苦读,一边头昏眼花选择美国那边的大学。必须要尽可能多地拿到A!不能再失眠了!我敲开楼下阿轩的门,问可不可以和他换房。
阿轩也在苦读。他推了推他的黑框大眼镜:"是楼上太热么?"
看他那副书呆子的模样,我只好实话实话,告诉了他"Elaine"的存在。
"那就换喽,我才不信什么鬼呀怪的!"阿轩居然满不在乎。
换房头一夜,我既没听谭咏麟,"Elaine"也没来楼下闹,居然还是失眠。早上我惴惴地问阿轩睡得如何。这家伙说睡得比在楼下还香。
第二夜,"Elaine"跑到楼下来闹了。闹多久我有点拿不准,因为没听谭咏麟,就没法计时。我恼了,果然就像"阿公"说的:它只是来耍我取笑罢了。
我干脆跟阿轩又换了回来,继续大模大样地听我的谭咏麟,"Elaine"也还继续大模大样地跟到楼上去闹,闹的时间越来越长,闹到谭咏麟都唱不动了,闹到不知东方既白。只可惜,我已分不大清到底是我的意念作祟还是真有"Elaine"在闹。恍惚中,我都疑心这"Elaine"只是一个调皮捣蛋、精力旺盛、化成凉风的孩子而已。
但调皮总该有个限度对不对?晚上我和阿轩面对面在客厅做功课,还亮着灯,"Elaine"就在我背后走来走去,往我头发、耳朵、还有脖子上吹凉气。有时背后的脚本声多了,乱了,我便知今晚"Elaine"又叫了伙伴过来开party(聚会)。
实在被闹得不堪,我便抬头问阿轩:"听见没有?"
阿轩吓了一跳:"听见什么?"
"我背后有人走来走去啊!"
"不要乱讲,"阿轩有点同情我。"要不要跟我换过来坐?"
"算了吧。"我摇摇头,已经开始相信这只是我自己精神恍惚了。
再往后,我甚至拿"Eliane"开起了玩笑,突然指着桌上的杯子,问阿轩:"喂,没发现西瓜汁少了么?"
阿轩只好气馁地放下书本,一口喝掉那杯西瓜汁:"拜托,这很好笑么?"
六
小梅总跟我打听"Elaine",那语气颇像是在打探我喜欢哪个男生。她还夸我胆子够大。可我却很心虚:直到最后,我从头到尾都没睁眼看过"Elaine"。
也许睁开眼,也只是随风飘荡的布质窗帘、淡绿色的碎花纹、或窗外一动不动的芭蕉树叶而已。闭眼感受"Elaine"呼出的凉气,我亦能在脑海中拼凑它的形象。可那终究只是一些鬼片鬼故事的碎片,也还在我认知范围以内,所以不怕这些碎片。真正怕的,是睁开眼看到的"Elaine",完全超乎我的认知。说到底,人想走出自己的世界,又怕走出自己的世界。
我马上就要走出马来西亚去美国读书了。我倒不担心"Elaine"会阴魂不散,跟着我漂洋过海。它连一间小屋都舍不得哩。
大姐终于升了迁,又刚怀上孕,心情无比地好。她请假送我回的新山。临到家前,她吃惊地摸着我的胳膊:"你在我家到底掉了多少磅?"
"二十磅。"
"书念得太辛苦还是我没照顾好你?你这样子我怎么和爸妈交待?"
我到底没把"Elaine"和她还有爸妈说出来。回到新山家里,一切就像是放在槽形鱼缸上的那盆"万年青":舒适,安心,百鬼不侵。拜完祖父的遗像,我便倒头大睡特睡--那种要死命找回几个月丢下的睡眠的睡法。
"Elaine"没有跟我来新山,更别说漂洋过海。它留在了它的吉隆坡,大姐家的街区,早已飞灰烟灭的油棕园。也许,"Elaine"只是一枚爱捉弄人油棕变的?从我的角度来看,它闯进了我的世界,玩闹两三个月。可从它的世界看呢?是我闯进去了么?它到底怎样看待我?一个爱听谭咏麟又胆小失眠的马来西亚女孩?
在大姐家楼上的那间小卧室,我和"Elaine"闯入了彼此的世界。它往我脸上吹凉气,我用十字架对付它。两三个月的时间,我们既没成为敌人,也没成为朋友。仅此而已。
谭咏麟的卡带倒是一直跟着我,跟到了阿肯色州立大学。排名虽差强人意,但坐落在山区的校园却风景宜人。我把自己捉襟见肘的身体套进了印有学校缩写字母的短裤T恤,大步走在清爽的夏末阳光里。学校附近租的房字,金发碧眼的Joanne做室友。
九月初的温度无比舒服,房间的中央空调沉默不语。百叶窗外,枫叶刚刚染上红色,像是刚学会化妆的少女,在等待秋天的来到。夜晚如此安静,我却因时差而睡不着。借了Joanne的录音机,也是索尼牌,只是比小梅的那台要大上两圈,而且是卡带CD双模式播放。
--突然想起了小梅。那台灰色的索尼录音机还给她了。她没说什么。她考的不理想,说要来年再试。她那双小杏眼的眼皮垂了下来。我开玩笑说这录音机你怕是不敢再用了吧。她笑了笑,抱着我,哭了--
我把来自马来西亚的谭咏麟放了进去,A面,第三首,《Elaine》,"缘分到此但我怎可意料--"早已下了热榜的粤语歌在地道的美式木房子里响起,"Elaine"不会再来,我依旧辗转难眠。也不知道在大姐家楼上那间小屋,它会不会有那么一点怅然若失。
英语文学课的黑板上,那位以题目刁钻、评论简短而闻名的白人老教授留下一篇longessay(大作文):
"Writesomethingunforgettable.Entertainme.Whowantsanotherboringweekend?"(写件难忘的事,好玩儿一点的,我周末太无聊了)
难忘的事?大姐的升迁?姐夫的衬衫领带?破旧牛仔裤?十字架项链?马来奶茶?印度飞饼?"阿公"那碟被神划过字的白米?阿轩的黑框大眼镜?小梅睁圆了的小杏眼?
周末的棒球场廖落无人,骆驼牌香烟又辣又呛。我把这些故事讲给Joanne听:是"Elaine"陪我度过来阿肯色之前的几个月,每个午夜,不离不弃。
这位来自南方的白人姑娘听得乐不可支,连夜把我的故事写成了essay,题目就叫《Elaine》。
她得了A。文学课的老教授给了据说是他职业生涯最长的一句评语:
"SeriouslyJoanne,isitfictionalornon-fictional?Butwhocares?Ilikeitalot.Verycreative!"(注:Joanne,你这到底是编的还是真的?可谁在乎呢?有创意,我喜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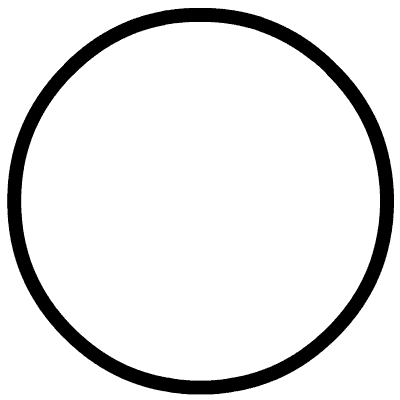 还等什么…
还等什么…
“
有故事的人
”第一本实体书由
作家出版社
出版了,点击下方“
”,去买几本《有故事的人》,看看别人的人生,想想自己的故事吧~

人人都有故事
有
|
故
|
事
|
的
|
人
投稿邮箱:
[email protected]
合作邮箱:
sto
r
[email protected]
主编:严彬(微信
larfur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