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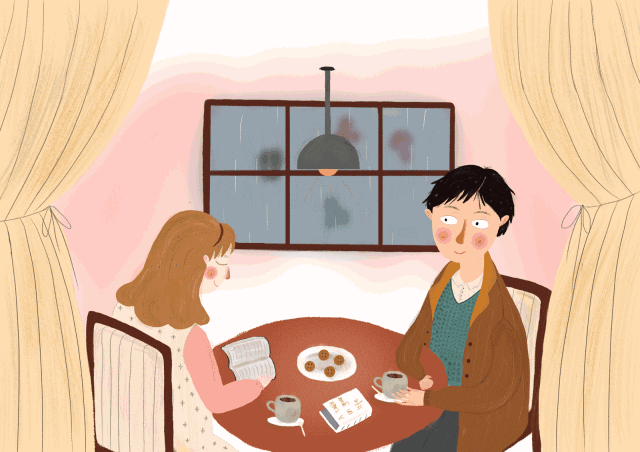
太心碎了。
前两天,刷到一条视频。
视频里的女孩一边哭一边吃东西,眼泪混着食物一起被塞进嘴里,看起来狼狈又伤心。
屏幕上的文字有些语无伦次,但寥寥几笔,就勾画出让无数女孩共鸣的画面。
“我讨厌你封建的思想,却又心疼你劳累的模样,我不知道该怪谁,于是我只好内疚责怪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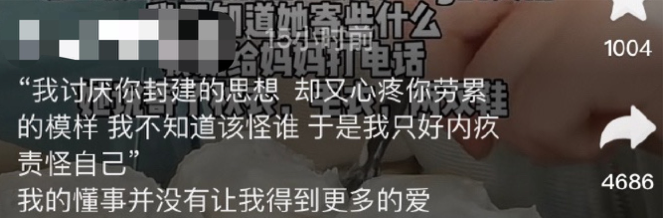
这何尝不是千万中国女孩拧巴而痛苦的自白。
她独自在外上大学,中午接到了妈妈的电话,让她帮忙下单快递,说“要给弟弟寄秋衣”。
她没多问,只下单了1kg的重量,但等到晚上却要补费用,她觉得奇怪,打电话给妈妈再问,才知道,妈妈给弟弟寄去了秋衣、毛衣、鞋子。
她在那一瞬间感到崩溃,问妈妈,为什么要让自己找快递公司?为什么寄给弟弟的东西却要让自己帮忙下单?
表面上问的是快递,没说出口的呐喊却是:“你想到了给弟弟寄十斤过冬的东西,却只在要帮忙做事时才想到我。”
电话那头的妈妈却还在“狡辩”:你懂一点,弟弟不懂。
不知道的,还以为姐弟俩差了十几岁,但实际上,他们都在上大学,年纪相差不会超过四岁。
但妈妈只听见了她一句轻飘飘的抱怨,就揪紧了这句话反复指责她的“不懂事”,阴阳怪气地一遍遍说:“你以为自己了不起了、生你这个女儿没要头、要你有什么用......”
爸爸发来了很多段语音骂她,指责她不懂事、没素质、不尊重人,最后竟然还高高在上地要求道歉。
“你觉得自己那么厉害,以后你有什么事也别找我们。”
伤心欲绝的女孩躲回宿舍,为了安慰自己想着吃个甜点,但依然没忍住边吃边哭——原来,眼泪真的是咸的。
和父母交流时没能说出口的话,她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在了网上。
“他们不关心我从江西到北方有没有秋衣,冷不冷,也没有说要给我买衣服,鞋子。
有个女孩说,自己工作了想给家里人买衣服,她在满心欢喜地计算着可以给爸爸妈妈买什么,但妈妈却只想让她再多出点钱,给弟弟买件贵价的。
面对女孩的生气,妈妈却狡辩不断:“那时候条件不好、年代不一样、现在轻松了......”
过去,他们永远在比较“女儿给自己买了什么,自己给儿子买了什么。”
甚至有时候,要用姐姐的钱来贴补弟弟,用女儿的情绪劳动为儿子省时省力。
而如今,他们还学会了更精巧更无可反驳的话术:因为你乖。
因为你乖,所以可以让渡权利;因为你听话,所以你可以被忽视;
因为你更聪明,所以爸妈事事麻烦你;因为你更优秀,所以家里的资源理所当然地流向了弟弟。
不懂事的弟弟得到了衣服玩具金钱和自由,懂事的姐姐们,只得到了一句“你真乖”。
在看那个女孩的讲述时,我最心疼的一点在于:
她在不停地解释。
解释自己“不是不能寄快递”,解释自己“不是要这些东西”,解释自己不是在争抢,解释自己不是不懂事,解释自己是个乖小孩。
可是我想说,她的愤怒没有错,她的委屈没有错,她明明可以不那么懂事不那么乖的。
但如今在大部分的姐弟组合中,流行的是一套更为广阔和隐蔽的重男轻女叙事——
姐姐的模板是贤妻良母,是付出和忍让,是万事先为弟弟让步。
许多女孩从记事起,就已经隐约明白了一个道理:想要获得父母的爱,就必须表现得更贴心、更懂事、更优秀。
于是姐姐们天然地习得了一套社会期待的枷锁,她们会主动做更多家务,主动帮父母承担一部分养育责任,主动说“不要”。
姐姐大了弟弟三岁,但在幼儿园里却上的是混龄班,她说她特意让弟弟早一点上学,这样姐姐就可以带着弟弟。
她自豪地描述着姐姐照顾弟弟的日常,给弟弟喂饭、抱着弟弟、“真的有一种妈妈抱儿子的感觉”。
姐姐还没长大,就已经被刻印出一套母职规训的模板,扮演着一个懂事贴心的角色。
女性意识普遍觉醒的当下,有不少女孩开始本能地反抗“贤妻良母”的规训,拒绝被这个工具般的词汇冒犯。
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忽略了,许许多多的女孩们从成为姐姐的那一刻起,就被植入了一套雷同的思想钢印。
甚至,还要在妻职母职之外,额外替弟弟承担更多的养育义务、情绪劳动。
一旦她们想要对此反抗,便会被打上“不孝”、“不懂事”的钢印。
于是,整个成长过程里,姐姐们的头上都悬着一根名为“愧疚”的高压电线。
她们太体谅父母,于是更早地学会了独立;她们太容易自责,于是心甘情愿地被剥削掠夺;她们太轻易心软,于是总在父母的疲惫里将愤怒内化,变成只刺向自己的利剑。
而当她们展示出一点点的锋芒时,父母又会拿着道德筹码行使审判大权。
就像这个女孩,她的父母甚至不用解释自己的偏心,只需要揪住女儿一个字眼,就可以把她逼入道德的绝境。
而弟弟呢?什么也不用做,就可以无条件地获得所有宠爱和资源倾斜。
可是,她想要父母同等的爱和关注,原本就没有错啊,她和弟弟获得同样的教育资源,这也没有错啊。
为什么默认女孩就要低人一等,为什么默认女孩只有读不起书出去打工才是惨,为什么要把隐形的重男轻女写成比惨大会?
1996年,导演李玉拍了一部只有二十分钟的纪录片。
剖腹产前的一次家庭会议上,他们商量之后决定让女孩当姐姐,这样以后可以照顾弟弟。
爸妈忙碌时,姐姐要陪弟弟玩会儿;看电视时,姐姐要让给弟弟;出门在外,弟弟在妈妈怀里,姐姐在后面跟着......
才六岁的她可能还不懂什么叫重男轻女,不懂什么叫偏心,只知道这个姐姐的身份,给自己带来了无尽的委屈。
而当她说起这些细碎的委屈,想要表明“妈妈不喜欢我”时,得到的却是“有理有据”的答复:你俩都吃得一样穿得一样吧。
可是,我们要的不是吃穿一样就行的敷衍,更不是隐藏在“好姐姐”夸赞下的偏心。
我们想要的,是平等的关照和尊重,是同样的资源和给予,是同等同量的爱。
但在这种隐形的沼泽中,姐姐们更加举步维艰。因为即便我们察觉到了这种隐性的重男轻女,也很难真正逃脱这种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