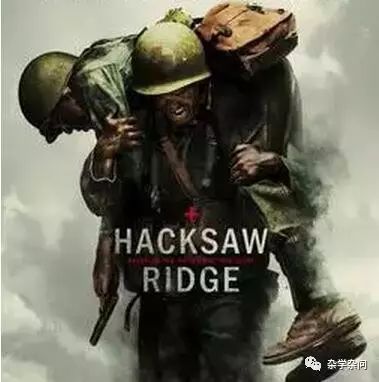新京报:现在会有一种质疑,认为知识分子只会提意见,拿不出解决方案,觉得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发声是很无用的。你怎么看这种观点?
龙应台:
不同意。提出看法跟提出批评就是知识分子本身的功用,而如何去执行和去解决问题,是另外一批人该做的事。我们可能要先明确知识分子的定义是什么?比如我写批评文章的时候是知识分子,我去做官(注:2012 年5 月起龙应台任台湾文化事务主管部门首任部长),就不是知识分子了对不对?那我们就界定,没有实质公权力而只限于提出看法的人叫做知识分子。如果定义是这样,表示知识分子的职责本来就在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是官员身份的事情。说知识分子只会说不会做,就如同批评怎么卖面的摊子不卖黑森林蛋糕。
知识分子放下笔,那他就不是知识分子了。我们也不该再用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去要求他或宠爱他。这时,就要以做事的标准来看他。卖黑森林蛋糕的,就不是卖面的。
新京报:你以前说过一个好的知识分子,不一定是一个好官?
龙应台:
往往不是。因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能力。
新京报:你是怎么能够在这两个身份之间做到相对平衡的转换?
龙应台:
通常擅长于做思考、提出意见的人,不擅长真正动手去做事,而真正擅长做事的人,不一定擅长思考,两种能力是完全不同领域的。我算是非常重视实践细节的人了,而且也很了解做事的时候特别需要部门与部门之间的细磨沟通,也非常重视实践管理及效率稽查等等。作为文人我几乎算得上“孤僻”,习惯静思独处,但是做事时,我花很多的工夫在细节的沟通上。
但是我做得不够好,譬如说,做官的必须身段柔软,跟你即使痛恨或瞧不起的人,为了政务通畅,还是得耐心周旋。这一方面我就做得很吃重,很艰难。
新京报:很多人都觉得知识精英进入了政治圈,会担心他们丧失掉自身独立性?
龙应台:
不是说会丧失独立性,这个前提是错的。作为知识分子的角色时,你只为自己的思想负责,你是一个作者。我写《野火集》就代表龙应台。但是当龙应台去做官,她的任何一句话都不代表她个人,她代表着整个机构、整个制度、社会,她凭什么还强调她的“独立性”呢?她是一个被公民选上的政策论述的一个执行环节——这跟一个人为自己负责,是多么天差地别的大承担啊。
我们社会批评拿的尺度是错的,说你要言行一致,当你做知识分子指点江山的时候,跟你后来做官有了公权力的时候,你要做一样的事,讲一样的话。怎么可以一样呢?后者一定要委屈,一定要有整体观,因为你顾全更多了。你不是个人舞台。
但是当团队的立场和你的核心价值抵触的时候,只有一个选择,不是大声嚷嚷来表演自己的“独立性”,而是辞职,脱离团队,离开权力的位置,然后再谈所谓“独立性”。知识分子的负责对象是自己一人的信念,不偏不倚,所以“独立性”重要。执掌公权力的官员,是对整个政治机构和社会负责,他必须把他的个人放下;如果要凸显个人,你先离开那个位子,这才是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