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杨早
《罗曼蒂克消亡史》,我是当成《渡部传》或《一个日本人在上海》来看的。影片一开始,就用字幕交代说:他住在上海很久,说上海话,也像上海人那样泡茶馆和泡澡堂子,已经没有人把他当作日本人(大意)。

▲
浅野忠信在剧中扮演渡部
这就是传主的待遇:称“他”而不名。整部戏确实都是围绕“他”——浅野忠信饰演的日本间谍渡部,一步步展开,回溯,闭合,落幕。全片只有他,是福斯特所谓的“圆形人物”,他的前世今生,出处没时,性格喜好,均历历可见。相比之下,连葛优饰演的陆先生都相当模糊,颇受好评的黑社会小巴辣子童子鸡有头无尾,遑论他人?
如果我没有记错,渡部是中国影视里第一个大写的“在上海的日本侨民”形象(你不会跟我提《霍元甲》里的浪人吧?),而构成他活动背景的那些人,陆先生(杜月笙),王先生(黄金荣),老三(张啸林),吴小姐(胡蝶),都已经是太熟悉的符号。这一个线头不提不要紧,一提起,就是东亚近代史上一条无法掩藏的伏线。
1904年,商务印书馆编辑徐珂为许炳榛的《甲辰考察日本商务日记》作序,感慨“我国与各国交涉,近数十年为盛,我国之政治之实业之风俗,殆无一不为各国所洞悉,其著书言我我国事者,统计之翔实,评论之精核,或较胜于我国人。彼果操何术以致此夫?亦其驻于我国之公使领事与夫游历之官士,以至行商传教之俦,皆各任侦探之务,而能各举其识故也”。徐珂感慨,中国商民,无知无识,在外国住得再久,也没有情报贡献于祖国。当他说这话的时候,心目中的比照对象,也包括正在中国急速扩张侨民势力的日本吧?
就在1904年12月,北京大学堂教习服部宇之吉,受北京驻屯步兵队长山本中校的委托,“在留驻北京之日本官民中各方面广求适当人物”,共同调查、编纂成《北京志》。参加编写的十七名作者里,有北京大学堂、北京警务学堂、北京法政学堂的日本教习,有领事馆书记生,有北京驻屯步兵队的军医,也有一名“清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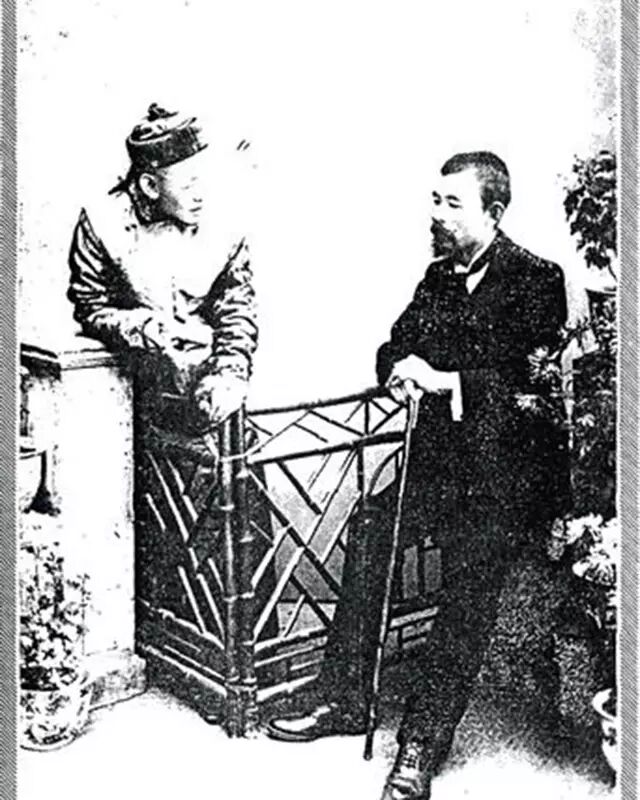
▲
清末生活在北京的日本教习
《北京志》分为三十九章,自人口、种族、政治、军事、商业、社会、教育、舆论、市政、旅游,无所不包。书的用意很清楚:“本书收集了有关北京的一切事项”,以裨日本政府“对北京有全面的了解”“促进对中国之开发”。在清末民初的北京诸多记载中,我们确实找不到一本比《北京志》更全面详实的记录了。日人对北京社会了解之深入,一百多年后读到,仍然让人咋舌。
据《北京志》记录,日本侨民(除驻军外)于日俄战争前,在京人数不足600人,战争期间一度下降至500人以下,和平之后,又增加至600人以下。北京的日侨中“有相当资力之商人为数甚少”,但是,区区五六百人之日商,却涉及北京社会的16个行当,包括:
银行业、杂货商、石油煤炭商、茶商、当铺商、书籍文具店、照相业、运输业、报社、掘井业、旅店业、建筑业及西式家具业、餐馆、理发业、卖药业、印刷业。
然而上海的日侨,较之北京,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在《北京志》截稿的1907年,上海的日本人数量已经达到了6268人,并每年以超过1000人的速度增长(除了1910、1911、1912三年有所减少),1933年“一·二八事变”后达到最高值26901人,之后又逐年减少,到了《罗曼蒂克消亡史》开篇标明的“1937年,淞沪会战前夕”,上海的日本人仍有23672人,而从事的职业类别,也有近50种。
在《罗曼蒂克消亡史》中,日本方面想约“上海三大亨”共组“东亚共荣银行”,陆先生与老三在谈判当夜反目,陆家被灭门。选择谈判地点时,王先生说了句“弗要在虹口”,于是陆先生把谈判地点安排在了渡部开设的日料店——也就是说,这家日本料理店不在虹口。这确实是蛮奇怪的。
此时的虹口,有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驻扎,据1924年的《日本案内》,上海日本人的九成,都居住于此,“说其是日本小都会也不过分”。清末民初的社会小说里,一说起吃日本料理,都是直奔虹口。

▲
《罗曼蒂克消亡史》剧照
渡部的日料店开在虹口之外,或许有一种可能:面向的是英租界内的日本银行公司的职员,那里有横滨正金银行、朝鲜银行、台湾银行、三井银行、三菱银行、住友银行、三井物产、日清汽船、日本棉花等。这些公司的职员,大部分也住在虹口,不过不少公司高层住在英租界。由于居住地域与从事职业的不同,上海的日本人社会还分裂成了“会社派”与“土著派”两大社群,还经常因为自治事务闹纠纷。
日本侨民初到上海,经常因为固执地改装租住的房屋为日本式住宅,与中国房东发生纠纷,由于日本在华势力的高涨,这种纠纷往往以中国房东的失败告终,于是英租界与公共租界的中国房东纷纷拒绝将房屋租给日本人,这也是形成虹口“日租界”的重要原因之一。渡部能在虹口之外建成那么大的一家原汁原味的日本料理店,不知是仗了日本驻军的势,还是靠了青帮老头子的名片?总之,对于一个时刻标榜自己要融入中国社会的日本人,却在虹口之外弄了那么大一个日本料理店,怎么看都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渡部在与青帮老头子们打麻将时,声称自己是“上海人”,“如果日本人来打上海,我就要和他们拼命”。在座的几位老奸巨猾也不知信不信。不过说话这当儿,上海社会的中日冲突,早已弄得不可收拾。
首先是经济上的竞争。入民国以后,上海作为日本投资市场的重要越来越被重视。日本对上海的投资从1914年的6000万日元暴涨至1930年的4.3亿日元,这种经济侵略也遭到快速成长的上海民族企业的抵抗,商战之激烈,达于极点就会用战争手段解决。淞沪事变后,一位日本小说家村松梢风在《中国公论》上发表文章,表达了日本国民的共同心态:
日本人无论如何不会放弃花费五十年营造的“上海日本”。每年的长江贸易额至少五六亿,多的时候七亿以上。如果说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长江贸易则是日本的营养线。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丢弃这条营养线。无论打什么样的仗,也不会放弃如此巨大的利益。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帮助上海的三万居留民,不能对他们见死不救。这当然是国家和政府的义务。
《罗曼蒂克消亡史》开篇所述,陆先生在为解决工潮,稳定上海经济秩序而努力,这当然是日本财阀不愿意看到的。

▲
内山完造夫妇
另一方面是上海日侨社会的激烈情绪。内山完造后来在回忆录《花甲录》里写道:“据说自1915年抵制日货运动以来,上海的日本居留民中就盛行这样一种说法,即华北的中国人知道日本的实力,所以不反日,上海不知道日本的实力,将日本人当傻瓜,激烈地反日。所以必须让他们知道日本的实力。”主张“膺惩中国”的主要是“土著派”,这些中小商人在反日运动中遭受的损失最大。1931年12月6日,“全支那日本人居留民大会”在上海召开,参会者达3500人。大会发布了强硬的宣言,要求“帝国政府必须采取积极手段来消除全中国的抗日运动……帝国政府必须拒绝姑息的解决方法并拒绝第二者的干涉”。
在这种汹涌的情绪下,1932年初的一起舆论事件成为淞沪事变的导火索。1月9日,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发表了一条报道:“日皇阅兵毕返京突遭阻击,韩人刺日皇未中,不幸仅炸副车,凶手即被逮。”日本侨民对此极为愤怒,指称《民国日报》“不敬”——应该是针对报道中的“不幸”二字,炸中副车是不幸,那炸到天皇的座车就是大幸喽?
对此,《民国日报》拒绝更正道歉,说“本报不独无侮辱日本元首之意,且亦于记载之中,微露惋惜词气”,说日本侨民的抗议是因为“日领馆中半通华文之辈所曲解或误释”所致。于是上海日本侨民决定上街游行。关东军乘此机会,在上海制造了杀伤日莲宗僧侣与袭击三友实业社两起事件。至此日本侨民的狂热情绪达至顶点,即使上海市长吴铁城表示接受日本领事馆的全部四项条件也无法平息这种情绪。在他们的呼吁下,日本海军找到了与在东北制造事变的陆军竞争的机会,淞沪事变遂于1月28日爆发。
“一·二八事变”后,日本人在上海更为强势,虹口的日本商店,“一·二八事变”前有60馀家,至1940年达到600家,占虹口地区所有商店的90%, 以致虹口被称为“小东京”。后世研究者说:“虹口虽然没有日本租界,但实际变成了日本租界……1937年‘八·一三’以后,虹口成为日本军队的占领区。”
1937年之后,青帮大佬隐退的隐退,出走的出走,投靠的投靠。这时,渡部已经假死遁身,换了一个身份。他还继续在上海从事间谍活动吗?他在这样的环境中,还需要再说上海话穿长衫打麻将吗?还是彻底回归到他钟爱却被压抑的日式生活,直到主动或被动地被送上菲律宾战场?
无论如何,渡部这样一个在上海的日本人,在他的形象背后,或许是明治维新之后涌向中国的越来越多的日本商侨,或许是日方培养出的大批“中国通”——历次上海之战,政府中密布被日方收买的汉奸,中方各种情报对于日方几近透明,又或是像内山完造那样,居住中国时间很久,对中国人与中国文化充满善意又不乏轻视……《罗曼蒂克消亡史》真正称得上“刻画”而又让人耳目一新的形象,唯有渡部。
原标题:《罗曼蒂克消亡史》为什么不改名叫《一个日本人在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