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撰文:Colin Kidd
翻译:陶小路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
ohistory
自从2007年9月我在北岩银行一家分行外看到一长串焦虑的存款人以后,我心里产生了一种无法遏制的想法: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可能部分在我们这个时代重演。北岩银行发生的挤兑预示了一场金融危机,这场危机与1929年的金融崩溃的规模相当;在那之后,保护主义,威权政治,蛊惑民心的民粹政治和本土主义在西方国家卷土重来;俄罗斯在克里米亚、乌克兰东部横行霸道,争夺地盘。但这种焦虑并不新鲜。《民主制度如何终结》(How Democracy Ends)、《民主国家如何消亡》(How Democracies Die)等书名的标题呼应着让-弗朗索瓦·何维勒(Jean-François Revel)出版于1983年的《民主国家如何终结》(Comment les démocraties finissent)。咄咄逼人的保守主义者的何维勒认为,西方民主制度注定失败,它的开放、多元化以及对批评的容忍使其在共产主义制度面前变得脆弱。他在很多地方都看到了民主制度陷入瘫痪、无能的种种表征:国际紧张局势趋于缓和;和平运动和反核运动的扩散;人们普遍认为反对共产主义是反动的,反对共产主义意味着反对进步。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很多人和何维勒一样对民主制度感到忧心忡忡。1974年2月,国内文官首长(Head of the Home Civil Service)威廉·阿姆斯特朗爵士(Sir William Armstrong)的精神一直处于严重崩溃状态,他当时确信,民主制度在矿工与特德·希思(Ted Heath)政府的对抗中处于险境。阿姆斯特朗的同僚、财政部常任秘书长道格拉斯·艾伦爵士(Sir Douglas Allen)更是当着众人面猜测,会不会自己有一天来办公的路上看到坦克列队停在皇家骑兵卫队阅兵场,同僚们无法判断他是否在开玩笑。英国当时是否处于一场左翼革命或者反革命政变的边缘?那样的历史时刻过去了,现在让人很难相信的是,在那个1978-79年“不满的冬天”
【Winter of Discontent, 指的是英国1978年至1979年的冬天,工党政府强制实行工资封顶之后,英国出现大范围的工会罢工。该说法出自出自莎士比亚剧作《理查德三世》的剧本开首对白,原句为“吾等不满之冬,已被约克的红日照耀成光荣之夏”(Now is the winter of our discontent, made glorious summer by this sun of York)——译者注】
过后,许多普通的工会会员认为工会权力对民主制度的威胁比玛格丽特·撒切尔要大,1979年转投保守党。1976年,当时的美国还处在水门事件的阴影下,美国独立二百周年纪念日在未经选举产生的总统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主持下低调举行。福特先是取代了声名败坏的前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Spiro Agnew),然后又取代了名誉扫地的总统尼克松。一些论者讨论了在如今被称为“帝王式的总统”
【“帝王式总统”(imperial presidency)这个说法来自于小亚瑟·施莱辛格出版于1973年的一本颇有影响力的《帝王式总统》(Imperial Presidents)的标题;施莱辛格在书中论述道,美国总统享有着巨大权力,超出了宪法赋予总统职务的权力】
的现实下,民主制度是否能够继续正常运行。三方委员会(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是大卫·洛克菲勒创立的讨论会,与会者是来自北美、西欧和日本的决策者、学者和记者。1975年,三方委员会发表了一份题为“民主制度的危机”(The Crisis of Democracy)的很有争议的报告,该报告认为,因为在福利上承担责任过大,民主制国家陷入了困境。当时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掌握在军政府手中——智利的皮诺切特、玻利维亚的卡尔洛斯·班泽尔(Carlos Banzer)、阿根廷的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Jorge Rafaél Videla)以及巴拉圭的阿尔弗雷多 · 斯特罗斯纳(Alfredo Stroessner)将军;南欧各国的民主制度很脆弱。葡萄牙初创的民主制度产生于1974年由中下级军官发起的政变
(亦即“康乃馨革命”——译者注)
;同年,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希腊军政府倒台。1975年,佛朗哥将军去世,西班牙的民主过渡进程开启;1981年,西班牙的一场未遂的军事政变遭挫败。
尽管如此,西方民主仍然存活了下来。到了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一篇文章,宣告了“历史的终结”,后来这篇文章被扩充而成的书成了畅销作品。福山坚信,随着东欧共产主义的崩溃,唯一一个还没有崩溃的理想便是自由民主制。即使在当时看来,他的观点也存在着谬误,同时也过于傲慢。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对未来的乐观预测没有何维勒准确——后者曾经预测俄罗斯会对西方开放社会进行干涉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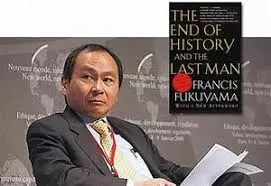
福山《历史的终结》
大卫·朗西曼(David Runciman)认为,我们许多人觉得可以从20世纪30年代或70年代的历史中寻找当前民主困境的确切先例,但是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他建议,
我们应该去回看19世纪90年代发生的民粹主义风暴。
在当时的美国,反叛的民主党人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成功地占据党内地位
【1925年,田纳西州教师约翰·斯科德斯(John Scopes)因为教授进化论遭到起诉,在那场审判中,威廉·詹宁斯·布莱恩担任检察官,他作为的检察官的职业生涯也在这场审判之后终结】
。与此同时,法国因为德雷福斯事件被撕裂。当时美、法两国内部存在着巨大分歧,可能会直接威胁到民主制度的运转;如朗西曼提醒我们的,信任是民主制度存在的根源。然而,两个民主国家都幸免于难,德雷福斯于1906年被无罪释放,民主党人最终驯服了布莱恩的民粹主义。
朗西曼警告我们,不要再把那些政变的经典符号——坦克开上街头,将军们占领电视和广播电台——当作是民主制度崩溃的先兆了。
这个过渡可能不会那么戏剧化,因此也就更难以被发现或者被防范。
实际上,他所谓的“僵尸化的民主制”现象可能已经是一些国家的现实:选民们确信自己决定了政策的制定,因为人们通过公投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而没有意识到,公投仅仅是一场舞台上的演出,政治精英精心策划了整场戏,他们不仅决定公投中的问题设置,而且决定了人们给出的回答的含义。朗西曼认为,民众很容易被欺骗,因为公投“被视为防止民主被颠覆的方式”。英国退欧公投的真正结果是“将更多的控制权交给了英国的政治精英,这些精英们的任务就是去实现英国人民曾经所希望达成的目标”。英国脱欧不是一场传统意义上的“政变”,但它让人们看到了要分清民主化与其对立面有多么困难。
朗西曼引用了政治学家南希·波密欧(Nancy Bermeo)的研究,后者描述了诸多类似于政变的现象,其中许多都会承诺实行民主,或者至少要做做样子,可能是通过“选票舞弊”,或者使用选举为已经掌权者的政权赋予合法性,即所谓“战略性操纵选举”;或者采用不那么突兀的方式,所谓“扩大行政权”,当权者使用不那么引人注意的方式逐步“侵蚀”民主规范 。如今,一场政变发生的标志是“当权者试图隐瞒已经发生的变化”。新的“非自由主义”的民主制度
【学者给它起的最佳名称是“竞争性威权政体”(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正在东欧国家“蔚然成风”,选举过程伴随着各种阴谋论,少数族裔被当作各种问题的替罪羊,人们举行各种活动,为自己拥有的所谓民主制度欣喜不已。在土耳其,埃尔多安狡猾地抓住实际发生的以及可能发生的军事政变为理由,以民主的名义颠覆民主。看似日常,被广泛认可,似乎不需要定义,于是这个概念被消解为一个具有讽刺性意味,充满悖论的词汇。

朗西曼
朗西曼提及的悖论中最令人不安的是我们中间很多人对那些投票支持脱欧、特朗普的人们居高临下的俯视。我们会认为:有些议题对选民来说难道不是技术性过高,对其理解能力的要求过高了吗?我们当然不希望被蠢人统治,或者更糟糕的,被至少在某些时候能够欺骗绝大多数人的胡乱吹嘘者统治吧?在过去几年里,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有这些想法。但是,万一我们这些人才是问题之所在呢?由懂最多的人或者自以为懂最多的人统治,也就是所谓的“智者治国”(epistocracy)表明上无疑具有吸引力。经济学家丹比萨·莫约(Dambisa Moyo)开出了自己的药方,她建议提高参选人的资格要求,其中包括需要有不少于规定时间长度的政治领域之外的工作经验;由政府出资进行选民教育,慢慢地让公民能够做出“正确的长期政策选择”;为选票赋予不同的权重,在选民中间划分出“不合格”、“合格”和“非常合格”三级,提高“选民中见识最多的那些人的影响力”。朗西曼表示对此无法认同,他认为这种“智者治国”的操作可能会制造出来一个傲慢、集体思维的“怪物”。对于未经训练、经常改变想法的民众,他这样写道:“在实施压迫上,无知和愚蠢无法像知识和智慧那样有效,正是因为它们在能力上的缺乏。”无论如何,“智者治国”总是会有蜕变为不民主的技术统治(technocracy)的危险:能够理解政治机制运作方式的人成为统治者,在这些人眼里,政治机制优先于民主价值观。
朗西曼对我们可能面临的各种威胁的不可知性保持警惕,他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在我们所知道的迫在眉睫的灾难面前,民主制度的反应迟钝。我们患有一种“末日疲劳症”。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核扩散造成的“潜在”威胁众所周知,但它缺乏政治“影响力”。
如果认为民主生活中会发生一场想要拯救地球的好人和不想拯救地球的坏人之间的战斗,并且这会是一场好人必然战胜坏人的战斗,那就错了。
实际情况要暧昧、混杂许多,且带着一种阴鸷的喜剧色彩:“双方都关心,双方也都不关心。两边的人都关心,是因为没有人希望世界末日到来。双方也都不关心,因为这是民主制度:人们真正关心的是谁有资格告诉他们该做什么。”
技术带来了好几个方面的挑战。
朗西曼从推特上的一个个热门事件和网上猎巫行动看到了古典时代所实行的直接民主,“善变、暴力、人们被赋予权力”,它是古代城邦暴民的现代版本。
暴虐的多数人不再能够杀死那些触犯众怒者,但是对其进行排挤的形式也变得更新、更快。一封措辞不当的电子邮件或一条推文就可以让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面临公众羞辱。言论自由是我们的自由民主制度中的核心部分,而且目前也面临威胁;但是
同样重要的是礼貌和虚伪——后者在我看来其实是民主社会里被最少称赞的美德。
组织政治(machine politics)能够让拥有广泛选民基础的政党发挥过滤作用,这种过滤作用可以将特朗普、极端分子和拒绝妥协的政治原教旨主义者筛出去,而这种组织政治如今已经被网络上的“回音壁”取代。如朗西曼在书中所写,曾经的政党“内部异质性强,不同党派之间有着非常多的共同之处,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共识”,如今党派对立的文化在网络上大行其道。据朗西曼在书中提供的数据,在1980年,接受问卷调查的共和党人只有5%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与民主党人结婚;而到了2010年,这个数字是49%。民众之间的党派之争达到了这种程度,民主的生活方式也就变得非常难以维持。
朗西曼认为,网络给“异常强烈的个人表达”提供了空间。不幸的是,如马克·扎克伯格这样的科技巨头对政治的认识非常之少,几乎是无知,可是这些人却认为自己巩固了民主制度,不认为自己导致了问题,而是提供了解决方案。在这里,朗西曼描述了一系列情势,当这些情势共同发挥作用时,民主制度可能会遭到破坏:一个对自己技术专制倾向没有自我认知的、脱离现实的精英群体;一个不眠不休的无政府主义电子平台,人们在这里抱怨种种无法得到解决的个人问题;一个被掏空的民主制度只能作出种种不痛不痒的妥协,提供短期解决方案,没有耐心、要求苛刻的网民对此感到沮丧和愤怒。 朗西曼表示,所有这一切,“使得
扎克伯格对美国民主的威胁比特朗普更大”。

扎克伯格这样的科技巨头对政治的认识非常之少
朗西曼没有兴趣向读者推销应对方案,但他确实也写了一些让读者安心的话,虽然这些内容读上去带有一种冷酷的闹剧色彩:“稳定的民主国家拥有一种非凡的能力,它们能在不去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依然做到规避这些问题可能导致的最坏情况。”他告诉我们,从未有过一个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人均8000美元的民主国家成为过军事统治国家。我们可能遇到的最糟糕的情况可能更像经济奇迹终结之后的日本或者像债务危机后的希腊。日本是一个老龄化国家,它的一半人口超过47岁;同时,日本也是一个政治体制僵化的国家。日本的政治“毒而无牙”:贪腐的政客源源不断,却也不会引发街头暴力或社会混乱。希腊则“实际上已经崩溃,但是表面上没有分崩离析”;在这里(希腊也是个老龄化国家),人们恐惧最糟糕的状况会发生,但是这个最糟糕的状况没有真正发生,
民主制度以一种“死而不僵”的方式持续存在着。
朗西曼的语调哀婉。让民主制度在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获得存在空间的历史条件正在发生变化。这个变化导致的结果可能是,民主制度开始“走下坡路”,目前正在经历一场“中年危机”。他认为
未来我们会看到民主制度“旷日持久的衰败”,其存活的条件是要进行各种大大小小的政治手术。
美国如果发生经济衰退会造成什么样的政治后果,会像日本或者希腊那样平缓吗?特朗普在大选后的早上发表的获胜演说出人意料的温和,当时我觉得他可能是另一个贝卢斯科尼,光是当选这件事以及总统这个位置能够给他的派头便足以满足他的虚荣心。我想错了。虽然朗西曼相信美国民主制度足够强大,特朗普不至于摧毁掉它,但他的确也在书中警告过,民主制度的中年后期光景并不会只有一个样子,不同的民主国家将经历各自的病痛,有时甚至会经历生死攸关的事件。但是,考虑到美国的民主制度面临种族分裂、激烈的党派之争的现实,外加这是个热爱枪支以及有着一个庞大的军工复合体的国家,我们真的能够确信美国的民主制度会“大器晚成”吗?
美国的确是当前民主制度弊病的一个独特例子。史蒂文·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和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在他们合著的《民主国家如何消亡》(How Democracies Die)中指出,
特朗普的当选并不是多数人选票的结果,他是由选举人团选出来的,而这个选举人团的设置正是为了防止特朗普这样的煽动者。
美国国父们很早就预见到特朗普的出现这一点并不能给人们多少慰藉。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这样写道,“那些倾覆共和国自由的人们,大多数是以讨好人民开始发迹的,他们以蛊惑家始,以专制者终”;这便是为何美国宪法第二条设置了总统的间接选举规则,将总统的实际选举权交给了选举人团,选举人团由根据各州立法机构制定的规则选出的地方名流组成。
国父们没有充分防范的是政党的崛起
,在那之后,这些有着独立思想的名流被政党转变为党派效忠者。两位作者指出,从很早的时候开始,“选举人(electors)就成了各政党代理人,这也就意味着选举人团将把关的权力交给了各个政党。”但是,这里我们也需要保持谨慎:过分热情的把关也是对民主制度的损害,因为“它会塑造出一个党派精英掌控的世界,普通人会被忽视,人民无法被代表。”
两位作者在书中指出,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政治的特色是两党合作,而这种合作的基础是一种“极其非民主”的折中举措。这种体系依赖于“种族排斥以及确立南方各州的一党独大地位”。在此之前,内战刚刚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种族和党派之间有很多冲突。只有当种族平等的理想被谨慎地搁置时,信任和宽容才能成为可能,而没有了信任和宽容,民主制度也就岌岌可危了。“宽容”和“克制”形成了美国民主制度的“防护网”,但是确保这种“宽容”和“克制”靠的是在官方认可下的对美国黑人的压迫和忽视。
此外,直到很晚近之前,“内部异质性”一直是美国政党很显著的特征,尤其是曾经的民主党,它在南方极端保守的白人新教徒与北方城市的蓝领、许多信仰天主教的少数族裔之间建立起了一个联盟。共和党也将东北部的自由派与中西部、西部的保守派汇集在一起。这些每个党内部存在的差异意味着一方不必要去妖魔化另一方。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共和党取代了民主党在南方的位置,两党成为不同的美国的化身,彼此对抗:一个是白人的、福音派和保守派的美国,另一个是多种族共同体的美国。两位作者注意到一组惊人的统计数据,“在政治参与程度比较高的美国人中间”,70%的民主党人和62%的共和党人“活在对另一方的恐惧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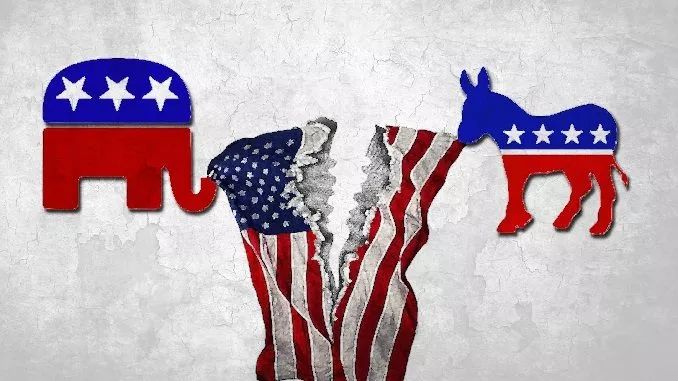
这种两极对立使得温和派没有多少行动空间。美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类似于特朗普这样的人物,史蒂文·列维茨基和丹尼尔·齐布拉特很了解威权主义者和排外分子对选民中虽不占多数,但仍然占有相当比例的少数派(在选民中占到30%左右)有着怎样的吸引力。因此,“真正能够防范”库格林神父(Father Coughlin),休伊·朗(Huey Long),麦卡锡或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
(以上都是知名煽动家——译者注)
这样的人的并不是选民本身的所谓民主本能,而是如今遭到削弱的政党机构。举行党内初选成为主流(其本身远非一件百利而无一弊的事情),终结了在充满烟雾的房间里进行秘密委任(以及排挤)的时代。即便如此,列维茨基和齐布拉特认为,共和党的大人物们本可以采取更多措施,阻止“一个并不真心实意拥护民主规范的总统”的当选。共和党高层的许多人“举棋不定”,包括约翰·麦凯恩、约翰·卡西奇、米特·罗姆尼和布什家族在内的关键人物拒绝支持特朗普。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勇敢地采取后续行动,支持希拉里。于是,党内这些大人物们团结一致的结果是让“选举变得正常”了。
诊断问题几乎和尝试解决问题一样困难。比尔·克林顿的前政策顾问威廉·高尔斯顿(William Galston)提醒我们,人民可以授权任何形式的政府,但是人民的授权并不能让强人政治成为民主政治。当然,一个领导者对于一些人来说是强人,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则是民主制度的拯救者。在大萧条时期,富兰克林·罗斯福公开提出他可能会向国会和美国人民寻求非常时期的权力。最高法院通过几个关键案件的判决,严重阻挠了罗斯福推行的“新政”,在那之后,罗斯福还试图对最高法院进行改革。从现在回望当时,罗斯福比特朗普更容易得到常规之外的行动空间。但这位连任四届的总统(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任职超过两届的总统)在很多方面都被认为是一位潜在的独裁者。民主制度下的领导者不可逾越的界限究竟在哪里?毕竟,如果没有罗斯福狡猾地行使其作为总统的权力,民主制度可能会在20世纪40年代初就终结了。
考虑到民主制度里包括了一系列政治活动,“民主”这个“简称”便显得极有误导性,因为这个“简称”假定选举活动中的竞争或者说人民意志是其关键特征。
全球的强人很趁手地以此为幌子,掌握了政权,而且他们可以凭借“人民意志”对自己的支持获得足够的合法性,然后令人信服地摆出作为民主人士的姿态。
至关重要的是,“民主”是一个含义残缺的术语,因为它忽略了对法治的尊重,遗漏了对中立机构(包括法院和公务员系统)的支持,对新闻自由的坚守,对少数群体的尊重,以及应当将党派反对者当作竞争对手而非敌人来看待。最终,在社会不同群体之间,政党之间,赢家和输家之间保持克制、良好礼仪和相互信任似乎与个人拥有投票权这点一样重要。另外,“民主”这个词还会导致其他一些理解上的混乱:我们所说的民主实际上是“代议制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与古代共和国的直接参与式的民主有着很大的不同。此外,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也看到,公民投票会让人分不清人民意志与经过选举产生的代表所拥有的授权。20世纪最重要的民主理论家、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更愿意用“多元政体”(polyarchy)来描述民主制度的运作方式,这套反应机制可以非常有包容性地,按照一定程序实现多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和解。达尔的这个术语不太可能流行起来,但是它能够提醒人们,在人类的众多活动领域中,政治领域非常容易受到名称和事物之间的混乱所影响。我们看起来对可能失去某些东西反应激烈,但是却并没有清楚地定义我们珍视的东西是什么。
我们对未来可能会发生的种种灾难的描述的确让早已存在于民主文化中的缺陷变得更加清晰。如今,人们非常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危险:我们可能会陷入限制多元化和自由的民粹主义政治之中。毕竟,如高尔斯顿所指出的,信奉多数主义的民粹主义者会以“彻底的民主主义者”自居,族群民族主义者(ethno-nationalists)也会如此,这些人这么做很“合乎情理”。但是,其它危险则不是那么明显了。高尔斯顿还提醒我们,自由派会将一些目标置于其它的目标之上,并且将自己的这些偏好等同于自由民主制的标准。在民主政治中,没有什么途径一定可以避免不自由的民粹主义和自由派精英主义的陷阱。
本文讨论的书籍如下:
-
How Democracy Ends by David Ruciman. Profile, 249 pp, £14.99, May
-
Edge of Chaos: Why Democracy Is Failing to Deliver Economic Growth – And How to Fix It by Dambisa Moyo. Little, Brown, 296 pp, £20.00, April
-
How Democracies Die by Steven Levitsky and Daniel Ziblatt. Viking, 311 pp, £16.99, January
-
Anti-Pluralism: The Populist Threat to Liberal Democracy by William Galston. Yale, 158 pp, £25.00, June
本文选自《伦敦书评》2018年9月13刊,《东方历史评论》受权译介。


点击下方
蓝色文字
查看往期精选内容
人物
|
李鸿章
|
鲁迅
|
胡适
|
汪精卫
|
俾斯麦
|
列宁
|
胡志明
|
昂山素季
|
裕仁天皇
|
维特根斯坦
|
希拉里
|
特朗普
|
性学大师
|
时间
|
1215
|
1894
|
1915
|
1968
|
1979
|
1991
|
4338
|
地点
|
北京曾是水乡
|
滇缅公路
|
莫高窟
|
香港
|
缅甸
|
苏联
|
土耳其
|
熊本城
|
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