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笔者案:李泽厚、刘小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很有影响的两代思想家,他们在屈原自杀的问题上都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在1988年出版的《华夏美学》和《拯救与逍遥》两书对“屈原自杀”问题的讨论都相当精彩,值得对读,一辩护一质疑。两人都文思喷涌。
李泽厚立足于儒道思想,更进一步,借屈原之死的思考发成浓烈的“情本体”思想的先声。中国传统“一个世界”,“社会历史”所积淀之“情本体”照样能够使人安身立命。

当时的刘小枫立足于基督信仰“拯救”的“十字架精神”的立场,判定“逍遥”的儒道皆是虚无主义,缺乏超越性之根基,没有成为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之可能。
不得不提的是,牟宗三立足儒家思想,建立一道德的形上学安立性命,其高足李明辉恰恰也是借助刘小枫所借助的舍勒的价值现象学,论证牟宗三阐发之“本体论之觉情”具有宗教般的超越性,不但根基稳重,人自己就具有神性,同时因“吾性自足”甚至优于基督宗教的“他者人格”。
这样来看,牟宗三和刘小枫反而在一个层面上争锋相对,李泽厚则在另一个层面上与牟和刘构成了争锋。但李和牟是中国文化本位的。
人生意义何在?基督信仰、共产主义信仰、儒家之“情本体”、儒家之“道德的形上学”,还是其他?重提这些思想资源,以便促进大家进一步的思考和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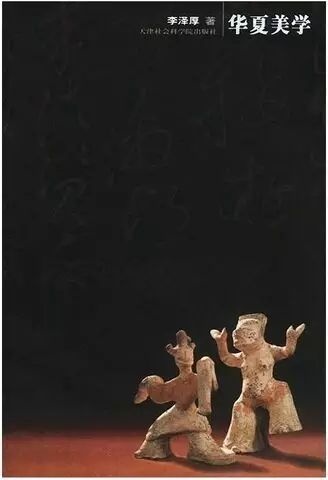
以下节选自李泽厚《华夏美学》第四章 美在深情 一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生死再反思:
屈原和庄子毕竟不同。其不同就在: 对人际的是非、善恶、美丑是否执着。庄否而屈是。庄以其超是非、同美丑、一善恶而超乎尘世人际,与大自然合为一体。屈则完全不同, 他是顽强地执着地追求人际的真理、世上的忠实,他似乎完全回到了儒家, 但把儒家的种种仁义道德远为深沉真挚地情感化了。儒、庄、屈的这种同异, 最鲜明地表现在对待死亡的态度上。我认为, 死亡构成屈原作品和思想最为“惊采绝艳”的头号主题。
无论孔、庄, 都讲过好些“邦无道则愚”、“处于材不材之间” 等等以保身全生的话, 这也就是所谓“ 既明且哲, 以保其身”的北方古训的传统教导之一。这种教导也同样存留在楚国和《楚辞》中, 例如著名的《渔父》: “圣人不凝滞于物, 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 何不沉其泥而扬其波; 众人皆醉, 何不餔其糟而戳其鲡” 、“沧浪之水清兮, 可以濯吾缨, 沧浪之水浊兮, 可以濯吾足。”但是, 这却恰恰是孔、庄都有而为屈原所拒绝的人生态度和生活道路。屈原宁肯选择死, 而不选择生,:“宁赴湘流, 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 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同上) 他的选择是那样的坚决、果断、长久, 它是自我意识的充分呈露, 是一种理性的情感抉择, 而绝非一时的冲动或迷信的盲从。
加缪说: “哲学的根本问题是自杀问题。决定是否值得活着是首要问题。世界究竟是否三维或思想究竟有九个还是十二个范畴等等, 都是次要的”。伽达默尔说:“人性特征在于人能构建思想超越其自身在世上生存的能力, 即想到死。这就是为什么埋葬死者大概是人性形成的基本现象。”如果说, 哈姆莱特以“活还是不活, 这就是问题”表现了欧洲文艺复兴提出的特点; 那么, 屈原大概便是第一个以古典的中国方式在二千年前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首要问题”的诗人哲学家。并且, 他确乎以自己的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个否定的回答同样是那么“惊采绝艳” , 从而便把这个人性问题—我值得活着么? — 提到极为尖锐的和最为深刻的高度。把屈原的艺术提升到无比深邃程度的正是这个死亡—自杀的人性主题。它实际构成中国优良文化传统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屈原正是在明确意识到自己必须选择死亡(自杀) 的面前, 来满怀情感地上天下地, 觅遍时空, 来追索, 来发问, 来倾诉, 来诅咒, 来执着地探求什么是是, 什么是非;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什么是美, 什么是丑。要求这一切在死之面前展现出它们的原形, 要就它们的存在和假存在来作出解答, “何昔日之芳草兮, 今直此萧艾也? ”“何方圆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 ” (《离骚》) 政治的成败, 历史的命运, 生命的价值, 远古的传说, 它们是合理的么? 是可以理解的么? 生存失去支柱, 所以“天问” 。污浊必须超越, 所以“离骚” 。人作为具体的个体现实存在的依据何在, 在这里有了空前的凸出。屈原是以这种人(个体血肉之躯) 的现实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来寻问真理。从而, 这真理便不再是观念式的普遍性概念, 也不是某种实用性的生活道路, 而是“此在”本身。所以, 它充满了极为浓烈的情感哀伤。
可以清楚地看到, 那是颗受了伤的孤独的心: 痛苦、困惑、烦恼、骚乱、愤慨而哀伤。世界和人生在这里已化为非常具体而复杂的个体情感自身, 因为这情感正是与是否生存相直接联系着的。事物可以变迁, 可以交换, 可以延续, 只是我的死是无可重复和无可替代的。以这个我的存在即将消亡的“无” , 便可以抗衡、可以询问、可以诅咒那一切存在的“有” 。它可以那样自由地遨游宇宙, 那样无所忌惮地怀疑传统, 那样愤慨怨恨地议论当政……“惟极于死以为态, 故可任性孤行”。(王夫之:《楚辞通释》)
他总是那么异常孤独和分外哀伤:
“鸳鸟之不群兮, 自前世而固然。” (《离骚》) “ 世困浊而莫余知兮, 吾方高驰而不顾。” (《九章· 哀邹》) “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 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 固将愁苦而终穷。” ( 同上) “涕泣交而凄凄兮, 思不眠以至曙; 终长夜之曼曼兮, 掩此哀而不去” (《九章·悲回风》) 。
这个伟大孤独者的最后决定是选择死:
“宁溢死以流亡兮, 余不忍为此态也。(《离骚》)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 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同上) “宁磕死而流亡兮, 恐祸殃之有再; 不毕辞而赴渊兮, 惜雍君之不识。”(《九章· 惜往日》) “ 临沉湘之玄渊兮, 遂自忍而沉流。卒没身而绝名兮, 惜雍君之不昭。” (同上) “知死不可让, 愿勿爱兮” 。(《九章· 怀沙》) “ 浮江淮而入海兮, 从子胥而自适;望大河之洲诸兮, 悲申徒之抗迹; 骤谏君而不听兮, 重任石之何益; 心挂结而不解兮, 思蹇产而不释。” (《九章·悲回风》)
王夫之说, 屈原的这些作品都是“往复思维, 决以沉江自失” , “决意于死, 故明其志以告君子”,“盖原自沉时永诀之辞也” (《楚辞通释》) 。在文艺史上, 决定选择自杀所作的诗篇达到如此高度成就是非常罕见的。诗人以其死亡的选择来描述、来想象、来思索、来抒发。生的丰富性、深刻牲、生动性被多样而繁复地展示出来, 是非、善恶、美丑的不可并存的对立、冲突、变换的尖锐性、复杂性被显露出来, 历史和人世的悲剧性、黑暗性和不可知性被提了出来。“伍子逢殃兮, 比干俎醢, 与前世而皆然兮, 吾又何怨乎今之人” 。( 《九章· 涉江》) “ 矰弋机而在上兮, 尉罗张而在下。” ( 《九章· 惜诵》) “ 固时俗之工巧兮……竟周容以为度。” (《离骚》) “ 天命反側,何罚何佑?齐桓九会, 卒然身杀。……何圣人之一德, 卒其异方。梅伯受醢, 箕子佯狂” 。(《天问》) 既然如此, 世界和存在是如此之荒诞、丑陋、无道理、没目的, 那我又值得活么?
要驱除掉求活这个极为强大的自然生物本能, 要实现与这个丑恶世界作死之决裂的人性, 对一个具有血肉之躯的个体本是很不容易的。它不是那种“匹夫匹妇自经于沟恤”式的负气, 而是只有自我意识才能做到的以死亡来抗衡荒谬的世界。这抗衡是经过对生死仔细反思后的自我选择。在这反思和选择中, 把人性的全部美好思想情感, 包括对生命的眷恋、执着和欢欣, 统统地凝聚和积淀在这感性情感中了。这里的情感是自我在选择死亡而意识世界和回顾生存所激发的非常具体而个性化的感情。它之所以具体, 是因为这些情感始终萦绕着、纠缠于自我参与了的种种具体的政治斗争、危亡形势和切身经历,它丝毫也不“超脱” , 是执着在这些具体事务的状况形势中来判断是非、美丑、善恶。这种判断从而不只是理知的思素, 更是情感的反应, 并且在这里理知是沉浸、溶化在情感之中的。这当然不是那种“普遍性的情感形式”所能等同或替代。它之所以个性化, 是因为这是屈原以舍弃个体生存为代价的呼号抒发, 它是那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存在的本身的显露。这也不是那“ 普遍性的情感形式” 所能等同。正是这种异常具体而个性化的情感, 给了那情感的普遍性形式以重要的突破和扩展。它注入“情感的普遍性形式”以鲜红的活的人血,使这种普遍性形式不再限定在“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 的束缚或框架里, 而可以是哀伤之至, 使这种形式不只是“乐以和” 、“诗言志” , 而可以是“ 怆怏难怀” 、“ 忿怼不容” 。这即是说, 使这种情感形式在显露和参与人生深度上,获得了空前的悲剧性的沉积和巨大的冲击力量。
在儒家传统的支配下,效法屈原自杀的毕竟是极少数,因之,它并不以死的行动而毋宁是以对死的深沉感受和情感反思来代替真正的行动。因之是以它(死亡)来反复锤炼心灵,使心灵担负起整个生存的重量(包括屈辱、扭曲、痛苦……)而日益深厚。不是樱花式的热烈在俄顷,而毋宁如菊梅松竹,以耐力长久为理想的象征。所以后世效法屈原自沉的尽管并不太多,不一定要去死,但屈原所反复锤炼的那种“虽体解吾犹未变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心理情感,那种由屈原第一次表达出来的死前的悲愤哀伤、痛苦爱恋,那种纯任志气、坦露性情……总之, 那种屈原式的情感操守却一代又一代地震撼着人们的心魄, 而经常成为生活的和创作的原动力量。司马迁忍辱负重的生存, 秘康阮籍的悲愤哀伤, 也都是在死亡面前所产生的深厚沉郁的“此在” 的情感本身。尽管他们并没有去选择自杀—死亡, 却把经常只有面临死亡才最大地发现的“在”意义很好地展露了出来。它们是通过对死的情感思索而发射出来的“在”的光芒。“死生亦大矣, 岂不痛哉。” (王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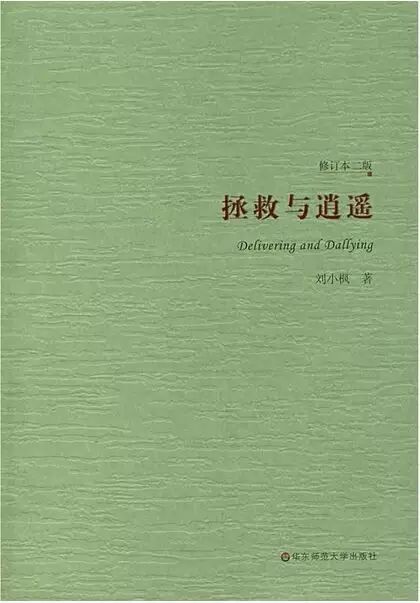
以下节选自《拯救与逍遥》 一 “天问”与超验之问:
儒家信念欠缺对人世的根本欠缺的认识把屈原逼上了绝境,遭到放逐后,屈原的信念也开始遭到放逐。这种精神放逐以一种奇特的形式表现出来:屈原时时不忘表达、抒发往日的怀念,仿佛毫不含糊地信守不移,却又不时流露出在儒家学说看来无异于“异端”的念头,以致最终提出“天问”。
屈原对信念的反叛首先表现在对儒家“仁”的怀疑,甚至到了欲以否定的地步。“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离骚》)。在世的孤独吞没了屈原,历史(王道)的价值让屈原彻底失望了。在忧伤、愤懑、苦涩的心情中,心系于民(“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抽思》,“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离骚》)的屈原,竟然也开始怨民、愤民(“世幽昧以昡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恶?”《离骚》),甚至产生遗世离群的念头(“世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涉江》)。本着儒家信念,屈原主动担当历史,自居为王道的命运,如今,他想把这一切统统抛弃,遁入大自然的怀抱,登高临远自乐畅情,摅虹扪天与物同情。在王道历史之外依息凤巢领略逸然趣味,吸露漱霜游心旷达。
的确,屈原已经走到彻底离弃儒家信念的边缘,再走一步就可以得到解救(“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涉江》)。君子的自足意志不能与历史、王道同一。就与自然同一(“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离骚》)。这是君子维系自身的意志自足的最后途径。
从儒家的现世承担到道家的逍遥于世有内在的联系,所谓儒道互补对君子来说是性命攸关的,否则不知多少君子会死于非命。孔孟肯定“道隐”(怀道隐遁),为君子提供了自救之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隐居以求真志”(《论语·季氏》)。“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为君子的意志自足留了一条后路。儒道互补的连结点仍然是个体人格的自足万德。无论儒还是道,个体人格都是不假乎外而足乎内的。当个体人格的自我实现在历史王道的路上受到阻碍,必然走向逍遥,那是另一种自我实现。孔子不过隐瞒了逍遥,仅表达过“吾与点也”的人格理想,看不起其它几位执着于现世事功的弟子,但从不多言。孔子似乎明白,心体自足光明透亮寂然不动需要最终的依靠,如果不承认隐遁逍遥,不仅君子的意志自足最终难以维持,他自己的存在方式本身也难以维持。毫不奇怪,甚而像据说大讲君子意志的性体论的《易传》,也承认隐遁逍遥的必要:“天地闭,贤人隐”(《易·坤卦·文言传》);“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易·大遇卦》);“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易·艮卦·象传》)。“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相对而言的道德原则。
奇怪的是,既然肯定了隐遁逍遥,尽管与庄子的逍遥不同,乃是心怀王道的逍遥,毕竟承认了王道(历史之道)的偶然性,为什么儒学要大谈君子人格与历史王道的必然同一?这不等于把君子人格出卖给历史这个魔鬼?什么是“行义以达其道”的必要条件?君子以什么价值标准来衡量天下有道还是无道?如果标准是王道本身(德政、礼乐),但历史中的王道无法自行实现,须要借助秘密政术(势、位),一旦出现道和德与势和位的分离,君子的使命就是要使它们重新合一,君子又何以判明有道无道?既然历史中的王道的实现只有靠君子出仕,从而使得君王行道成为可能,不然的话“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君子从何判断自己该不该隐?难道该不该隐本身就是“从心所欲”?
经过信念的放逐,屈原仍然回到了原有的信念,他走不出去。道家信念在屈原看来不过是“忽倾寤以婵媛”,因此他坚持不归隐、不独善其身,还要“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