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的断言:香港就是文学!从海上孤岛到世界都会,从帝国殖民地到社会主义特区,香港经验比传奇更传奇。

作者陈国球教授
陈国球教授用了十五章的篇幅,讲述了十五个不同的香港故事。始于工程浩繁的《香港文学大系1919–1949》十二卷总序,终于风雨如晦年代的居港诗人徐迟。作者一路带领我们游弋于学院内外:从驻节香港的殖民地大员,到心系劳工大众的左翼文学家;从求全责备的香港文学大系,到活泼精要的各式选本;从先锋的现代诗、人间小说与话题电影,到苍凉南音和悲情粤剧;从弥敦道上的咏叹,到维多利亚港边的回想……无数的香港故事,看得人感慨丛生。
作者开宗明义,表露文学以“抗拒遗忘”的心迹,笔触所及,皆是有情众生:
“香港”,由无名,到“香港村”、“香港岛”,到“香港岛、九龙半岛、新界和离岛”合称,经历了政治地理的不同界划,经历了一个自无而有,而变形放大的过程。重要的是,“香港”这个名称底下有“人”;有人在这个地理空间起居作息,有人在此地有种种喜乐与忧愁、言谈与咏歌。有人,有生活,有恩怨爱恨,有器用文化,“香港”的意义才能完足。(《香港的抒情史·自序》)
追述文学香港的前世今生,揭示香港对整个华人文化圈的意义,思考香港的未来。地区、中国、政治、殖民、现代性等等这些看起来如“三尺青锋”般冷硬的议题,经作者娓娓道来,化为写给香港的一部抒情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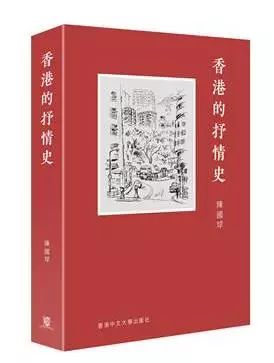
《香港的抒情史》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共四百五十二页,平装,全彩色印刷,定价港币一百三十五元,各大书局有售。本文选自第五章《诗里香港—从金制军到也斯》
一、从1925年的一首“香港”诗说起
LAMP-BESTARR’D, and withthe star-shine gleaming
From her midnight canopy or dreaming
Mirror’d in herfragrant, fair lagoon:
All her streets ablaze with sheen and shimmer:
All herfire-fly shipping-lights a-glimmer,
Flitting, flashing, curvingpast Kowloon:
Oh, to see her thus!
Her hill-recesses
Bright with household glow that cheers and blesse
Weary men and guides them home to rest:
And the criss-crossstrings of light ascending
Round the Peak, a-sparkle, circling, ending
Wherethe roadways touch the mountain-crest.
Ending? No! For humanaspiration
Passes here to starry consummation,
Mountain-roadsinto the Milky Way.
Earth is strewn with Danae’s goldendower.
Grandly here the Master Builder’s power
Crowns thework of England in Cathay.[1]
这首诗题作《香港》(Hong Kong),写于1925年11月,风格上与“维多利亚时期”及“现代主义”之间的“佐治时期诗风”(GeorgianPoetry)相近。[2]这首诗气象高华,以光亮闪耀的意象贯串,配合大量双声头韵,铿锵有致,节奏爽朗。全诗以灯火与星光起兴,前两节描写路灯、船舶灯号、天上星光、水中光影,渡过海港,从九龙到香港岛,闪亮山径蜿蜒至太平山顶;最后一节,以“完了吗?不”一句接通人间天上,直达九天银河,并以神女嫁妆(Danae’s golden dower)为喻,接引古希腊神话的世界,以英伦王国无穷无极之境为结。

金文泰
这首诗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鲁迅笔下的“金制军”。1927年鲁迅从广州到香港作两场演讲:分别是2月18日《无声的中国》及19日《老调子已经唱完》,根据他对中国文化当下现象的观察,以及对未来的预想,为于“新文化”尚在懵懵懂懂之间的听众做点启蒙工作。大概鲁迅这次香港之旅有一些不快的经验,他回广州后写了《略谈香港》、《再谈香港》,以及《述香港恭祝圣诞》三篇文章,对香港冷嘲热讽。[3]《略谈香港》特别提到当时的港督金文泰;这位“金制军”在他眼中,是与前清遗老沆瀣一气的殖民统治者,共同在香港“保存国粹”,抗拒“新文化”。[4]事实上金文泰(Cecil Clementi,1875–1947;1925–1930在任)是少数精通国粤语的香港总督。他本是牛津大学古典学系毕业生,曾出版古典拉丁诗集Pervigilium Veneris 的翻译和研究(1911初版;1936三版),又译招子庸(1782–1850)的《粤讴》为英文(Cantonese Love Song;1904初版),其余还有哲学与历史地理的着作。可以说,在从政生涯以外,金文泰还是一位诗人学者。《香港》一诗载于他的诗集《诗游记》(A Journal in Song, 1928),是他1925年11月刚就任香港总督之职时作。这不是他第一次来香港;在此以前,金文泰已经有丰富的香港经验,历任新界助理田土官、巡理府、助理辅政司、行政立法两局秘书,以及署理辅政司兼两局当然官守议员等职。然而,这时他刚从锡兰辅政司调职回来,接替以强硬手段处理“省港大罢工”但效果并不理想的司徒拔(Reginald Edward Stubbs, 1876–1947;1919–1925在任)。
金文泰回到香港履任帝国在远东的殖民地高职,应是满腹鸿鹄之志,内心也是尽是喜悦,眼中的香港一片清明光亮,和平安静。当然,香港夜景之灯影璀璨,并不是虚言。香港地势崎岖而市区人口密集,随着城市发展渐渐构筑出独特的夜景。早在1887年,港督德辅(George William Des Voeux, 1834–1909;1887–1891在任)曾赞赏香港的夜色,说入夜以后的香港之美,“童话世界以外,无可比拟”。[5]金文泰诗中以光明的意象描述香港,显示他没有鄙视香港为化外之地。反之,金文泰对香港情深意厚,据说至1930年他与妻子要离开香港,转赴新加坡担任英国海峡殖民地总督及驻马来亚高级专员的时候,十分不舍,说:“我乐意留在这里,多于到任何其他地方去。”[6]另外,根据其后人忆述,金文泰常说他在香港渡过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7]
当然,诗中也毫不隐晦地展现出帝国殖民主义的视角。金文泰从一个全景的、鸟瞰式的角度描叙;这种叙述方式加强了叙事者与所叙述事物之间的距离感,而香港被“物化”,显而易见。翻译家闵福德(John Minford) 形容这首诗为“吉卜龄式”(Kiplingesque) 的英诗[8];结尾两行以为“香港”之明亮,正是上帝造物之工,为英伦在远东霸业加冕(Grandly here the Master Builder’s power / Crowns thework ofEngland in Cathay)。金文泰是出色的殖民地管理人,被视为“严肃、无所畏惧的老派帝国主义者”[9]。他以相对柔软的身段抚平“省港大罢工”引发的政治与社会问题[10];他扩大本地华人参政的权利,与新界乡民建立良好关系;他支持成立官立汉文中学,又向英国政府申请运用庚子赔款以成立香港大学中文学院;诸如此类的政绩,赢得当时舆论的好评。在西方历史学者眼中,“这位深思远虑、学问渊博的总督让香港变成更好的居住地”[11]。以今视昔,我们应如何诠释这位殖民主义代理人的内心世界?大概不是一两句简单的政治判语能了事。
翻看1925年的历史,我们知道金文泰笔下光辉灿烂的都市,并非当时整个香港的真实写照。当时省港大罢工尚在炽热进行中,社会秩序及经济大受影响,事件直至翌年才渐渐平息。二十年代香港还深受水荒困扰,又面临房屋不足、租金高昂、卫生情况恶劣、贫富悬殊等问题。[12]闪耀星空覆盖下,并非如诗中描述般岁月静好,而是一个在躁动中与生活缠斗的移民社会。我们有必要换一个角度,再细看过去的“香港”。
二、三十年代香港诗中的“维多利亚城”
三十年代以诗歌为香港地景留下纪录的有鸥外鸥(1911–1995)、柳木下(1914–1993)、刘火子(1911–1990)、李育中(1911–2013)等本土诗人。例如鸥外鸥就有“香港的照像册”等一系列刻画香港生活的诗,其中的《大赛马》与《礼拜日》,以不同的场景与事件,讽刺香港人精神生活的贫乏,将命运寄托于赌博,而“奢望”往往转成“叹惜”。 《狭窄的研究》写“香港/狭窄极呵,/高极呵/拥挤极呵。”更重要的是诉说香港之无根、变幻、浮游无所归依的生活:“没有一株树永久,/没有一座山永久。/没有一寸冷落了的土地永久,/没有一所房子永久”[13]。又如柳木下在1957年整理三、四十年代的诗作,题作《海天集》,因为“香港的碧海和青空,在某一个时期,曾经是我的寂寞的伴侣。[14]当中收入如1938年的诗《大厦》,写一个乡村少年与城市的高楼大厦对话,大厦的窗如眼睛望向远方;少年意想这是“望乡”,但得到的回应却是想望“纽约、伦敦”。当中“城”与“乡”、“世界”与“本土”等不同的期待视野互相颉颃,正是香港的写照。三十年代香港有不少高楼落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于1935年启用,位于中区的旧汇丰银行大厦。新的高层建筑物改变了都市的面貌,亦预示了以摩天楼作为城市标志的香港未来。柳木下用简洁朴素的语言写出香港日益富裕,并且渐趋西化的境况。诗的结尾略带感伤,暗指这城市将会朝着资本主义大都会的方向慢慢演变,往昔的纯朴一去不返。

30年代的香港
城市高速都市化与工业化,造成贫富不均、环境破坏等问题。新文学运动以来“为人生的艺术”与“写实主义”思潮在香港更有发展的空间。不少诗人在作品中刻画社会的黑暗面。例如作为写实主义的坚定拥护者刘火子,于1934年写成《都市的午景》一诗,主题就是社会之不公平:
长短钟针交指着正午的太阳,
说这是最平等的一瞬吧;
而地狱与天堂间的距离呢,远着呵!
金属的钟音回荡于都市之空间,
一下,一下,紧敲着人们之颗心。
于是标金局里的人散了,
堂皇的写字间也空着肚子
看那意大利批档的门阶,
流注着白色的人流,
而雪铁龙车子又把这人流带走,
一队,一队,水中的游鱼哪!
白色的人流把Café的肚子充实了,
丰满的Tiffin,奇味的饮品,
雷电机播散着爵士歌音,
一口茶,一口烟,笑语消磨这短促的一瞬。
金属的钟音回荡于都市之空间,
一下,一下,紧敲着人们之颗心。
于是繁杂的机声戛然停止了,
黑洞洞的机房放走了人,
揩着汗珠,喘息!
低矮的门阶,
流注着黑色的人流,
凉风拂去心之郁抑,
才知道阳光那麽令人可爱!
肚子空了,走吧,
行人道上游着疲惫的人鱼。
街头,渠边,蹲满了人,
两碗茶,一件腐饼,
耳间还留存着权威者吆喝的厉声,
一阵愁,一阵怨,
悲愤消磨这短促的一瞬。
长短钟针交指着正午的太阳,
说这是最平等的一瞬吧;
而地狱与天堂间的距离呢,远着呵![15]
这首诗虽以写实为宗,但结构上颇为用心。开首和结尾的重复构建文本世界的框架,中心部分则以相对错落的重复以并置贫富之间(“地狱与天堂间”)生活的差异。作者利用“正午”时针分针重叠喻意在同一时空之下不同阶层却处于不同境地:“堂皇的写字间”、“意大利批挡的门阶”、“雪铁龙车子”、“café”、“Tiffin”等描写有闲阶级的日常生活;这些华丽的意象与接着写低下阶层的“黑洞洞的机房”、“低矮的门阶”、“疲惫的人鱼”、“街头渠边”、“茶”与“腐饼”等形成强烈对比。时钟在时针分针两相交叠之际敲响,钟音回荡之间就出现“现在进行式”(“交指着”、“紧敲着”、“空着”、“流注着”、“游着”、“留存着”)的各种活动,与全诗此起彼落的对位节奏互相支援(“一下、一下”、“一队、一队”、“一口茶,一口烟”、“一阵愁,一阵怨”),由音声牵动因各种意象而生的情绪,造成看似平实,却暗存巧思的“现实主义”佳作。
蔚蓝的水
比天的色更深更厚
倒像是一幅铺阔的大毛毯
那毛毯上绣出鳞鳞纹迹
没有船出港那上面遂空着没有花开
天呢却编回几朶
撕剩了的棉絮
好像也旧了不十分白
对岸的山秃得怕人
这老翁彷佛一出世就没有青发似的
峥嵘的北角半山腰的翠青色
就比过路的电车不同
每个工人驾御的小车
小轨道滑走也吃力
雄伟的马达吼得不停
要辗碎一切似地
把煤烟石屑溃散开去
十一月的晴空下那麽好
游泳棚却早已凋残了
至于李育中发表于同年的《维多利亚市北角》,则刻画了香港的另一个面向:一个水光水色的“抒情”境域:飘着白云的蔚蓝天空、波纹鳞鳞的蔚蓝海水,北角半山尽是翠青之色;但当这些“抒情式”的意象还未开始发挥作用时,作者马上配以绝不抒情、逆反自然的“人工”比喻,把读者的抒情感觉摧毁粉碎:蔚蓝海水的波纹好比足履践踏之下的毛毯纹迹,天上的白云看似工厂作业间撕剩的“不十分白的”棉絮,对岸的山有如秃发老翁,这边北角半山的树色却拿来与老电车的斑驳绿油漆相比较;“人”在此间不是享受自然之乐,而是吃力地推着矿产走在铁轨上。象徵工业文明的马达“吼得不停”、“要辗碎一切”,煤烟石屑四散……,成为全诗的高潮。结尾更清晰的点明:“人”与“自然”相交亲近的“游泳棚”,“凋残了”。[16]这种对“山水告退,城市方滋”的感喟,对“现代化”、“城市化”的批判,当中的环境保护意识,在三十年代的香港而言,可说是“前卫”。
三、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城市的“回忆”与“展望”

50年代的香港
北角位于港岛东北端,是最早期发展的区域之一。四十年代国共内战以来,大量内地移民来港;其中来自上海、宁波、南京一带的移民因文化相近,主要聚居于北角一带,故此五十年代的北角有“小上海”之称。六十年代以后,因为印尼以至东南亚地区排华,不少闽籍华侨迁进北角,而渐渐取代迁出的上海人而成为地区主要社群,所以又有“小福建”之称。物换星移,现时的北角各式高楼大厦林立,社会设施增加,聚集了不同种族、籍贯的居民。北角的种种变化,是香港作为一个移民城市的表徵;而此地也生发出许多香港文学的记忆,例如五十年代香港现代主义运动的推手马朗,就在1957年写过下传诵不绝的《北角之夜》:
最后一列的电车落寞地驶过后
远远交叉路口的小红灯熄了
但是一絮一絮濡湿了的凝固的霓虹
沾染了眼和眼之间朦胧的视觉
于是陷入一种紫水晶里的沉醉
彷佛满街飘荡着薄荷酒的溪流
而春野上一群小银驹似地
散开了,零落急遽的舞娘们的纤足
登登声踏破了那边卷舌的夜歌
玄色在灯影里慢慢成熟
每到这里就像由咖啡座出来醺然徜徘
也一直像有她又斜垂下遮风的伞
素莲似的手上传来的余温
永远是一切年轻时的梦重归的角落
也永远是追星逐月的春夜
所以疲倦却又往复留连
已经万籁俱寂了
营营地是谁在说着连绵的话呀
马朗(1933?–)是华侨子弟,在澳门出生,小时曾在香港居住;但他的文学事业主要在上海开始。他年纪轻轻就是《文潮》杂志的主编;是张爱玲小说最早的评论者之一,又与文坛前辈邵洵美、吴伯萧等人多有往还。他有一段思想左倾的时期,五十年代初理想幻灭,南下香港,为上海旧识罗斌主持环球图书杂志出版社的业务,利用商业报刊的余资办了香港五十年代最重要的现代主义刊物《文艺新潮》,在1956年3月创刊,发刊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到我们的旗下来!》是香港文学史上重要的文艺宣言,也吸引了不少年轻的本土作者投入这一波现代主义的风潮。五十年代的马朗,就是带着与许多来自上海的“南来文人”的文化资本,虽则他的文化养成本来就有香港的成分。[17]
1957年的“小上海”,对于沪上风华仍然锁在心头的马朗来说,其意义当不止于眼前风物。叮叮作响的最后一列电车,走在北角街头;它是从云雾间的记忆轨迹开到眼前?还是由春秧街角转向驶入心内的时间匣子?“濡湿了的霓虹”营造了“朦胧的视觉”;“紫水晶里的沉醉”、“满街薄荷酒的溪流”,把北角点染成一片春野;“登登”之声,既是小银驹驰骋的蹄响,也是舞娘们穿着高跟脚在踱步。“卷舌的”当然不是粤语,但这“夜歌”是北角的呢?还是上海的?“素莲似的手上传来的余温”,与“营营地说着连绵的话”,究竟都属幻觉还是全然现实?北角,对于不少南来文化人而言,是一个时空交错的叠影迷宫;北角大概就是马朗“年轻时的梦重归的角落”;或者说,是“怀想北地的角落”。马朗这首诗,让北角的夜晚,投下香港文化记忆中最迷离凄美的光影。

70年代牛头角巴士总站
相对而言,本土诗人也斯在1974年写的北角,却是另一种风景。诗题是:《北角汽车渡海码头》:
寒意深入我们的骨骼
整天在多尘的路上
推开奔驰的窗
只见城市的万木无声
一个下午做许多徒劳的差使
在柏油的街道找寻泥土
他的眼睛黑如煤屑
沉默在静静吐烟
对岸轮胎厂的火灾
冒出漫天袅袅
众人的烦躁化为黑云
情感节省电力
我们歌唱的白日将一一熄去
亲近海的肌肤
油污上有彩虹
高楼投影在上面
巍峩晃荡不定
沿碎玻璃的痕迹
走一段冷阳的路来到这里
路牌指向锈色的空油罐
只有烟和焦胶的气味
看不见熊熊的火
逼窄的天桥的庇荫下
来自各方的车子在这里待渡
也斯(1949–2013),梁秉钧,是本土文学发展的关键人物;他既是诗人、小说家、散文家,也是学者、大学教授;他又常常跨越文学边界,与从事不同媒体(如摄影、舞蹈、戏剧等)的创作人合作。他的作品,充满本土气息,又有非常国际的视野。这或者是香港的“本土”意涵:既不离弃脚下尘土,又经常流动、飘移,不停越界、溢出;又或者可以说,只有香港这种文化风土,才能孕育出也斯这种特性的文学家。我们说也斯“本土”,要注意他原在广东出生,来香港后居于港岛南端的黄竹坑的一个村落,十岁时举家搬到北角。北角是他认识城市生活的出发点。
也斯的“北角”诗没有马朗的浪漫迷醉。他以“寒意”开展这个文本世界,而承受这外力的是“我们”。“我们”与“外界”有所周旋。我们“找寻泥土”、“歌唱白日”,想“亲近海的肌肤”,这都是本于人性“情感”,出诸自然;可是结果总是“徒劳”,因为所面对的是“柏油的街5. 诗里香港| 139道”;城市由电力发光,已渐渐取代日照;虽然见到彩虹,但实际这是海面上的“油污”。这个城市的无声“万木”,是不是“三合土森林”?“巍峨”的“高楼”,只觉“晃荡不定”,如水中倒影。“我们”穿越这个城市,看到包围着“他”与“众人”的是“黑如媒屑”、“吐烟”、“漫天袅袅的黑云”,路上只见“碎玻璃”、“锈色的空油罐”、“烟和焦胶的气味”。这是一个“冷阳”的世界:有光有影,可是感觉是“冷”的、“寒意”逼人的。直至“我们”遇上来自各方的同道,在汽车码头前“待渡”。
七十年代的香港,本来就是充满现代城市的冷漠;经济腾飞,改善物质生活成为社会的主旋律;在殖民统治下的权贵与精英眼中,文化活动仅仅是“康乐文娱”的末节。然而这时不少的年轻文化人,在躁动之中思量存在的意义,批判现实种种不公义,叩问未来前途的可能与不能。在二十五岁的也斯笔下,北角也不见得是一个温煦和暖的地方。也斯以冷静的笔触,模写山水田园的技艺,捕足城市物象的形与色,展示这个不再田园的境界;当中隐含的,正是对“我城”的反思。用也斯自己的讲法,诗中出现的各种“物色”,固有其深义:
尝试同时描绘内在及外在两个空间,用“漫天袅袅、黑云”等表达城市的焦躁愤怒,又以“高楼投影在上面/总是如此幌荡不定”刻画眼前房地产及经济蓬勃的虚幻本质,还有未来的难以预计。[18]
可见写城市冷漠的也斯,内中并非冷感。正是心中火热,他才有冷静批判的力度;他才会在结尾想到“我们”与“来自各方的车子”,同在“逼窄的天桥的庇荫下”。“庇荫”的意象、“待渡”的想望,让读者有许多想像的空间。这是殖民统治的颂扬还是质疑?“来自各方”的车子,与“我们”的车,将会同船共渡,航向未来。[19]或者,也斯还是怀着“共济”的期待,盼望有抵达“彼岸”的一日。
也斯写这首诗的时候,香港的“1997”问题还未浮现。直到八十年代中英开始谈判,1984年签订“中英联合声明”,香港将会结束港英殖民统治,回归中国。由是人类政治史上罕见的漫长的“过渡”时期,才开始出现。我们不必渲染诗人的超自然预感能力,但也斯对香港在政治、社会,以至文化的“边缘”性,香港人难以主宰自己的前路等等问题,显然有深刻的省思。
四、“完了吗?”:与港督说再见

香港1984
由1984年12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订,到1997年7月1日政权移交,有十四年的悬宕与焦虑;期间世界、中国,以至香港,都经历不少扣人心弦的变化。该来的终于到来。四十八岁的也斯在这一年写下了《悼逝去的─和金文泰香港诗》:
我从山脚下仰望已经看不见星空
太灿烂了日本电器广告牌一重重
不会以为这是蓬莱这经济的特区
费尽思量勉强步和你异乡的韵律
多年来你的言语总令我结结巴巴
是冷漠还是伤感呢对于你的离去?
眼前闪过一列又一列璀灿的意象
犹似汉赋雄辩滔滔把我们来丈量
书写我们在传统的铁划银勾之中
洒落一点墨迹,是被弃的文字孤儿
不如你的期望,聆听世代人的善颂
我们没有窃笑,默对你弥留的病床
完了吗?不,消逝又幸存,辗转反侧
商人与士兵共舞取悦抑嘲讽星辰?
在言语买卖里也做过欢快的生意
大家习惯了在僵硬的形式里舒伸
雾岛迷湖连同巍巍崑仑泰山压顶
把宝珠埋葬,这样就完了吗?也许?不?

香港诗人也斯
1997年也斯追和的,正是1925年金文泰以总督身分到香港履任时写的一首诗。也斯很少会写出这种每行字数相同的齐整诗句;当中押上好几个行末韵,也不多见于也斯其他的诗篇中。这是以汉语诗的形式以回应金文泰对诗歌韵律颇为讲究的“佐治诗风”。这次隔世的诗歌应和,应是香港殖民历史的一个重要的文学铭刻。
金文泰满目是繁星闪耀的夜空;也斯从山下向上望,星空已不见了,因为街上灿烂的广告牌─香港的角色已被认作“经济特区”─掩盖了往昔如梦的星光。开篇的“今昔之比”,打开一条往返于“历史”与“现实”的通道。而“现实”与“未来”,也是由另一段“历史”来规限:“汉赋”与“铁划银勾”─传统的天朝文化象徵,会来“丈量”我们、“书写”我们;这与诗人说金制军所运用的帝国语言,“总令我结结巴巴”一样。事实上,语言文化本是一种宰制的力量;当不能自主时,就好比“被弃的孤儿”。英帝殖民时代要结束了,“我”─诗人,香港人─应该“冷漠”?“伤感”?还是“窃笑”?在烟花灿烂的日子里,“商人”(=经济)与“士兵”(=军事政治)共舞,合谋互利;诗人想到的是:崑仑泰山之倾压下,在迷惘中的岛民与金文泰想像的神女嫁妆,一并被“埋葬”了吧?是否一切都“完了”呢?
金文泰回应“Ending?”的疑问时,很坚决地说:“No”;他以为帝国是“无穷无极”的。也斯对“完了吗?”的问题,无法如昔日港督的肯定,只会充满焦虑地“辗转反侧”,“也许”、“不”之后,都要加上问号。
“费尽思量勉强步和你异乡的韵律”,是一种很复杂的感觉。也斯,和许多香港人一样,与昔日的金文泰的交往,就是他留下的一种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如何在帝国权力架构内找到某种可以共容的空间。然而,殖民主义的不公义,并不会随之而消失。1997年7月1日,还要为“殖民主义”唱一阕哀歌吗?
百年来,香港人亲临身受许多历史的荒谬,种种不解莫名,唯有香港的诗歌可以作证。
(初稿曾在2015年4月29日及6月18日于台湾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及清华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演讲;2016年6月8日定稿)
注释
1. Cecil Clementi, A Journal in Song (Oxford: Blackwell, 1928), p. 85。
2. 英皇佐治五世(KingGeorge V),1910年到1936年在位。从1912年开始,英国诗坛上陆续出现了由马殊编的五辑《佐治时期诗集》(EdwardMarsh, ed.,Georgian Poetry, 1912–1922),收入Edmund Blunden, RupertBrooke, Robert Graves, D. H. Lawrence, Walter de la Mare, Siegfried Sassoonand John Drinkwater等人的诗作,被视为这时期诗风的代表。
3. 三文均发表于《语丝》,分别是第144期(1927年8月)、155期(1927年11月)、156期(1927年11月)。其中《述香港恭祝圣诞》一文发表时的形式是致编者信,署名华约瑟。
4. 鲁迅《略谈香港》,页69–71。
5. 原文是“could hardly be equaled outside of fairyland”;引自AustinCoates, AMountain of Lights: The Story of the Hong Kong Electric Company (London:Heinemann, 1977), p. 3。
6. 原文是“I wouldgladly have stayed here rather than anywhere else in the world.”引自FrankWelsh, A History of Hong Kong (London: Harper Collins, 1993), p.390。
7. MayHoldsworth, Foreign Devils: Expatriates in Hong Kong (Oxford, England:OxfordUniversity Press, 2002), p. 38.
8. John Minford,“Foreword:‘PK’,” Islands and Continents: Short Stories byLeungPing-kwan, ed. John Minford (Hong Kong: Hong KongUniversity Press, 2007),p. xiii.
9. 原文是:“a no-nonsense, fire-eating imperialist of the old school.” 见PeterWesley-Smith, Clementi, Customs, and Consulsand Cables: Some Issues in HongKong-China Relations (Hong Kong: s.n., 1973), p. 3。
10. 参考John M.Carroll, Edge of Empires: Chinese Elites and British Colonials inHong Kong (Hong Kong Hong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35–158。
11. 原文是:“the thoughtful, learned Governor left Hong Kong a better place tolive with.” 见Russell Spurr, Excellency: theGovernors of Hong Kong (Hong Kong:FormAsia, 1995), p. 156。不过,同一位金文泰总督,在1930年离港到新加坡担任英国海峡殖民地总督及驻马来亚高级专员,其评价却大大不同,所行政策不受当地华人欢迎,留下“亲巫反华”的名声;参考C. F.Yong and R. B. McKenna, The KuomingtangMovement in British Malaya 1912–1949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90), Chapter 6, “The ClementiOnslaughtand the Lampson Diplomacy: The Taming of the ‘Double-HeadedSnake’, 1930–1931,” pp. 134–171;古鸿廷《东南亚华侨的认同问题:马来亚篇》(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4),《六、金文泰总督(1930–34)统治下的马来亚华侨》,页111–141;杨进发《新马华族领层的探索》(新加坡: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金文泰总督与海峡华人1930–1934》,页345–364;陈哲雄《殖民与移民:史密斯、金文泰总督与新加坡华人社团》(新加坡:南洋学会,2015),页178–225、265。
12. 参考科大卫(David Faure) 有关于早期香港普罗市民生活的描述,“The Common People in Hong Kong History: Their Livelihoodand Aspirations Untilthe 1930s,” in Lee Pui-tak, ed., Colonial Hong Kong and Modern China:Interaction and Reintegration(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pp. 9–38。
13. 《礼拜日》原刊《大地画报》第3期(1939年2月),《狭窄的研究》刊《大地画报》第4期(1939年3月),载陈智德编《香港文学大系。新诗卷》(2014),页139–141。《大赛马》原刊1939年,载《鸥外鸥之诗》(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页44–45。
14. 柳木下《海天集》(香港:上海书局,1957),《后记》,页83。
15. 刘火子《都市的午景》,原刊《南华日报》1934年11月23日,收入陈智德编《香港文学大系。新诗卷》,页103–104。
16. 北角的七姊妹区从1911年起,有中华游乐会搭建游泳棚,供水上活动;以后不同体育会先后在此区修建同类设施,广受市民欢迎。1933年香港政府预备在七姊妹区填海,要求各体育会迁离;由此引发了一场“保卫七姊妹海浴场”运动。李育中的诗写于1934年,意味着一种以文学介入社会的态度。香港政府于1935年正式开展填海工程,泳滩愈受环境污染,1940年政府全面收回各浴场。参考潘淑华、黄永豪《闲暇、海滨与海浴:香江游泳史》(香港:三联书店,2014),页41–66。
17. 马朗生平参考马朗、郑政恒《上海.香港.天涯─马朗、郑政恒对谈》,《香港文学》,第322期(2011年10月),页84–93。无可置疑,马朗是早慧文人。然而,现在一般记录马朗的生年为1933年,却未必可靠。根据香港教育大学中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助理李卓贤的查考,马曾在1936年上海《粤风》以及1938年香港《儿童世界》以原名“马博良”发表作品,各自标明为小学四年级及小学五年级学生。依此推算,其出生年应该早于1933年。
18. 原文是:“[The poem] tries to simultaneously portray the inner and outer space,using ‘floods andblack clouds’ to hint at the city’s anguish,‘staggering giants onwaves’ to depict theillusive growth of property and prosperity that one faces andtheunpredictability of the future.”见Leung Ping-kwan,“Urban Poetry of HongKong,” in Leung Ping-kwan, Amanda Hsu, Lee Hoi-lam, ed., Hong KongCulture & UrbanLiterature (Hong Kong: Hong Kong Story Association, 2009), p. 74。
19. 也斯曾说这结局暗喻香港的情况:“大家等着过渡,却不知未来会怎样。”原文是:“everybody is waiting in place to cross, not knowing whatthefuture holds”;见Leung Ping-kwan,“Urban Poetry of Hong Kong,” p. 74。
本文由公众号凤凰网文化(fhwwhpd)首发,感谢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不激不随(CUPress)授权活字文化发表!
陈国球:《香港的抒情史》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
作者獨闢蹊徑,從多年讀書和教授文學史經驗出發,談香港文學的多樣面貌:從中學語文教材到盜版工業,從現代詩、流行小說到蒼涼南音和悲情粵劇,北角、旺角、彌敦道,都是作家詠歎和重視的都市場域。
自序 / vii
一 走進文學史
1. 香港?香港文學?—《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總序》/ 3
2. 中國文學史視野下的香港文學─「香港」如何「中國」/ 37
3. 臺灣視野下的香港文學 / 73
4. 書寫浮城的文學史 —論葉輝《書寫浮城》 / 97
5. 詩裏香港 —從金制軍到也斯 / 127
二 可記來時路?
6. 文學評論與「畸形香港」的文化空間 —《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評論卷一》導言 / 149
7. 承納中國,建構虛幻 —香港的現代文學教育 / 193
8.「選學」與「香港」—香港小說選本初探 / 227
9. 情迷中國 —香港五、六十年代現代主義文學的運動面向 / 261
10. 可記來時路?—文學香港與李碧華 / 311
11. 香港文學的「曾經」與「可能」
—香港早期文學評論的流轉空間 / 333
三 申旦抒中情
12. 抒情 在彌敦道上 —香港文學的地方感 / 349
13. 政治與抒情 —論唐滌生的《帝女花》 / 367
14. 涼風有信 —《客途秋恨》的文學閱讀 / 397
15. 放逐抒情 —從徐遲的抒情論說起 / 413
▲ 转载请联系后台 | 入群请加微信:daskapit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