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年前,特朗普宣布参选美国总统时,很少人看好这位夸夸其谈、举止出格、毫无执政经验的亿万富翁。尽管他的胜出至今充满争议,但假如认为他仅仅是靠着充满煽动性、攻击性的争议言论达成了这一点,那就太小看他了。
他那句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确实击中了很多人的心,他以一种更贴近草根社会的直觉,意识到了这是美国人身上广泛存在的一个痛点。不妨这么说吧:如果是希拉里上台,恐怕也有这一场贸易战,区别可能只是两人做法上的不同。
如果去费城、底特律这些老工业城市看看就知道,那真的令人唏嘘。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破败,满街都是要饭的,普通人的收入陷于停滞——如今一个典型的美国大学应届毕业生的年收入,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只比1980年时高大约1000美元。这些是无论什么观点立场的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
近些年来因而有许多人都在探究这个问题:“美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曾两度荣获普利策奖的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在80岁之际写出了《谁偷走了美国梦》一书,从书名就可看到他的结论:
以往那个仅靠个人奋斗就能得到更好生活的美国梦,对许多人来说已经变得遥不可及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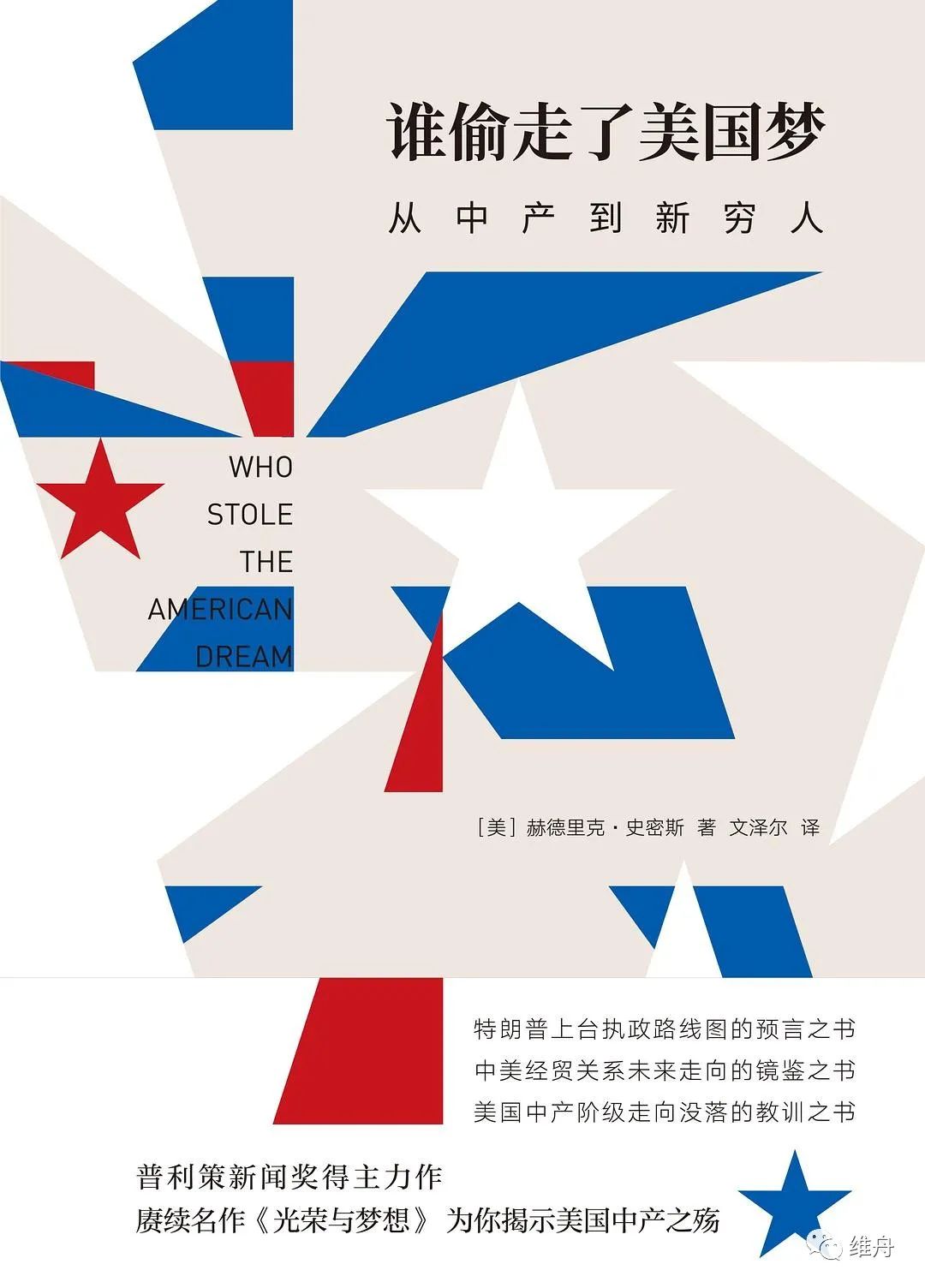
是什么造成了这一点?各方的说法不一。在右翼看来,这是贸易全球化、移民和大政府惹的祸,一如《觉醒:新民族主义简介》一书所证明的,这种反建制、反贸易全球化、反移民的根基在美国民众中广泛存在,这也是最坚决支持特朗普的民意基础;相反,左翼则归罪于1971年开始的“老板们的反叛”:一些右派的商业领袖逐步扭转战后的方向,推行过度的自由市场,其结果是巨量的财富流向社会金字塔的顶端,而中产阶层不但收入长期停滞,有些甚至沦为新穷人,因为他们的工作机会都逐渐因为成本考虑而流失到了海外。《谁偷走了美国梦》所持有的正是后一种观点。
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没有共同的大前提。尽管最近的调查证明,特朗普在共和党民众中的支持率高达88%,而民主党群体中仅有不到10%的支持率,然而
他们其实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如何扭转美国社会的贫富分化和社会裂缝
。
特朗普作为共和党的亿万富豪,开出的办法是减税,理由是这样才能鼓励企业家多投资、创造就业机会;然而在像赫德里克·史密斯这样的民主党支持者看来,这一番塞壬之歌早已不再能打动穷人,因为过去四十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富人们在获得减税之后并不会通过涓滴效应带动社会整体富裕,他们是在全世界外包工作机会,追逐利润的最大化。
两者的公约数在于:他们都相信要让流失的工作岗位回流到国内,为此就要提倡购买美国货、甚至不惜四处点火发动贸易战。
事实上,早在2006年美国大选时,两党虽有诸多分歧,但在为美国就业机会流失而抨击中国这一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

这是因为,
“让美国再次伟大”这句话本身就意味着回到“过去的好时光”
——那是1970年代之前美国制造业仍然繁荣的时代,这也是美国中产阶级得以充分就业的基础。
美国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反对贸易全球化,说到底原因就在这里:他们看到的不是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好处,而是“原本属于自己”的工作机会通过外包、代工等方式流失到了海外,因为那些地方的工人成本低得多,资本只服从资本的规律。这确实让美国的跨国企业赚取了更为丰厚的利润,但问题在于,企业并不会将自己在海外攫取的丰厚利润和国内的雇员分享,反倒常常拨出一大部分作为对商业领袖的犒赏。在此,
答案是很明确的:偷走美国梦的正是这些巨富阶层,是他们为了实现自己利润的最大化,无情地抛弃了国内的中产阶级群体
。
这也是全书中最精彩的一部分,赫德里克·史密斯以其长年记者调查的老到笔触,将当下美国社会裂缝的症结追溯到半个世纪之前的那场文化内战——正如《六十年代与现代美国的终结》一书所证明的,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深刻地改变了美国,以至于此前与此后的美国几乎在各方面都截然不同了。虽然女性、黑人等边缘群体在当时争取到了应有的权利,但捍卫传统保守价值和既得利益的群体随即开始做出反应,带动美国向右转。
没错,工人们获得了更有保障的权益,那工商界老板们就开始将工作机会迁往西南部的“阳光地带”——不是因为那里更暖和,而是因为那里没有东北部那样成熟、有组织的工会力量。与此同时,他们将制造业机会外包给海外那些所需报酬更低的工人,并推动1978年通过新的破产法,这使得企业管理层在公司破产期间仍能牢固控制公司,但却能一举废除原本长期有效的、许诺最低工资、健康保障和终身养老金的工会合约。换言之,
这些社会金字塔顶端的精英们甩掉了包袱,扔下了雇员让他们自谋生路,而去那些他们更不受约束的地方大赚其钱
。
这成了一个时代的分水岭:在1970年代之后,整个国家分成了两个美国,“公司CEO们和金融界精英们扶摇直上,而普通美国人则困于停滞不前”。以前美国之所以是一个机会之国,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人们的财富相对更平均地分配,而这有赖于几点:
立法保障、机会开放带来的社会流动、工商界精英的自我道德约束,以及工会力量的制约
。
但在近几十年,这些都失效了:企业家们组织起来推动对自己更有利的立法、社会阶层逐渐固化、精英们不再觉得自己有道德责任去照管工人,而是将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的目标。不仅如此,随着美国的“去工业化”,它逐渐从一个工业帝国转变成了一个消费社会,沃尔玛取代通用汽车成为最大雇主,而在这些服务业中,工人分散在一个个店面里,流动性也大,彼此更难形成有组织的力量去和资方谈判有利的劳动条件。1993-1997年间担任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长的Robert Reick在2007年撰写了一本书,将这种顶层精英不受约束地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形态称为“超级资本主义”,认为它已“蔓延到政治领域,它吞没了民主”。

不论好坏,有一点是确定的:
1970年代之后美国出现的新经济形态是不可逆的。
当制造业工作机会在发达国家中消失时,支持中产阶层的引擎确实减弱了,因为在随后的阵痛中不管取而代之是什么,都无法像传统的制造业那样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和退休保障。
这四十多年来,美国经济创造最多工作机会的是物流业,昔日的旧制造业厂房变成了巨大的物资仓库,昭示着整个经济转向后工业化时代。在这一波浪潮中,美国女性劳动者数量首次超过男性,因为很多男性制造业工人失去了就业机会,但女性却更能满足服务业经济的需要。
与此同时,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政府支付的薪资、补助超过民间企业的现象。就此而言,这些年来受益者多是民主党的支持者,而一个典型的锈带工人——一个失去制造业机会的白人男性,则更可能支持特朗普。与其说他们要的是“未来”,不如说他们要的是“过去的好时光”。
如果说这样的“诊断”大抵正中症结,那么对于“如何找回美国梦”所开出的药方却很令人遗憾。
试图通过贸易战的方式让制造业机会回流美国,这就算能稍稍见效,却根本无济于事——这么说是因为,早在三十年前,美国就曾通过敲打日本和西德的方式保持自身的竞争力,当时日德在货币升值、面临巨大政治压力的情况下,扩大对美国高端制造业的投资,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这才缓和了双方矛盾。
然而很显然的一点是:这根本未能逆转1970年代以来美国的大趋势。归罪于全球化贸易、外来移民和外国工人“抢走了”自己的机会,这与当年英国工业革命时卢德派归咎于机器夺走了自己工作,进而群起砸机器又有什么本质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