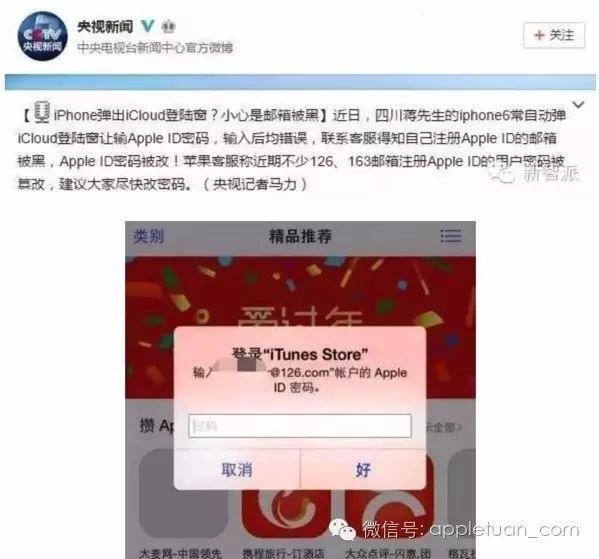我为什么写该书?
《莎士比亚历史剧与英国王权》出版问世已经有三四个月了,这是我疫情期间的第二部书,去年我曾经出版过一部《苏格兰道德哲学十讲》,该书是在疫情期间新写的,去年我在大百科全书还出版了一本《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是过去论文的汇总文集。《莎士比亚历史剧与英国王权》是我用一年多的时间写出来的一本新的学术著作。作为一个提纲挈领的初始发言,我想简单地叙述一下,在我出版了其他几本书之后,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我希望发言之后能听到其他五位年轻学者直言不讳的深刻分析和批判,使我重新思考下一步的学术研究如何展开。
《莎士比亚历史剧与英国王权》的写作凝聚了我的关怀。三年前,我曾在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出版过一部《中国宪制史(两卷本)》。之后,我一直想写一部关于英美宪政的书;由于宪法学涉及一些较为敏感的问题,目前仍然没有专门著述的可能性。但研究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是如何演变的,欧洲、美国乃至世界各国的宪法政治、市民社会和现代主权国家是如何兴起和发生的,这个问题意识一直萦绕我怀。正好在疫情期间,我在法学院开设了一门《法律与文学》的课程,发现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来表达原先想写英美宪政史的想法。在这门课里我主要讲三部分的内容:
第一部分是古典社会的经典作品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以古典的希腊城邦国家的构建过程,尤其以“俄狄浦斯王”和“安提戈涅”作为分析对象,探讨古典城邦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一些伟大的文学或戏剧作品中所展示的法律问题。第二部分是现代国家的发生,通过近代文学作品来展示一个现代国家发生过程中的一些与此相关联的法律和政治的问题,我当时就选择了莎士比亚。第三部分是通过科幻小说,如《弗兰肯斯坦》还有其他的一些科幻小说,来展示一个高新科技所编织的未来社会中法律和社会演变的一些问题。当时在这门课程的讲授中,我就集中研究莎士比亚的作品,尝试揭示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在发生过程中隐含着的政治与法律的问题。这是我为什么写这本书的第一个原因。
为什么写这本书的第二个原因更具体一些。莎士比亚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大剧作家,他所处的时代是英国封建社会近现代重要的转折时期,他的作品有37部之多,在我聚焦到莎士比亚作品之后,我就想要实现原先关于写一部英美宪政史的想法,所以我就集中到莎士比亚的历史剧——莎士比亚历史剧是他的戏剧作品中极其重要的内容——通过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来展示现代英国是怎么发生演变的。谈到莎士比亚的历史剧,这里就涉及到了王权问题,涉及到了王权之争:弑君、谋杀、复辟,权力的正当性,以及相关联的英国历史中所谓的大灾难,如何克服大灾难并实现英国新生的问题。
一个现代的早期的英格兰民族是如何构建起来的?这就会涉及英国史。在诺曼底王朝之后,依次是金雀花王朝、兰开斯特王朝、约克王朝、都铎王朝、斯图亚特王朝。莎士比亚正处在都铎王朝的最后一位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他去世前还经历了斯图亚特王朝的开始。在这一转折时期,莎士比亚历史剧所描述的虽然是封建制度下的王权,但这王权也是处在封建制度晚期的转型过程中;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后,英国很快就发生了光荣革命。虽然莎士比亚在光荣革命前去世了,但是他已经预感到未来社会的变化。
以王权为中心的莎士比亚历史剧的研究会涉及到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这是一个法律政治的研究或者政治法学的研究,研究的对象是莎士比亚的历史剧而不是文学戏剧。但它与主流的宪法学还有所区别:主流宪法学所构建英国宪政史是以大宪章作为起点,以光荣革命作为标志;光荣革命创立君主立宪制之后,整个宪政主义在英美、在西方开花结果。在《莎士比亚历史剧与英国王权》中,我企图以光荣革命为标志进行区分:英国的宪政史有两部分内容,有上半部的故事和下半部的故事。主流的宪法学或政治学,宪法学说史和政治思想史,强调的是后半部分的内容,即光荣革命以降的故事:宪政国家在英美和欧陆国家的不同的路径选择和演变。我曾经在《苏格兰道德哲学》这本书中勾勒出了宪政主义的这两个路径。我当然赞同宪法学的宪法史和政治学的政治思想史的主流路径。但是,在西方和中国的政治思想界和宪法学界,对于前半部分故事——即从诺曼登陆,尤其是从约翰王之后的整个早期英国的宪政史,以及从兰开斯特王朝、约克王朝到都铎王朝,甚至到斯图亚特王朝的早期英国围绕王权的现代国家发育——这方面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而莎士比亚的英国历史剧,恰恰展示了这一段围绕着王权的现代国家的演变史。在这个过程中,英国君主逐渐从君权神授,到马基雅维利式的有为君主的兴起,然后再到德才兼备的守法君主。亨利五世、亨利七世,尤其是他没写到的隐含着的伊丽莎白一世,这都是莎士比亚心仪的伟大君主。在戏剧化的创作中,通过故事情节的人物塑造,叙述重要的战争、谋杀和篡权,莎士比亚又展现了一些同样伟大却又邪恶的马基雅维利式的君主,像理查三世、亨利四世,都是有为的君主,但有时也是比较邪恶的君主。莎士比亚以文学化的富有宪政想象力的作品及其人物塑造,展现了对现代早期的有为、有德又合法的君主的理想寄托。这一部分内容在国内研究比较少,我们的认识也比较肤浅。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是相对的王权专制时期,这和后来的路易十四和路易十六的法国王权专制主义是不同的路径。因此,我们要区分这些内容,比较这些内容。英国之所以能建立君主立宪制,就是因为君主的演变。莎士比亚给我们勾勒出英国宪政的叙事、路径、框架,使得我们联想到,英格兰会有一场光荣革命而不是法国大革命。第二,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不单纯只是英国历史剧。我有一个广义的,更加泛化的理解,我认为莎士比亚历史剧包含着所谓四大悲剧中的至少三个悲剧,《哈姆雷特》《李尔王》和《麦克白》,这都涉及到了君主和王朝。更远则可以追溯到罗马剧,我重点分析的是《科利奥兰纳斯》和《尤里乌斯·凯撒》。我认为,这两部剧中,莎士比亚企图超出封建体制的王权框架,进入到更广阔的罗马共和国的贵族共和制,从罗马的共和国面临危机到罗马帝制的转变,在这两部剧中有所展现。这就使我大致分析了莎士比亚在广义和狭义上的全部15部历史剧。莎士比亚不是一个理论家或学者,他不是通过专著和概念化的表述来展示他对政治共同体的认知,而是通过一系列经典的戏剧,展示出未来的立宪君主制与现代英格兰民族国家的兴起。此外,这里补充的又有一些当时的英格兰市民社会的内容,上述这些大致就是本书的主体部分。本书的第一部分,我从广义和狭义上区分了莎士比亚历史剧,以及说明了历史剧中所谓的“都铎史观”。我们知道,宪政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都会涉及到辉格史观,但在此之前还有一个都铎史观。莎士比亚处在都铎王朝时期,他与都铎史观是什么关系?他如何突破了当时官方的都铎史观,建立起一套莎士比亚式的英国历史叙事?他的作品回应了这些问题。本书的第二部分重点分析莎士比亚的每一部历史剧。历史剧的内容非常有意思,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人物,不同的主题都很分明,几乎没有重复。关于这部分我对莎士比亚历史剧的具体分析,拙著中都有了,近三十万字,涉及到王位、王权、真假王冠,等等,在此我就不再展开了。最后,本书的第三部分脱离了莎士比亚的戏剧内容,转而分析英格兰的王权与封建法。封建法首先包括封建的王权体制,后来还涉及到封建法和教会法,即王权与教权的关系;英国政治是封建王国和天主教会的二元体制。此外,莎士比亚所处的时代又是英格兰的文艺复兴时代,又有市民社会和市民法的产生。因此,莎士比亚历史剧中大量的对权力和财富的认知,具有早期现代的一些内容;他不是纯粹的封建制度下的作家,而是从封建制度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位伟大的戏剧家。他的戏剧创造出了一系列具有英格兰早期现代属性的内容——不仅有君主的形象,也有市民的形象。随着戏剧故事的展开,英格兰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其现代市民社会、现代法治的立宪君主制的雏形,以及莎士比亚的理想寄托逐渐显现。关于英国王权的解读又可以追溯到罗马共和国向罗马帝国的转型。对于凯撒的解读,我也有自己的新认识:不能把凯撒完全作为一个专制的独裁者,他也未必就不是独裁者。在凯撒之后有几条道路,布鲁图斯也是一条道路,屋大维也是一条道路。“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莎士比亚有不同的解读方式,可以从文学的方式解读,可以从历史的方式解读,而我试图从政治和法学的角度,围绕着英国王权的发展,围绕着现代英格兰早期国家的形成,来解读莎士比亚的历史剧。这就呈现出了本书对光荣革命前英国早期宪政史的文学化的表述和分析;这也可以与一系列西方或者英国的法律史专家的纯粹的法律研究著作,如乌尔曼 (Walter Ullmann)、梅因(Henry Maine),形成对照。我们可以通过莎士比亚的历史剧,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展示英格兰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新法制形态的孕育过程。这对于今天中国社会也具有启发意义。我们一方面可以学习参照英美国家的塑造过程,另一方面也可以对比英格兰的现代国家的演进,寻找自己的道路。这样,通过分析莎士比亚历史剧就为我们打开了具有丰富想象力的阐释空间。最后我想说的是,真正了解英国和莎士比亚,可以把本书作为拐杖,但最终要自己进入和分析莎士比亚的作品;大家有机会可以到泰晤士河的环球剧场欣赏莎士比亚历史剧的演出,在文化氛围中感受英格兰民族是如何塑造出来的,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是如何奠基的。大体上说,英国开辟了现代社会的自由法治的源流;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展示了英格兰王朝的一系列波澜和曲折,但英国最终走向了比较好的前途。值得庆幸,莎士比亚生在变革的时代,变革时代中所对应的王朝的演变,某种程度上说具有建设性、积极性的意义;而有些作家所写作的王朝注定就是一个被遗弃的王朝,这是比较可悲的。所以,虽然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包含大量的悲剧,但在这些悲剧中,我们仍然感受到那个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幸运。莎士比亚的真正意义还需大家各自品味,进入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寻找和研究自己心目中的莎士比亚,以及莎士比亚作品中的英格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