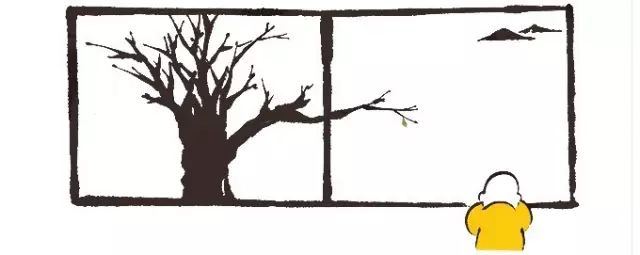👆懂不懂艺术都能看懂的
象外
编者按:
这是
《诛心三连》第三期
。
我给辛云鹏发去的“诛心”三问,实际半是严肃、半是游戏意味的。谁知道辛云鹏录了一个长达十几分钟的“真情”“自白”,发还给我。所以,我索性把他的回应转码成文字,放了出来,方便观众快速阅读。但艺术家说话时的场景和声情,还是很感人的,尤其是穿插在流利表达间的、偶尔的卡壳,语塞,急促的表达不出来。
因为象外暂未开视频号,视频号又有和公号端不同的观众浏览习惯和平台推荐机制,所以编者将视频挂在了自己的小号上,在象外公号发布。
辛云鹏答“诛心三连”
(因为是口头表达,所以不那么书面化)
:
雷徕你好,我就自己在家里录这个视频来,回应你三个问题。
首先感谢你去张某某的空间来看我的个展。北京的天气很冷,然后你去了两次
(第一次恰逢闭馆)
,非常感谢。你提的问题很好,但是我诚恳一点地说,就是这些问题,其实在处理这个展览和作品的时候没太想。因为因为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所以我可能很容易应付你的问题。所以我争取不应付。
辛云鹏 今天 Today 3000x3000x250MM 灯箱, 5号足球(2022卡塔尔世界杯赛场用球), 5cm仿真草皮, 11人足球赛场专用脚旗旗帜旗杆, 插入式旗杆弹簧腿, 指向性话筒防风套件以及低位三脚架, 打印传单, 线缆, 等⋯⋯,综合媒介。2024 Ed. 3+1Ap
图片均有艺术家及某某空间MOUMOU提供,此致谢意
是这样的,就是……首先真的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作品好在哪。我只是觉得,比如说我有五六件作品,我准备在这个展览上去实施,但是我会挑一些无论是从现实层面上,还是从作品的上下文关系上,更适合这个地方的作品。如果跟自己
(的创作脉络)
比较来说,有一些作品可能我还没有想好,或者在过程当中遇到一些问题,就会去更换方案。那么,在作出这些选择的时候,其实也有一定的成分,是没太思考,没太想清楚的,就把它实施出来了。这种情况我经常会出现。所以一个展览做完了以后,我发现问题很大,然后到下一个展览,再去弥补这个问题。很多作品都不是想好了才去做。这是对自己的夸奖吗?
我也教过课,我也被一些当代艺术家
(喊)
回学校做老师,被他们教育过。我发现一个共同性,就是大家在谈别人作品的时候,都谈得比较生动,比较有自己的视角,谈自己作品的时候,确实是很难谈。
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展览应该是在2020年,在周翊那里
(C5CNM,西五空间)
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那个展览的一个延续,一个姐妹篇,对我来说,它有一个上下文的关系。因为我觉得在那个历史节点去探讨一个中文语境的转换,对我来说比较有趣,比较感兴趣这个点——“从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到今天,我们看到足球赛场上中资企业的这种“中国第一,世界第二”
(的广告)
,这种变化。
昨天 Yesterday 2000x2000x300MM 电机, PVC水池, 高浓缩泡沫粉(视最终效果每日添加500g以内), 时间控制器或遥控感应开关, 等⋯⋯,综合媒介。2024 Ed. 3+1Ap
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
“
你觉得面对狼狈的大环境,搞趣味性反讽的叙事,会是一种消解现实沉重的行为吗?这样做是道德的吗?为什么?”
其实,我是这么看大环境的。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从事艺术创作到现在,我就没有一刻不狼狈的。现在大环境也狼狈,那就更狼狈了,但以前也没有好到哪儿去,是吧?从来没好过。
“搞趣味性的反讽叙事。”其实不是有意去做反讽和趣味的叙事。我觉得首先做作品这件事情,或者说做艺术这件事情,它本身就是有趣的成分在里面。无聊的作品也有,但那不是我自己感兴趣的那种作品。“会是一种消解现实沉重的行为吗?”“现实沉重”,包括悲观的东西,这个没有办法靠作品去表达。比如说,我个人比较消极的那一面,可能也在
(作品)
里边了,但只是我不想用这种
(视觉)
语言,用比较让人感觉沉重的语言来讲这件事情。
那种道德评判,当然就更没有考虑过了……可能有一些问题,你说的这个,可能我存在一些问题,就是,我有某种天然的优越感,那种优越感会不自觉地在作品里被呈现出来,这个是我需要警惕的一件事情。但总的来说,我个人不是一个很乐观的人了……我这么说很干巴。我觉得,我们在创作,还有从事当代艺术这件事上来说,其实最重要的,我觉得不是这些;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要讲一些陈词滥调的东西,无论沉重也好、还是反讽也好,尽量用一种好的方式来呈现,或者说用一种有机的(视觉)语言去呈现。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更重要,而且我也是更偏重于看这类艺术家的作品的。陈词滥调的东西,哪怕是很宏大的叙事,对于我来说,我也不太喜欢。
明天 Tomorrow 圆盘直径1200mm,高度可变,其他依现成品原始尺寸可变。木, 涂料, 步进电机, 传感器, Arduino控制板, 现成品, 等⋯⋯,综合媒介。2024 Ed. 3+1Ap
“既然您的装置作品那么通俗有趣,那您说说对晦涩、高冷、必须放在艺术系统的内部语境才能理解的装置作品的看法吧。”
“
如果觉得不够刺激,不够坏,那么也可以不搭理我
(这句不是问题,而是附注,艺术家搞错了)
。”
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分两个方面来说。一个就是,我其实很难对应上什么是“晦涩高冷、必须要放在艺术系统内部语境才生效”的
(
装置作品)
。我们简单来说,这种,它是作品吗?还是一种艺术商品?如果是商品的话,它放在一个特定的艺术语境来谈,其实反而是比较多见的。凡是作品,那肯定都跟社会有关系的,尤其是中国当代艺术。中国当代艺术的内部逻辑,实际上跟社会变革是息息相关的。而且我觉得,这种社会性是中国当代艺术,不能说唯一、也是唯二的合法性,否则就没有意义了。因为我们在
(艺术形式)
语言上,实际上
(已经)
做了这么多事情,其实在语言上,我们能做的东西
(已经)
很有限,
(尤其是)
放在国际上来看。希望未来的年轻艺术家能够
轻松一点
做艺术,不像我们现在,还是社会包袱比较重。当然,这个所谓的“晦涩高冷、必须要放在艺术系统内生效”
(的作品)
,你发我的这些图,我也看了,我觉得其实这也不是高冷了,这是体制化的一个表象,就是说,画廊应该做什么样的作品?现在媒体这么泛滥,大家互相学一学,看起来同质化这么严重。看看这么多画廊做的这些装置作品,感觉像一个艺术家做的。
……就不知道在回应什么问题……装置……实际上,虽然我不算一个合格的装置艺术家,但我觉得
在今天来看,
装置艺术多多少少,已经走向它的反面了,它当年所面对的、要解决的那个问题的反面,它已经成为那个问题了。一个是剧场性下行,就是变成观众本位,跟观众互动,讨好观众的一种东西。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其实它变成了一种
(
相当于)
架上
(绘画)
,
一种雕塑,
就是看起来很“美”的
(东西)
。其实我觉得,装置和雕塑,还是有分别的,这种分别在我内心还是挺强烈的,只不过我需要花时间把这个问题整理出来。
我看看还有什么可以聊的。大环境确实是不太能聊,因为每一个个体的情况也不太一样。总的来说……总的来说也不好说,总的来说,说完了你就没法播了。“会是一种消解现实沉重的行为吗?”其实,真的,这几个问题我基本上在这个展览上,没有考虑。对于我来说,在798这个地方,做一个墙上不挂东西的展览,已经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了。
而且现在艺术家职业化这件事情,跟我成长的这个过程
(对比)
,感觉是一个非常突兀的事情。因为我艺术生涯成长的那个阶段,实际上艺术家还是有一个群体面貌的,就是有自我组织,有朋友啊;现在,好像分配到不同的单位里去,然后给这些单位工作了。
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这几年可能有一些比较水的画廊,ta的工作,可能主要是处理一些常规的博览会。可能一年下来要组织的展览形式,可能就是博览会那几面墙。可能大家现在一谈起当代艺术,每个人脑子里面想的那个东西都是不一样的,非常不一样。因为我们留给当代艺术的那个内核的东西,好像在今天来看,消失了。Ta变成了一种谁都可以去描述的东西,
(这)
有好、有不好的地方。你比如说,
现在
有很多年轻人,招上来要在一些商业画廊里工作,就
(让人)
很担心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做展览了。但是当年的画廊空间,是要好好做展览的。那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第二点,你说的这个,我要反思一下,我自己是不是有这种优越感,放在了自己的表达里去。“你觉得你的作品好在哪?”关于作品的价值判断,好与不好,实际上在创作者的角度上来说,想得比较少。我不知道你们这代人是不是想得会多一些,我其实想得比较少,因为有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在描述作品,在去做价值判断的时候,我们在调用一个比较古老的系统。这个也是个问题了。现在很多自媒体、公众号,在给大家讲这种价值判断,但多多少少是一种媒体行为;艺术家在工作的时候,还是要摆脱这些东西的影响。其实无所谓的。当然也不是说完
(全无所谓)
,它是一个程度的问题,不是说绝对的;艺术家就完全有权利来做这种价值判断,或者说艺术家做一切事情都是对的——那当然不是这样。
是不是有点太长了?“你觉得作品好在哪?”……或者换一种说法,就我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我会想,就是这些东西到了撤展的时候,他们大概怎么放,才放在工作室里不占地方。那些木板可以拆下来,然后锯成一条一条的,可以做成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家都不知道的,我内心的一个想法,我总觉得,其实装置它不是一个材料的堆积,它不是把一个材料变成另外一个东西,这种工作。装置实际上临时性很强,就是说,他是迅速组成一个表达,然后这个表达在ta完结的时候,就消失掉了。我觉得,这是装置最厉害的地方,后边的东西都不重要。所以,这算不算是一个优点呢?我觉得……我希望它是个优点。因为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压力很大,但是ta们用装置去表达,用身体去表达,其实可能性还是很大。
(Ta们)
不用投入大量的金钱去竞争,去做一件还比较什么好看的、或者说“完美”的作品,不必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