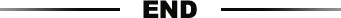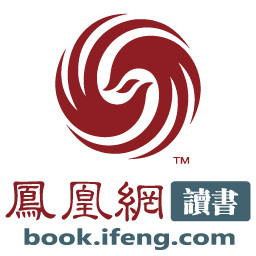"我"不是我,是陈兄
用第一人称写陈兄
是基于传递人物内心以及把控表达边界的考量
更为重要的一点--
他是我唯一不顾虑以代自传书写会致使曲解的人
文章在3次共计144分41秒深度访谈(In-depthInterview)和十年知交基础上写成
文中人名及部分地名使用化名
1
2006-2010
人年轻时花去珍贵的光阴
把最清醒的时日奉献给阅读经典
哪怕只学到皮毛也具有恒久价值
岁月久远,我已日渐淡忘学生(硕博)时代的往事经历。原以为我的一生都将如那时一般丰沛、坚实、满怀豪情,不,堪承这些词语的日子唯属于那时候,已经过去了。
如果说至今我身上仍携有一点聊胜于庸常的理念修为,得益于硕博四年浸润在厦大开阔而敦厚的人文景气里,并且我是用了功的。其中以阅读为甚。零六年秋偶拾周国平著《人与永恒》,即被书中讲述人情感的细腻所震动,神思随之驰骋心灵,捕获激动人心的一个下午。
其后寻来他所有专著及译著,读过始知有哲学,知尼采、叔本华、柏拉图、苏格拉底、黑格尔等哲人,继便一头扎进西方哲学里,阅读他们的原著。那些书籍如道道灿烂而崇敞的荣光,当初是我胆敢攀附,而如今回顾,它们已附着在我的生命之中。
我直到现在还回味罗素与叔本华的智慧,前者明晰且审慎地探究人精神领域和社会整体结构的运作规律,后者清楚如何给人生少惹些麻烦,使风险和痛苦不伤及生活的幸福,因适时中断而潇洒自得。尼采我一直没有读懂,但深奥学说将人累得筋疲力尽,不失为一种锻炼。人年轻时花去珍贵的光阴,把最清醒的时日奉献给阅读经典,哪怕只学到皮毛也具有恒久价值。《人与永恒》一书我送给了慧月,在同年我们初次见面时,虽她刚才成年,识见尚寥,我已灵敏察觉与她的志同意合。
上述大师的思想完全不朽,古典作品乃是人类精华的记载。恰巧那年李岚清赴厦讲论古典音乐,我正沉浸在古典之美当中,信奉大千世界诸多美好而人生短暂不能尽享,若要尽力,不如汲古,因其已经过了时间的检验,毋需再试错。故此我又慢慢进入古典音乐世界,聆听、感受、与之共鸣。
生活费很少,到底拨出两百元钱买了一个漫步者音箱,它陪伴我直至毕业。是时我还替一位老教授顾看家宅,他家里有三样宝贝:两只猫、一书架中外哲学著作以及一台自国外带回的价值不菲的收音机。收音机里留的光盘即是肖邦夜曲,整个暑假我沉醉其中,犹如与一位极其优雅、柔润、多情且富藏内涵的年轻女子共处,心中滋生疼惜,情不自禁。
而莫扎特的旋律是三十岁的女人,高贵、典雅、爽朗又不失风趣;贝多芬则是四十来岁的企业家,拼搏进取、深刻勇猛,是冲锋陷阵的人,充满了理念理想,与事业的不顺和命运的坎坷做激烈而有韧性的斗争;至于施特劳斯的圆舞曲乃是足够欢畅的,像篝火里起舞的那一群人,永远在跳舞、跳舞、跳舞,赋闲的宫廷式荒诞,但是使永夜像似永昼……古典音乐是向着人类的心魂说话。
嘉仪是我的中国古典乐。她当时已在古风唱圈做歌手,我们相识于校内网,很快走到一起,我与护士姐姐也就这样散了。护士姐姐出现在我有强烈生理需求和需要异性伴侣的时候,一旦爱情从别处降临,我是必然成为此处一个负心的人。嘉仪是我的爱情,爱情是毫无逻辑的全副身心的吸引,是两人都立即变作半人与对方合而为一。
我们身处异地,以整夜复整夜的电话互诉钟情、见识与琐事,分享的魔力在于令有限生活奇迹般地延展成无限。我且想要占有她的全部,想要彼此在无限之中完全融合。第一次做爱前,我发誓将爱她一辈子,两人在仪式里热泪盈眶,尽管并没有做成,片刻后又紧紧拥抱,同时恨不能把心掏出来交予对方。
爱与性的认真纯粹皆是赤子之心。她在我眼里是完美的人,聪明漂亮、有灵性、能作曲,她读的书我喜欢,她的情绪化我也喜欢。却爱情与其他美好事物一样,总是盛极而衰,这些特质后来许多转化为我所厌腻,但撇开相处兼容问题独立看待它们,始终仍都是好的。
相爱的人将爱情的衰落看得一清二楚,青春又是与其强求苟延不如终结在炽盛时,好合好散的年纪。我们遂约定分手,并且终于做到。毫无保留的深爱在分离时一定艰难,时常想念,非常孤独,只得硬挺,没有别的办法。回想这场爱情,有始有终,算得以圆满。感情事之好坏,之欣慰遗憾,是从不以分合计的。
我也并未自此失尽爱人力气,董姐每年回厦时带我吃饭,我仍向往她的动人。在去厦大硕士生面试的火车上与她认识,漫谈家事与成长足迹,她从来身在优渥环境里,怕是因此怜惜有人辛苦又努力,那些年逢在厦门就会招待我吃饭,海味山珍管饱。
她彼时已三十岁余,言谈举止合乎分寸又散发魅力,我不知女人的美丽还有此种向度,总是看呆了,而她对我的小心思当然都清楚,不作声,有时只忽然笑了。那笑容也好看。
一零年我博士毕业,去往宜芗市宏林药业做研发。离厦没有太多感伤,经济上匮乏数年,满心都是对进入企业工作的憧憬,想及即将领取的一月一万薪金,就像终于盼到领取立世的希望。
2
2010-2014
我在宜芗不大高兴的原因
还在周围多是无味的世景人物
令我觉得无聊
中国药企的研发系统不像国外分技术与管理两线运作,技术人员不进管理层难以有成长及价值感,我因此开始学习管理知识,每天用最快的速度料理完当日工作,余时阅读大量管理学资料。当时确实也对管理有兴趣,治人重在收心,收心意为使人自身体验增值,彼此愿意合作。
不到一年,我几读遍管理类有影响力的书籍,颇为疲惫,但是当时有激情,而且认为如此度过时间方是可满意的,不然会觉不安。这是社会与自我的双重驱动,走出校门适应新规新矩之法,虽则总不免有些焦躁。
我在宜芗不大高兴的原因,还在周围多是无味的世景人物,令我觉得无聊。小城本地人居多,眼界心胸都相对窄隘,但我择业是时一则迫于经济压力不敢妄去大城市,考量如需落定当地至少房价可承,二则宏林确是行业翘楚,于是虽然感到无聊,一切同事少有私交来往,仍可以扛下来,每日下班后便独自在宿舍看书,周末亦常这样。
但我很难把周末从头到尾地利用好,因平日一人食饭读书,休息日仍是一人,周六尚好,周日就着实体会到了孤寂。这种孤寂从自己发生的,不大有药可救,心里便愈惶惧躁动,是故那段时期我常去嫖妓,寻一个出口罢。一般敲小背,也敲大背。
我自省此事多不在身体上的刺激满足,而是男人内心深处有性事需女人共同完成这种预设,如若自行解决,则解决之后也少不了会空虚窝火。且人永远对陌生新鲜的身体有兴趣,这是本性,我由本性的餍足中减少许多苦闷。
工作两年左右,我想安定下来,有明确的结婚意愿。姑且尽力托人介绍,因涉及婚姻我是理性居多,认为须有一定基数才能遇到合适的人,而且我不是唯感情者,当我意识到人可以不与所爱之人结婚,也一并意识到与不爱之人结婚亦无妨。
伴侣只要整体能够入眼,去相处去培养,所得一样是感情。是故我不苛求婚姻要以极浪漫的爱情开始,它终归是能够生活在一起即好。带着此种理性设想,加之一点真正走进婚姻的冲动,一三年初,我与妻结了婚。
那时我已做到公司管理层,目标的实现比预期稍快,然而应酬上的消耗有些厉害,社会是这样,往往不能避免,又且人际里多有勾心斗角,内心不愿,表面不得不如此,要费力应付。始觉人各有苦乐,主管、经理、总监、副总,抑或院士、院长、教授、讲师,不见得谁过得更快乐,上天总是讲究平衡感。我知我自然要脱身当下位置,但什么时候,尚无预期。
适逢此时,公司成立了企业大学,我有机缘讲课,接触到培训师的行当。课程反响甚佳,且讲课使我感到从容自在,我便渐渐滋长成为独立培训师之念。人在一个圈子里被捧至高点,眼望见外面更为广阔的天地,自会期望那里有处更高的位置在等候自己。
但我仍熬在原位,心想再半年一年,也还做得到--为己,离职只有一个经济问题;为人,宜芗是妻的故乡,她不肯轻易隔别。
之后还是耐不住。徘徊再三,我觉得我的生活应该不是在宜芗这样一个小城市,做着一份逐渐稳定已无甚挑战的工作,拿着一笔比下有余比上不足的收入,认可顺受相对薄弱的教育医疗等社会资源,如此至老了。复频繁想起在厦大时的生活,那里人事都曾教导我人生整体可以有非常好的状态,经历体验不息精彩。
三十二岁仍是敢拼搏的时候,有足够的冲劲挑战未来,也还认为人生选择的主动权是紧紧握在自己手里的,并且深信男人的安全感并非来自家庭,而是他的事业。我遂递交了辞呈,心里升起一种果断放弃拥有以追求未酬壮志的英雄气概。
3
2014-2016
但我已决定不再彷徨
熟思自身无论天赋或运气都如常人
生活所给予的掣肘也如常人
说起培训师的事,那时确是光明。辞职以后我先到另家药业担任企业大学校长作为过渡,即培训课程的实际买家。我不是胆怯,只为想规避些曲折麻烦,籍此摸清买家诉求,并且建立一点人脉关系,为将来自己去讲课铺一段路。
上海有顶尖的培训师成长项目,排出日程专去系统学习了授课、写课,尤其是包装与推广的技巧,因我深知业内市场竞争激烈,不懂或不屑于包装推广的人是难以占据一席位置的。
次年,也即一五年,我从企业大学跳到北京一家专门的培训机构做培训师,往前又挪一步,由纯粹的采购方走到了中介方,委托其培养以及将我推送到市场里。
真正进入圈子,对业态有务实且横纵向都增拓的了解后,行业往往没有表象那么优好,看起来是渐渐坏下去。其实也不是新添的坏,是外层涂饰的漆皮剥落已尽,于是原相就显现出来。
培训师一行没有渐进过程,要么成就名师,时间自由,薪酬很高;要么不成,课程很少,迷途里奔波。而绝大部分独立培训师依然是在谋生,饱受行业中痛苦的地方,为这份工作能否持续地进行和发展下去而犯愁,一百人中只有一个人能欢度兴趣寓于事业的生活。
我在北京,公司迟迟不敢把我推到客户面前,使我觉察原想成为这一领域弄潮儿的自己很有可能变成一颗弃子,随时间的推移,梦想由我看来,希望已不多。
去年六月,我从北京回家,开始着手写书事宜。并非真为培训行业引入新血,纯是出于迎合市场的商业动机,预想凭此证明自己实力,告诉买家我不单可以讲课,还具备将经验总结成集的才能。期间一直推送课程进市场,接单不甚稳定,终于夜半梦里被手上没有足够的收入吓醒,坐起身感到满屋子的风雨飘摇。
我静下来,掰指头算--计从研发岗位出来已近一年半,如果到两年我再回去,博士学位与科研经验恐都将难再被认可,因为科研是与时俱进的,离开太久的人把不准时代脉搏,有博士及管理人员的履历却又研发与管理双不如人,会使公司根本无从安顿。
不知不觉间,我已落险境至快要不复专于一业,一事无成了,不由又出一身的冷汗,慎思事业改变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大的,有时侯人先前选择了一个专业,也许注定就要在这个专业上稳稳当当地走下去,而出走创业也好,变更职业轨道也好,它所带来的风险和代价常常超出想象。天将拂晓,我意识到于大部分人而言,人生实际上不是有特别多的选择。
一日车在路上刮擦,对方司机看起来是四十上下的男人,横肉堆赘脸上,一笑又全起了褶子。待处理时见他的身份证,吓住,他竟与我同年出生。忙不迭地复望眼前同龄人,不免疑心自己如正照镜,也有此般暮气。恍惚须臾,醒悟原来不经意间,自身最有力量的年华已经过去了。
又想及目下,妻五万的私房钱移出贴补家用,我毕竟是有家之人,到现在还是乱闯,倘闯入的是深渊,自己有自己负责,领着别人又怎么行?妻与双方父母需依恃我,房贷逐月应还,这些都是明确的责任,必得完成。
于是如何讲不以别人为中心?因为个人有了家,个人的中心就未必是在自己了,经常别人倒是他的中心,虽说为人,其实也是为己。回顾从前,青春时是没有责任感可言的,要到中年,身上附加一块又一块担子,且不愿意垮在原地,没有一点进展人就老了,始要产生责任心出来,扛起担子往前走。
此时有咨询项目找到我,邀我介入。收益不错,但我已决定不再彷徨,熟思自身无论天赋或运气都如常人,生活所给予的掣肘也如常人,虽仍想在培训师的路途继续探脚,目前却不能。且我创立一番事业的激情亦真有些淡了,感到激情并非供给人一味追随的永动力,而是需在不断体验到成就与价值的情形下彼此相互支付的一种推进。
我开始在宜芗找工作,主要是投简历给当地高校。有天晚上和妻散步,走在街巷里观察着路上形形色色的人们,很清楚地看到这就是真实的生活,没有那么多幸福。时刻的幸福存在于孩童时代和学生时代,存在于恋爱的时光。出了校园,苦痛也要和快乐一样与人生连带,无从避躲的。
社会就是如此,我从前任性,到了这个年纪的确该收一收心。这个年纪其实也不太容易为生活的小事开心了,不停地感受微细的乐子乃是年轻人的专利。但到了此时,但凡一地可以落脚容身,就可以安家。
那晚与妻散完步回去,楼下望见自家窗口亮着的灯,诚觉窗内那方小世界就与别处都不一样。我始知道家庭虽然不如事业给人的安全感,但是它会给你很强的责任感,让你持重地对待事业这件事情。
原想好留在本地高校教书,不料获悉学科尚未建成,不具机缘,终是去了江城一家药企做研发。命运是这样安排,决定总是由天地人共同做的。这份工作离家却也不远,薪金足够,研发亦是我可控的范围。
两年间晃荡一遭,跳出又回到研发老路,抛弃又需寻稳定安足,人生莫不像钟摆,趋近一头又被另一头吸引,往回走。摇摇晃晃地,何时磨砺够了,就慢下来,可最终究竟停在何处,却都不好说。
4
2016-2017
人要努力维持自己的身体健康
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行
要保住工作,要应对琐细
留给自己的时间并不很多
我到江城以来,已半年余。现下这家公司的研发水平比宏林薄弱,需我带去许多经验并手把手地培养人才,工作颇忙碌,每日加班。虽同是科研,好在此处技术线与管理线划分清晰,我将盼望在研究系统内有所作为,顾好自己与团队的研究水准即可。
从前短暂享受过做领导的乐趣,现在于不断分析与解决纯科研问题之中感到逻辑能力的释放,虽不至于激奋,但是会有很多坚持,逐渐地做一点,愈益体味出些许锲而不舍的意思来。这里薪酬也满意,能令小家康适,父母日后如需看医用钱也不必害怕,且有富余为家人买份重疾保险,并积攒一些成长与休闲基金。
妻在宜芗还是不愿出来,我便周末回去。小别胜新婚,自我到外做事,常想念她,两人感情很好。以前不愿陪她看电视逛街,现在因为觉得异地对她有亏疚,这些也愿意去做了,包括周末时揽下所有家务活,她在一旁夸奖,我内心亦有喜悦。周期性地离别重逢使人没有机会做饭渣子,得失有时便是这样不可算计。
婚姻当然仍有很多缺陷,不会完美。两人相处一定存在彼此不满意或不适应的地方,但是又必须得花时间精力去培育和退让,因为当初选择了这份感情。婚姻乃一直是不进则退的关系,如果不肯培养也不肯让步,它就会反噬,出现许多矛盾扰乱各自心境,甚至讨取高昂代价。总之不能以完美来要求它,那是不近人情的,过于理想主义。
这些年我也不是对婚姻从未曾有理想化的期待,如果说让我想过与之结婚会有琴瑟在御般的人生,一个是嘉仪,一个是慧月,唯此二人。但即便幸运如彼,人生亦不会美好若想象,因人是没有那么契合的人,婚姻本身的属性也不是那个样子。
不管与谁携手,两个人一起走下去了,终究都会走往一处平和平淡的位置,到底可谓殊途同归。妻近来许是无所忧虑,尽情释放她的天真,宠我似成了溺爱,使我独在江城常心想--一个女人愿意这么去爱一个男人,且她由此自得许多幸福,是很可爱的。
三十出头时,我在感情上还有些躁动,而今则越来越淡泊,爱与性都无奢欲。也许是宣泄与挥洒纷纷转移到工作中去,也许是不再匮乏。风花雪月之味我已尝过,再尝不过是回味,毕竟不如初次,而且闹出动静来不免伤掉家里和气;肉体的寻欢倒直是短平快地,有时调剂无不可以,但我亦懒去,网上有一种声优,我以之配合解决就足够了。男人在长期与同一个女人做爱导致性冷淡的状态下,总得要想点法子保持余生性欲。
偶尔记挂的都是老的感情。上次见董姐在四年前了,我春节回家路过北京,坐车到她小区附近叫她出来吃饭。她那天有点憔悴,她当然也自知,低头间忽然抹了一点口红,抬头时立马又光彩起来。她笑着问我"是不是很有效果?"我微有心酸,想到从前她是不需要口红的。
当我已人到中年,便明白中年男人在现实里沉浮成熟,早不再需要年龄大的女人给予淡然的安全感,而是转为需要年轻小女孩的简单笃定来澄清与激励自己。但太多年了,人的分量就不太会因不需而减轻,她仍独特在我的记忆里,许再几年过去了,又坐下来吃一顿饭。
慧月始终是一杯淡茶,一本纸书,好得恰如其分。也许以后,叫我牵念的友人亦只得她倆,因为前面十年青春留下的故人也只得她倆。
我今三十五岁,一个三十五岁的男人已经一只脚踏入世事。这个年纪经历过一些事情,譬如辞职、创业、理想、现实、失落、挫折、婚姻、矛盾、支持和爱,是时候放下青春的幻想,稍为安稳地敷衍下去。
数年前骑着单车飞驰在白城环岛路上,哼着小曲,不知道为什么那样愉快。青年人离生活还是远的,故而美丽。生活过了青春以后很多时候并不美好,身心与周遭都有持续的丧失,不应再以美好作为标准。倘若还以美好要求,则就陷入执迷。
我曾对生活和未来有很高期许,在厦大读书甚至刚工作的几年里,都认为命运全靠自我把控,能者多劳多得,人凭借天赋、平台与勤力可有一番作为,并且人生总体来说是愉悦向上的。这些年生活虽然没有狠狠地给我一记耳光,它也已经向我显示了它真实的样子,意即平俗前行在老生常谈里乃是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的生命之流。
人要努力维持自己的身体健康,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行,要保住工作,要应对琐细。有时想做一件事,看见岳父母忙着做饭,就少不得放下去帮忙;晚上到家已八九点钟,想到第二日又需早起上班,便不能专心读得进几页书。我的生命不动声色地割碎在我所怀拥和牵连的人事物里,留给自己的时间并不很多。
我也曾觉得时间是有价值属性的,应该有意义地度过它,去产生一波复一波的生命高潮。但现今我在仅有的私人时光里,周中晚上与家人视频完随便看两集电视剧,或者用虾米的随机播放听几首歌,周末在往返家中的大巴上看看《歌手》和《奇葩说》,吃着事先准备好的桔子、瓜子与薯片,时间就这样过去。
以前总认为这是在消磨,是"kill time",然而时间又许本来就是可消磨的,谁说得准?我前三十五年还从未像现在这样,有闲让薯片在嘴里缓缓融化,认真体验过吃薯片的乐趣。生活或不是为了意义,也不是为了快乐而存在,它有这些成分,但是也有其他的固有的属性。
而一旦人知道了日子也具苦辛,人又有时是极容易被安慰的,如我想此后只要能以工作养家糊口,不受意外的气,又有一丁点自己余暇,就可以算是幸福了。这似乎是退步,倒是进步也难说,事实的两面都有光劭。
回顾前面十年漫漫,最大收获是今时可以接受当下的状态,不能说乐在其中,但是能够容纳日子是这般过法。不去与之斗争,不去内耗煎熬,不过度期待与反抗,反倒可给自己腾出一点心力与时间,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我仍然有时思考,有时自省,但都已随缘,想不透彻也无妨。
我渐可安信思维的敏锐度与深度并不会因生活方式的变改而流失,生活也并非离开思索就无从体验。恰恰相反,人在生活之中体验的所得才是最深切的,是自己书写的哲学。我亦仍然往返于失望与盼望之间,只是都不张扬,波澜很小。
菲茨杰拉德在四十岁时写的《小心轻放》里说:"在一个成人的内心,那种希求气质超群的渴望,那种'不断奋斗'的渴望,最终只会让忧郁雪上加霜。"我也从渴望与忧郁中走来,那是年龄、经历、环境等等缘故,不足为奇。在此举步维艰的历程里,我不断变迁着对身处的世界与自己人生的观念。
与其说变迁,不如说是化繁为简的一种修正,唯有那些足够坚实的力量留了下来,而且比青年时更为深刻。人在岁月里变成新的人,其实不是全新,是生命河流中新的段落,将来还会走到下一个段落里,直至离开,直至最终回到汪洋大海。
前日,妻确认怀孕,我未有电视剧里演得那种兴奋,只觉得终于给父母有所交代,也不需再应时备孕,有些如释重任。孩子没来临时,我想过它最好聪慧,但转念聪慧与幸福与运气是没有什么必然关系的,公司里新入职的数名硕士生每日配置药品昼夜勤劳,过得很辛苦,而我妻许正躺在沙发上不知看着什么连续剧,闲情很多。人生这回事,得失不好说,命运也不全可控。我今唯愿它健康就好。我也知道,在成为一个父亲的新角色里,我将给我的孩子以我的爱。
责编:笑笑
本文版权归属有故事的人,转载请与后台联系
阅读更多故事,请关注有故事的人,ID:ifeng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