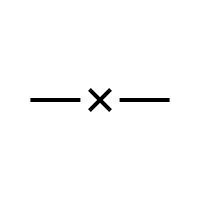被忽略和被歧视的历史
「当人们问我的背景时,我总会花很长时间来解释:我的母亲是俄罗斯人,我的父亲是加纳人,我出生在保加利亚。」
摄影师Liz Johnson Artur说。
1960年代,苏联为了在冷战中从非洲大陆争取更多的支持,并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开始大量接纳非洲留学生来苏联,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当然,这也是为非洲的局部代理人战争储备软实力)。
Liz Johnson 的父亲就是其中一员,他的父亲从加纳来到了保加利亚,学习生物化学。不过很不凑巧,因为一起突发事件(加纳留学生跟当地警察发生了冲突),所有的加纳留学生都被强制遣返回国。
1964年,父亲被遣返后几个月,
Liz Johnson 出生,开始了没有父亲的成长历程。
Liz Johnson 和母亲在德国、保加利亚度过了自己的童年,随后在1990年迁居英国。

Liz Johnson 的父亲没有机会来到欧洲,他回国后就一直待在加纳。直到2010年,Liz Johnson去非洲寻找,才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父亲,而这时她已经46岁了。
那次非洲之行,改变了
Liz Johnson 的生活,也激励她开启了一条新的摄影生涯。她决心去记录下所有散落在俄罗斯广阔土地上的非洲裔或者加勒比裔俄罗斯人,找到那些所有缺失了父亲的后代。
那些跟母亲生活在一起的单亲孩子们,以及那些被父母抛弃,在孤儿院长大的黑皮肤孩子们,便是她所要追寻的对象。
在他们的内心,黑人身份和俄国身份一样,是个人存在、个人意识的归宿。
所有这些被归类为「非洲裔俄罗斯人/
Afro-Russian
」的群体,从没有像普希金祖先一样,能被沙皇所赏识,并有机会从优秀的黑奴变为国家的中上层。
他们生活在一个排斥和不理解黑人的环境里,也很少跟其他黑人接触,所以完全没有机会像美国和英国的黑人一样,形成一个强大的族群,进而促成一种黑人亚文化的出现。
每个黑人混血下一代的个体经历,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的共同身份中,都有一种
与历史和现实对抗的元素——在一个有很强排外性的社会里,不断向俄罗斯人证明自己是俄罗斯人,也不断抵抗社会歧视的挤压。
在Liz
Johnson的眼里,俄罗斯是这些二代混血人群的家园,他们不可能隐藏在社会里,等着忽视和被歧视。她希望这些记录,能够让历史造就的一代人,找到自己的身份和归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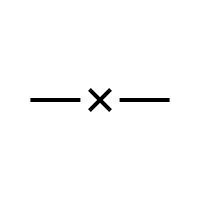

Marie-Therese/玛丽·特蕾莎
我出生在圣彼得堡,我的父母都为联合国工作。我的母亲来自一个俄国家庭,父亲有法国和瓜德罗普(法国在加勒比的一个殖民地小岛)血统。我母亲的家庭在十月革命后离开了俄罗斯。
因为我父母工作的缘故,我小时候在非洲国家待了有十年:刚果、加蓬、埃塞俄比亚。我中学快毕业的时候搬回了法国,之后我又读了一个法学学位。当时摆在我面前有两个选择:去孟加拉国,还是俄罗斯。我选择了俄罗斯,于是我在1995年的时候来到了俄罗斯。
最开始的时候,我在做法律顾问的工作,后来我有读了一个经济学位,所以我就开始在大学里教授经济学。
我和我的11只猫生活在一个小一居里面。生活马马虎虎,但是我喜欢这里。我觉得在这里会有比法国更多的就业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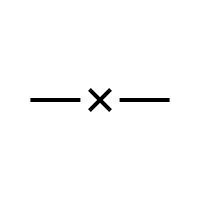

Gera/杰拉
1961年我出生在莫斯科。
我的父亲曾经参加过古巴革命,后来他来到莫斯科学习哲学。他曾经和切·格瓦拉、菲德尔·卡斯特罗并肩作战。
当我一岁的时候,他回到南美继续参加游击战,和格瓦拉一起战斗在玻利维亚。
我一生只见过他那么一次。


我的母亲、我的弟弟还有我住在一个狭小的筒子楼里面。当我5岁的时候,我的妈妈生了重病,她在医院没法照看我们,于是我们就被送去了孤儿院。我和弟弟在孤儿院里面住了3年。等到了上学的年纪,我妈妈才把我们接回了家。
我的童年挺心酸的,但我对于拥有黑人血统还挺自豪的。从小到大,我都是关注的「焦点」,当然这种聚焦在俄罗斯并不是意见好事儿。
俄罗斯是一个非常沙文主义的国家,身为一个黑人在这里的确不好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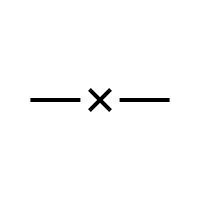

Amina/阿米娜
我出生在莫斯科。我的母亲来自俄罗斯,不过她来自西伯利亚,图瓦共和国。我的父亲是尼日利亚人,他们在莫斯科大学遇见的。
在我快5岁的时候,我的父亲离开了俄罗斯,因为一些原因,他再也没有回来。
当我完成了我的学业,我决定离开莫斯科。我上学的地方,同学身份复杂,他们来自全球各地。我在那里感觉到自在和放松。在莫斯科市中心的时候也不错。
但是我真的很不喜欢这个城市的郊区,那里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氛围。我在市中心还不会担心安全问题,但一离开市中心,我就觉得非常不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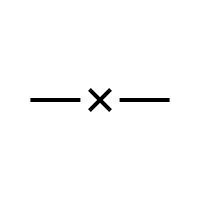

Vlada/弗拉达
我在莫斯科住了7年。大多数时间,我觉得这里是个不错的地方,但是我还会选择去到别的地方生活。


我旅行去过巴西和西班牙,那里的人们非常不同,更加的友善和开放。莫斯科是个美丽的城市,但这里的生活有时候会变得困难重重,到处都有麻烦事儿。
陌生人会不打招呼就来摸你的头发,这是让我最受不了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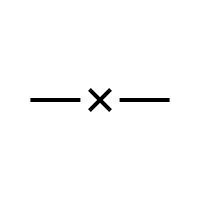

Elena and Peter/艾莲娜和彼得
我的名字是艾莲娜,今年55岁。我是彼得的母亲。我们住在莫斯科郊区。
我在尼日利亚大使馆当一名厨师,彼得的父亲是一名外交官。我一直都知道,他的父亲在尼日利亚还有一个家庭。
每次他回国的时候,我都会陷入各种问题。比如发现我们家的信箱里有寄来的色*情明信片。在彼得还小的时候,我推着婴儿车上街,人们会探头来看我婴儿车里的孩子是什么颜色的。一些朋友和邻居,也因为我生了个黑人小孩而跟我反目了。


我送彼得去托儿所的时候,别的家长会向托儿所抱怨,为何接收一个黑人小孩。托儿所的工作人员心肠不错,他们很支持彼得。但是其他小孩就不一样了,他们会说,「别碰他,碰他你就会变脏。」现在情况好些了,因为他长大了,能够替自己出头了。
2年前,我赢得了去尼日利亚的机票,我就带着彼得,回了一趟他父亲的祖国。在那里,和他的非洲妻子、非洲孩子住在一起。还真挺不错的。在他家,我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我现在还能记得当时的热情,那是段不错的旅行经历。对于彼得来说,能够见到他的兄弟姐妹们,也是非常不错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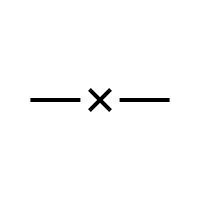

George/乔治
我在10年前来到俄罗斯学习工程技术,但是我对武术和搏击的热爱让我彻底转行了。我到圣彼得堡之后和一个俄罗斯女人生了个儿子,所以我必须得去找工作了。
我在俄罗斯朋友的帮助下开了一个搏击Studio,教人们武术和格斗。俄罗斯朋友们对我真的非常不错,如果是在刚果,这件事绝对不可能发生。
2004年的时候,圣彼得堡突然出现了一堆光头党的袭击活动。有一个非洲学生因此而丧命,我们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
我在集会上讲话,然后国家安全部门FSB的人就把我拘留了两天,来回盘问我的行为和动机。

但是这一切都不会让我觉得绝望:我知道要想改变人们的态度需要经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我甚至想到过要加入安全部门,成为他们的一员。我通过了所有的考验、测试,但最后他们还是没有录取我。不过我是百折不挠的,我换了一个部门继续申请,于是现在,我以志愿者的身份为安全部门工作。

我想要努力去报答我在俄罗斯获得的一切。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努力去改变俄罗斯人对待我,和对台黑人同胞的态度。这是最好的改变现实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