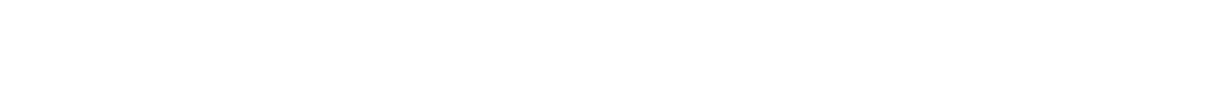 SANGHATALKS EP286
SANGHATALKS EP286

前段时间看到一段话:
一群发好心出家的年轻人,在这充满僧色,却缺乏法味的佛教大环境里,其内心的不安与飘荡是可想而知的。
这段话不知是说者自己内心的体现还是在评论所见。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莫名一动,感觉似有一道闪电击进心中,有同感更有有痛感。之所以痛是这话里所描述的“年轻人”似乎就是自己;之所以有同感,因为这不仅有自己影子,也是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感知到的外境。每个发好心出家的年轻人,心中都是有极豪迈的气势,或成佛做祖,或弘宗演教,或挽法幢于欲颓。当年玄奘法师被问及为何出家,时年少的大师答道:“远绍如来,近广遗法。”大师的愿力确宏大,每一个发好心出家的年轻人也均是如此。大师之愿伟哉,每一个发好心出家的年轻人亦伟哉!

当年玄奘大师所处的环境如何呢?是国力鼎盛的唐朝,是佛教地位相对较高的王朝,是修学风气大盛的时代,但同时也是经典不全,义理争端、各成门户,不乏营苟的时代。当作为青年僧的玄奘大师看到教内由于对义理的理解不一而各自立山头的时候,摄论、地论两家关于法相之说争论如潮的时候,他是怎么看待这些现象呢?玄奘大师并没有因为前辈大德们的争论而对佛法产生怀疑。大师对佛法的信心从未动摇,他想到的是西行求法,是去动身解决这些问题。
求法面临的是何等环境呢?一没钱,二没人,三没势,并且国家限制他的出境。大师拥有的只有一颗想要去求法的心,就只有一个单薄瘦削的肩膀。此等情况放到如今,我们绝大多数人就会打退堂鼓,甚至根本就不会生起要去西行求法的心,更别谈遇到那些难以解决的困难,以及后来遇到的重重磨难了。义净三藏法师曾写过一首诗求法诗:
晋宋齐梁唐代间,高僧求法离长安。
去人成百归无十,后者安知前者难。
远路碧天唯冷结,砂河遮日力疲殚。
后贤如未谙斯旨,往往将经容易看。
求法的艰辛是如今的我们难以想象的,就好像如今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难以想象战争时期人们的生活状态。就算我们看到那些描写战争的文字,观看战争片,我们看到、感受到的也仅仅只是表面,跟那些切身经历过的人的感受难能是一样的。

回观如今的我们,是什么导致了我们的不安和飘荡?是时代的大环境吗?是。是佛教的小环境吗?是。是其他的某些大大小小的外境吗?是,都是!这就像玄奘大师所处唐朝的佛教一样,有诸多的问题。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会面临的问题,但每个时代也都有每个时代的优越性。没有最好的时代,也没有最坏的时代。无论何种时代,也都是做好的时代也都是最坏的时代。玄奘法师的时代,我们如今的时代。我相信,如今我们每个人遇到的境遇再不好,困难再多,也难以和玄奘大师当年只身西行求法所遇的障难相比。我们没有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做事,我们没有一个人两手空空去完成一项巨艰到无法完成的任务。
面临同样一种环境,有的人把自己的不快都推给环境,有的人找寻自己的原因。有的人找到问题解决问题,有的人只是抱怨生不逢时。其实,所有的生不逢时和伯乐难遇都是对自己先天不足和后天不努力的安慰和借口。每个佛弟子都有自己最初的无上发心,但最终结果的不同根本就在于对最初行愿力的坚持。对行愿的坚持和坚定,需要对自己充满信心,需要对佛法充满信心,唯有有信心的人才能持续前进。
有时自己的不安和飘荡就是看到别人的不安和飘荡时,动摇了自己的信心。外在的腐朽侵蚀了自己内心的纯净,逐渐把自己变成了自己之前不屑为伍的人,逐渐和那个曾令自己厌恶的腐朽的环境融为一体。但心内仅存的一点微弱光明又时而提醒着自己的与众不同,此时心内何止是不安和飘荡,是恐惧和追悔。如果那一点微弱的光明也被蒙上灰尘,那剩下的就只有得过且过,只有麻木,只有悲哀。

也许热血并不是一个修行人该有的气质,但是
“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 我若向火汤,火汤自枯竭”
的大无畏的勇敢和自信,一定会是这个充斥着萎靡颓废、精致利己环境里的一剂强心剂。《普贤行愿品》中所言:
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行愿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语意业,无有疲厌。
这才是大乘佛弟子的气质,这才是每一个有担当有悲愿的佛弟子该有的态度。
这个时代也许充满僧色却缺乏法味,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些而丧失自己的修道之心,就好像我们不能因为有提婆达多和六群比丘的存在而舍弃对佛陀的虔敬,对僧宝的皈依,对佛法的修持。
无论何时,法恒不变。法在,一切都在!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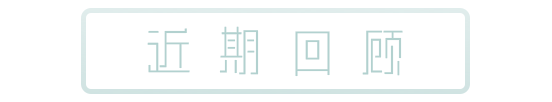
当你遇到一颗裸奔的粽子……
胡扯之无处安放的荷尔蒙
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Road
一条狗对快乐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