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曾博
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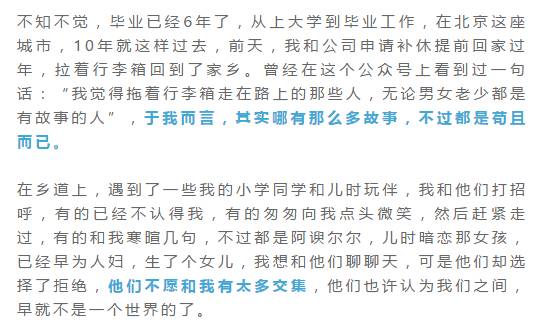
我拉开尘封的抽屉,拿出小学的毕业照,细认每一个同学的名字,回忆之前在这个村子发生的事,后来,我震惊地发现,一张63个学生的班级大合照,最终考上大学的,只有我一个,最终逃出这座山束缚的也不过寥寥几人。
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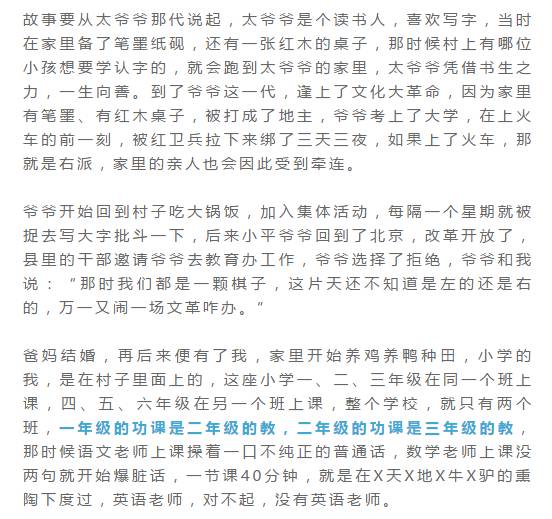
那时,我还分不清什么叫公办老师和代课老师,后来才知道,整座学校,只有一名公办老师,那就是校长,校长还是隔壁村的校长,还是隔壁的隔壁村的校长。
我放学一回到家,爷爷就拿着棍子站在我背后,我一偷懒他就打我,每逢周末,爷爷就拿出被老鼠咬过的绿皮本子,教我认古文,我说,爷爷,考试不考这个,学这个上不了初中。爷爷唧唧地说:“怎么会,我们以前都是看这个的呀。”后来,爷爷把他的自行车卖了,到县上的书店给我买了一套教辅书。我一考试不及格,哭的不是我,是爷爷。
后来,到镇上读了初中,教学环境好了很多,老师大多都是师范职校出来的,那时候给我们小学上初中的名额就只有7个,我和其他6个玩伴就一起到了镇上读书,而剩下的,大多数都回去帮家里务农活,帮忙收割稻子。然后,我考到了县上读高中,最后,到北京上大学,这就是我的读书生涯。

03
还记得考上大学的那会,爸爸在村子的一大块空地上,请了全村的人吃了顿饭,有很多乡亲,还有我的小学同学都来参加,投来羡慕的目光,村长让我在北京好好混,将来出息了不要忘了大家,如果可以的话,把几个小学同学带出这里。
后来才明白,我的小学同学们、我的儿时玩伴们,其实并不是他们不聪明,而是他们没机会。我比他们,只是多了一条棍子。
04
我以为到了北京读大学,就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刚上大学那会,老师问我们,为什么想要报考这间学校(我的学校不是清华、也不是北大),我的同学们有过半的回答都是“高考失手了,落榜才来的这所学校”,他们大多有北京户口,招生的分数也比我们低将近100分,我的回答却是:我花了二十年的时间,用尽所有力气,才来的这所学校。
当他们在讨论香港、澳门哪里买东西便宜,澳大利亚还是法国好玩的时候,我却连天安门和万里长城都没去过。来到北京,我的梦想和《中国合伙人》里的成东青一样——去天安门。
毕业一年,我住在六环的一间十平方米的出租屋内,这里交通还算便利,到上班的地方只需要30分钟,可是这已经过去6年,一分一秒也没有缩短,30分钟的距离,恐怕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突破。经过四年的高等教育熏陶,我的眼界、见识、品味已经和北京青年无异,从被虐的小白实习生,到IT部门的小组长,然后跳个槽到另一个公司做程序部门主管,我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一双擦着发亮的皮鞋,手里拿着一台苹果笔记本,然后刷了公交卡——挤上了一台公交车。
后来才知道,北上广深不是你想改变就能改变的,你当了主管,很多富二代、官二代早就在北京呆腻了,然后出国转战新加坡、伦敦、加拿大。你努力的目标,可能就是很多人的起点。
但是,我并不是说这些富二代、官二代不好,我在北京读书的一些同学们其实很善良,有的成为了我十年的知己之交,可是有的东西你就无法去解释,他们的生长环境、教学资源,能让他们身上的每一种特质都有舞台承载,从而熠熠发光,你要知道,智商、情商和勤奋,这东西是可以先天或者后天“遗传”的。他们的眼界、见地、能力,可能都是我们,穷其一生都无法企及的东西。
草根逆袭有时候回想,或者是一春梦,只能认命,可是认命吧,又不甘心。我用了6年的时间,用每天啃面包的意志力,在六环交了一套房的首付,勉强说服了女朋友她爸妈把女儿嫁给我,这些原本是天然选择、你情我愿的事情都开始变得触不可及。下一步,从六环到三环,可能要几代人耗费上百年的努力。
05
曾经有不下百次念头,放下这一切,回到那大山,开个小店,这该死的阶层流动,我不干了,爱谁谁干,可是一想到下一代,就不想让他们再重复这样的命运,只能是硬着头皮上。
沙漠中沙粒无数,最幸运的沙子,也只是偶尔能够浮到表面上来,享受一次阳光、享受一次春风而已,还有很粒沙子,可能一辈子没有见过任何阳光,一直埋没在下面。每个人都像沙漠里的一粒沙子,只是我比较幸运一点,多了一条棍子而已。
很多东西,其实一早就想清楚了,如果你改变不了世界,那很简单,被世界改变就对了。阶层固化四个字已经让无数人落泪,只能嚼烂,然后咽进肚子里,不敢去面对,一旦面对了,看到明天初升起的太阳,可能不会微笑。
这些,我相信不止我,还有万万千千个我。我的儿时玩伴,也不止他们,还有千千万万个他们。草根逆袭其实并不苦逼,苦逼的是看不到努力后的希望,失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望多了会变成绝望,阶层固化其实并不恐怖,恐怖的是阶层固化所产生的深深的无力感。
作者:
曾博同学,专注记录北上广深的年轻人,微博
@曾博同学
,文章经作者授权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