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入选美国HHMI国际青年科学家,摄于美国HHMI
记:
“最年轻的院士”这样一个光环,有没有给您带来压力?
邵:没有什么压力,我只是觉得多了一些责任,就是在一些学术体制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
记:
在科研上取得“突破性的成果”,您觉得是靠运气多一点,还是靠努力多一点?
邵:是这样的,如果你足够努力,运气总会来的;如果你不努力,不可能。
记:
您觉得在做科研的过程当中,最吸引您的地方在哪儿?
邵:科学探索的过程。我对一件事情原来是不明白的,全世界人都不明白,那么我们现在明白了,这是一种享受。
夜幕降临,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健身房里,邵峰挥舞着乒乓球拍,时而一个削球,时而一记扣杀,在防守和进攻之间自由切换。
而在显微镜下的微观世界里,邵峰面对的则是另一场关于进攻与防守的较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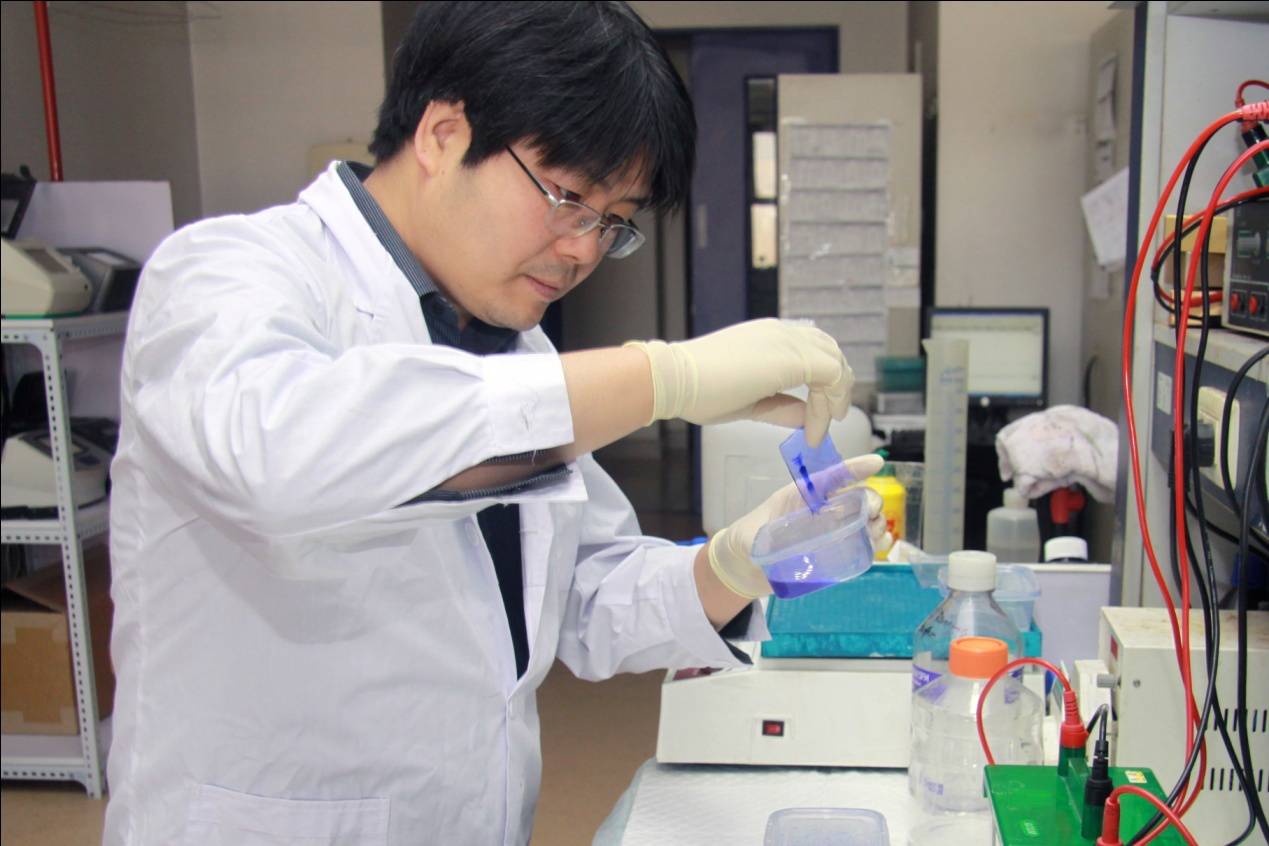
我们主要是研究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跟病原之间的一个斗争。我们实验室主要是做细菌感染的,比如说像肺结核菌、霍乱、伤寒这些疾病,这些都是由细菌感染导致的。他们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跟他们斗争,当然他们想赢我们,我们也想赢他们,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里面去做研究,应该说是做到了世界最前沿。
眼前的邵峰,宽松T恤,运动鞋,脸上写满锐气,这与“最年轻”的院士这一标签显得极为相称。他试图将自己的研究领域解释得更为通俗易懂,并坦言,外界更关心成果会在哪里“应用”,而这个问题对于“最前沿”的科研探索来说,似乎无解。
我想强调一个观点,就是说,新的科学发现、新的科学探索,有时候你是不知道会走到哪儿的,它最终会对我们的健康、对人类的生活有多大的影响,很多东西其实是无法在现在进行准确预测的。
要做“最前沿”,那就意味着“原创性”的探索——不知道哪条路能通向罗马,也许罗马根本就无法抵达或者不存在,一切都像是一场“冒险”。这对于邵峰而言,似乎已是司空见惯。当年他没有留在美国而是回到国内做科研,又何尝不是一个“冒险”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