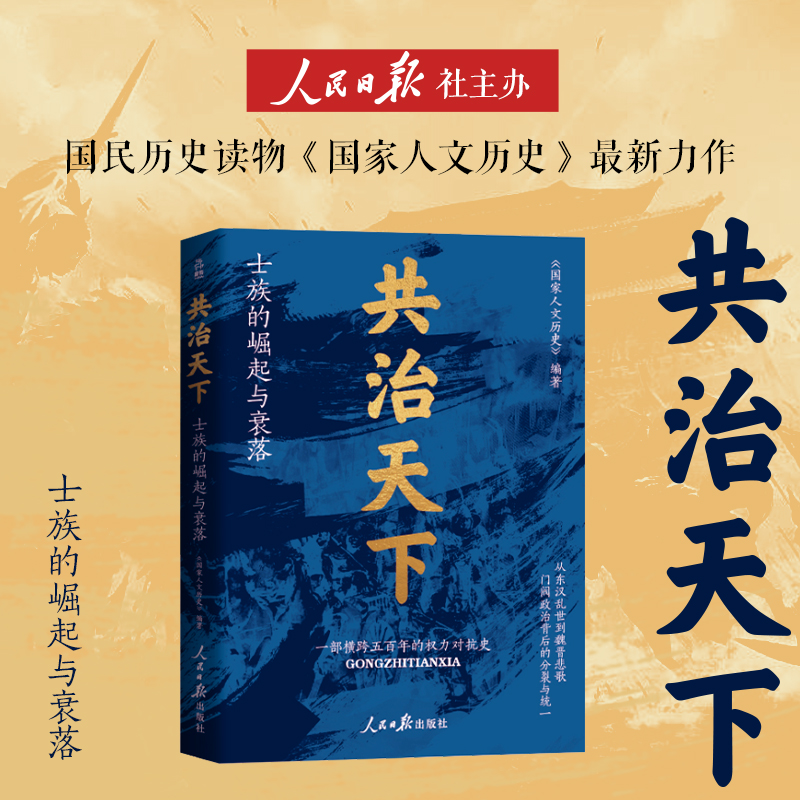西周初年的大分封中,齐国被分封在今日淄博市东北部的临淄
(营丘)
一带,历经数百年的时间,终于在莱夷为代表的东夷部落中逐步站稳脚跟。在随后漫长的岁月中,齐国逐渐征服了周边的诸多东夷部落,将济南盆地、胶东半岛、河济平原等地纳入统治,还进一步南下吞并了今日鲁南地区的莒
(jǔ)
国等地。到战国时代前夕,经过几百年的征伐,尤其是对以莱夷为代表的东夷部落进行兼并,齐国的疆域从今日淄博周边的一隅之地,扩展到了今日山东省大部和河北省南部的广大地区。但到这时,齐国的扩张也就进入了一个瓶颈。


齐国的东方是胶东半岛,春秋初年散布着广泛的莱夷部落。但到战国初期时,齐国在这个方向的领土已经到达了黄海,自然也就到了扩张尽头。从齐国向西是当时华夏世界最富庶的中原地区,这里包括赵国的邯郸、卫国的濮阳等繁华大城。但齐国春秋时代就被晋国所压制,到战国时,脱胎自晋国的魏、赵、韩同样不是易与之辈,一旦面临齐国的入侵很容易团结起来,齐国在这个方向难以拓地。
齐国的北方是华北平原,春秋时代这里的开发程度极低,在这里发展的燕国甚至一度被当地部落隔绝道路而与中原诸国失联。齐国控制了华北平原东南一角,边境到达黄河进入渤海的出海口一带,再往北便是燕国国都周边的核心领土了。
齐国的南方边境地理环境复杂又恶劣,西南方向隔着泰山是鲁国,被称为“大野泽”的巨大沼泽地也在这个方向,正南方向则是堪称天堑的沂蒙山区。这些天堑的存在,使得齐国向南扩张严重受限于后勤能力。虽然如此,战国初期的齐国在这个方向还是颇有扩张,不但将鲁国完全削弱成了一个弱国,还继续向南拓地,最终与扩张到淮北地区的楚国和在这里经营已久的宋国接壤。


这里存在一个第三方对诸侯兼并的“痛感”问题。对于中原诸侯国来说,如果一个诸侯国吞并了周边的“蛮夷”部落,其他诸侯国很少能感知到这种吞并,也多半不会把这当回事,也就没有“痛感”。如齐国吞并以“莱夷”为代表的东夷部落,秦国吞并西戎诸多部落,楚国吞并诸多越人部落,中原诸侯国根本不会去关心。到战国时,秦国还能继续吞并义渠、陇西等地的戎狄,楚国还能继续经营百越地区,赵国有娄烦、林胡这些边地民族聚居区扩张,甚至燕国都可以向东胡部落拓地,但齐国却没有了类似的“蛮夷”部落可以吞并。甚至秦国在战国前中期的诸多战争,除了当事诸侯国外的第三方也很难有“痛感”。巴、蜀诸国控制的四川盆地,对中原国家来说完全是陌生的异域。魏国西部的河西、上郡、河东,也是与其他诸侯交集较少的偏远之地。秦国在东方攻占的第一批重镇宜阳、南阳,也在韩国的西部边境,其中的南阳还是韩国作为秦国盟友时从楚国手中夺得的,中原其他诸侯很难有切肤之痛。
战国中期,齐国向南和向北都尝试突破地缘桎梏进行扩张。齐国向南此时要面对的是已经灭亡越国、吞并淮河流域的楚国,双方围绕淮北、泗上诸国和今日徐州一带等地区展开了反复争夺,但都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北方,齐国进行了更大胆的冒险。齐宣王以干预燕王哙禅让宰相子之引发的燕国内乱为名入侵燕国,试图扶植原来的燕太子平为傀儡君主,大批齐军常驻燕国境内并大肆烧杀抢掠,但周边诸侯显然都对燕国的迅速沦亡感同身受。燕国西边的赵国此时由一代英主赵武灵王统治,他与韩国一起拥立身在韩国的燕公子职为新的燕王,秦国和魏国也站队燕国,四国一起出兵,在燕国百姓的支持下击败了燕地的齐国占领军及其扶立的燕太子平。
这场动乱,齐国损失并不大,齐军还从燕国掠夺了大量的财富,但这一事件充分暴露了地缘环境对齐国扩张的负面影响:齐国周边只剩下赵、魏、燕、宋、楚这些大国,不像秦、楚、赵、燕那样还有地方可以开拓。齐军对周边任何一个国家取得较大胜利,其他所有诸侯都会联合起来反对,以防止齐国的进一步坐大。
就在此时,地缘环境更为恶劣的宋国最终引爆了自己和齐国的地缘危机。
宋国是商王朝王族的直系后裔,从武王伐纣以来已经存活了七八个世纪。战国中后期时,宋国夹在齐、魏、楚这三个一流强国之间,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这三个国家之间相互平衡的产物,其地缘形势可以说相当绝望。大部分时间内,宋国都奉行结好楚、魏的外交政策,作为一个大国之间的缓冲国存在。然而,宋康王驱逐兄长自立后,按《史记》记载:
“东伐齐,取五城。南败楚,拓地三百余里,西败魏军,取二城,灭滕,有其地。”
宋国突然大爆发,同时对周边所有强国开战
。“败魏”指公元前317年三晋联军被秦将樗
(chū)
里疾在修鱼击败时趁火打劫,“败楚”指公元前303年齐、魏、韩联合伐楚时宋国趁机夺走了楚国的淮北,“伐齐”说的则是公元前294年田甲挟持齐湣王期间宋国夺取齐国五座边城。


宋康王如此激进地到处树敌到底是因为什么,我们已经很难得知了。宋国的军事冒险没有立刻遭到清算,是因为齐、楚、魏都有自己的内部问题要优先解决,而宋国的实力比其中最弱的魏国仍然颇有差距。当这三个国家最终都能腾出手来,并且达成共识要消灭宋国时,宋国是没有任何反抗机会的。而宋国偏偏在此时发生了内乱,于是齐军轻松攻破宋国首都,将其灭亡。至于楚、魏在灭宋过程中的收获,我们不得而知,史书上随后记载“齐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欲以并周室,为天子。泗上诸侯邹、鲁之君皆称臣,诸侯恐惧”,宋国侵占的淮北之地不知道有没有被楚国短暂收复,但此时又被齐国占领了,“西侵三晋”大约是齐军吞并了魏国占领的宋国土地。齐国火并楚、魏吃了独食,几乎独占了灭宋成果。
战国中期以来这半个多世纪,齐国一直是最一流的强国,马陵、桂陵之战击破巅峰期的魏国,利用燕国内乱五十天内控制燕国全境,与韩魏合兵在垂沙之战中大败楚国,作为合纵长领导诸侯联军攻入函谷关迫使秦国割让大量关外土地求和,都是其实力的体现。在灭宋前不久,秦国和齐国曾短暂以“东西二帝”并称,说明这两国的实力凌驾于其他诸侯国之上。独吞宋国后的齐国领土大增,如果能消化宋地,其经济和军事实力都会有进一步提升。在宋康王的一系列扩张后,掌握富庶淮泗地区的宋国实力已经超过燕国和韩国,足以与魏、赵匹敌,而齐国却迅速灭亡宋国并鲸吞其全境,这个效率也让魏、赵等周边诸侯大为惊恐。齐国灭宋还意味着以鲁国为代表的泗上小国已经完全被齐国领土包围,假以时日这里也会被齐国吞并后消化。

对于魏、赵、韩来说,他们西边是一个逐渐东进的秦国,东边则是灭宋之后实力大幅提升的齐国。事实上,秦国和齐国瓜分三晋的可能性在当时也很大,几年前秦齐“互帝”不了了之,但如果他们真的“互帝”成功
多半很快会开启瓜分三晋的进程。对北边的燕国来说,一代人之前,齐国就差点灭了自己,齐国消化宋国故地后再度北上的话,燕国还能不能幸存就很难说了。对秦国来说,齐国的实力继续膨胀下去,魏、韩会逐渐沦为齐国附庸,秦国继续东进也会变得困难。因此,秦国决定站出来组织联合伐齐。
在齐国灭宋后的第二年,秦军在途经韩、魏领土并与这两国军队会合后,进入陶邑周边的原宋国领土,击败了这里的齐国占领军。赵国也从北方出兵,攻占了齐国的灵丘城。在获得了前哨战的胜利后,五国联盟在第二年派出自己的主力精锐,会师由燕军大将乐毅统率,在济水以西的决战中击败了齐军主力,随后渡过济水追击,一举攻占齐都临淄,齐闵王也踏上了流亡之路。
与秦国矛盾太深的楚国没有参与这次五国伐齐,在齐国主力背叛后
(齐国将领触子率齐军主力在济西之战中与五国联军对峙,因齐闵王强令决战并威胁惩罚其家族,触子临阵消极指挥,导致齐军大败)
,派出大将淖齿派兵援齐。但楚国近年来吃齐国的亏并不少,十几年前垂沙之战主力被歼,两年前又被齐国黑吃黑夺走了淮北之地,所谓援军只是浑水摸鱼时降低齐国君臣戒备的借口。最终,被齐闵王任命为齐相的淖齿暴起发难,虐杀了齐闵王。虽然淖齿后来被齐国民众攻杀,但楚国却借着这个机会成功控制了淮北地区。


同样被诸侯围攻,秦军战败时可以退缩到函谷关后面,就算诸侯联军花费巨大代价攻破函谷关,也通常无力继续西进。而齐国的地缘形势却并不能支撑他们同时对抗多个大国。不同于“四塞之地”的秦国,齐国在各个主要方向都没有可以倚靠的天险,著名的天堑泰山此时已经变成了齐国腹地,齐国必须用灵活的外交手段和足够的机动部队来抵消恶劣的地缘。当周边所有强国都认为齐国的扩张打破了他们的平衡,甚至连秦国都千里迢迢派兵来加入反齐同盟时,无险可守的齐国一旦野战失败,就会迅速丧失临淄等富庶的核心地带,躲到胶东半岛等区域苦撑待变。
在进入齐国核心地带大肆掠夺后,大部分诸侯国认为削弱齐国的战略目标已经达到,于是结束了这次军事行动。燕国仍然想继续攻占齐国剩余的领土,但在经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之后最终被田单用火牛阵击败,田单拥立齐闵王之子田法章为齐襄王,齐国得以复国。
复国后的齐国,
沦为一个被赵魏楚欺压的二流诸侯国
田单拥护齐襄王田法章复兴的齐国,此后又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田法章及其子末代齐王田建统治时期
(包括田建初年由生母、田法章之妻君王后摄政的时代)
,并没有让齐国再次伟大,反而只能偏安一隅,完全没有了当初和秦国分庭抗礼的气势。到秦始皇开始灭亡关东诸侯国时,齐王建更是选择对这一切袖手旁观,等秦国灭亡关东五国时,孤零零的齐国几乎只做了象征性抵抗就灭亡了。按照传统口径,这是因为当时的齐相后胜收受了秦国间谍贿赂,对齐王建进谗让他坐视赵、魏、楚这些周边国家灭亡,于是最后轮到齐国面对秦国时,便孤零零再找不到盟友了。
这个说法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却更像是“从后视镜看历史”,是用后面秦国灭亡六国的史实反过来指责先人的决策错误。我们不妨思考一个问题:从田法章夫妇、田建的视角来看,驱逐燕国势力后的齐国,最凶残、最危险的敌国是谁?《史记·楚世家》记载了楚顷襄王十八年
(前281)
一位说客对楚王说的一番话:
“故秦、魏、燕、赵者,鶀鴈也;齐、鲁、韩、卫者,青首也;驺、费、郯、邳者,罗鸗也。”
按照他的意思,此时的秦、魏、燕、赵可用鶀
(qí)
雁
(大鸟)
作比,也就是一流强国;齐国沦落到与韩、卫、鲁并列的青首
(中鸟)
,也就是中等国家;至于邹、费、郯
(tán)
、邳
(pī)
等罗鹫则是仰人鼻息的小国。此外,这番问对的参与者楚顷襄王虽然丢失了郢都,但楚国此时的重心已经东移,在两淮流域站稳脚跟后仍然是一流大国。也就是说,当时的秦、魏、赵、燕、楚,都比复国后的齐国更强大。
在这些一流强国中,秦国虽然实力最强,却仅有一个陶邑
(定陶)
与刚复国的齐国接壤,而且未来魏国更是吞并了秦国的这块飞地,因此齐国很难直接感受到秦国的威胁。五国伐齐中最积极的燕国很快会重新沦为弱国,而且被赵国牢牢压制,也不再是齐国的主要威胁。但剩下的赵、魏、楚三国,都堪称齐国后期最凶残的敌人。


赵、齐两国在战国后期一直围绕华北平原进行激烈争夺,五国伐齐时赵国几乎派出所有精锐,大肆掠地。公元前284年五国伐齐的主要战事结束后,主力继续作战的除了深入胶东半岛的燕军,便是蚕食黄河与济水之间齐国城邑的赵军。公元前283年,廉颇率赵军攻占阳晋;公元前280年,赵奢率赵军攻占麦丘。即使在公元前279年田单击破燕军复国之后,赵国仍然在进行这种蚕食:公元前274年,赵将燕周攻占齐国五都之一的高唐;公元前271年,连没有什么作战经验的文官蔺相如都领军伐齐至平邑,俨然把齐国当作刷军功的经验包。至此,齐、赵两国几乎是以济水为界,齐国在济水与黄河之间的广大领土都被赵国蚕食殆尽。
再这么发展下去,赵国大约会进一步渡过济水逐步蚕食齐国腹地。但此时赵国与秦国的矛盾逐步升温,最终导致了公元前260年的长平决战。讽刺的是,长平对峙高潮中,赵国竟然还想问齐国借粮,此时的赵国才是齐国最凶恶的敌人!
而已经被秦国泰山压顶牢牢压制的魏国,在齐国的崩溃中受益最大。五国伐齐时,魏国夺取了原来宋国的大部分精华地区,并在这里设立了大宋郡和方与郡。田单复国时连原先的齐地也不能完全收复,对宋地自然鞭长莫及。长平之战后魏国出兵救赵,在邯郸大破秦军主力,随后便占领了秦国在陶邑一带的飞地,这块飞地除了原属于宋国的陶邑,还包括刚、寿等原属于齐国的城市。声势正盛的魏国又顺手牵羊,攻占了齐国五都之一的平陆。魏国击败秦国的结果,不要说宋地或者原属于齐国在齐襄王时代丢失的刚、寿,连田单好不容易收复的平陆都丢了。比起这个如狼似虎的邻居,齐王田建或许还是觉得远在天边鞭长莫及的秦国稍微温柔一些。


楚国在五国伐齐时打着援助齐国的名义浑水摸鱼,残酷虐杀了齐闵王,随后又重占一度被齐国夺走的淮北地区。但楚国显然不满足于此,而是继续北上进入了齐国经营数百年的势力范围。如薛邑曾经是孟尝君封地,五国伐齐后被鲁国浑水摸鱼占领,在楚考烈王继位初期被楚国夺取。几年后,楚国又灭亡了鲁国,将投降的鲁国君臣封在莒地。莒是当年五国伐齐时齐国最后的两个据点之一,此时也已经被楚国渗透。可见战国末期楚国不断北上,侵占了很多齐国领土。楚国还吞并了其他泗上小国,与魏国争夺宋国故地,对齐国南部边境构成了极大的压力。
曾经和秦国东西并帝的齐国,在五国伐齐后元气大伤,沦落为被赵、魏、楚轮番蚕食的二流诸侯国。后世金宣宗在华北打不过新兴的蒙古汗国,异想天开地试图南侵“取偿于宋”“北失南补”,结果与南宋王朝两败俱伤,金王朝这个奇葩思路在历史上也沦为笑柄。赵、魏、楚此时的作为,堪称与金宣宗的奇葩思路不谋而合,便是“取偿于齐”“西失东部”。这个荒唐逻辑的最高潮,大约是公元前241年赵、魏、楚、韩、燕五国伐秦,面对函谷关天险一筹莫展时,主帅庞煖灵机一动,借口齐国不参加合纵是秦国帮凶,兵锋东进抢了齐国一座港口城市。但此时的齐国比一千五百年后的南宋更弱,面对这种荒唐的战争借口也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土地惨遭蚕食。
齐国固然知道秦国是虎狼之国,但战国后期持续半个多世纪都在围攻和瓜分自己的赵、魏、楚诸国同样如狼似虎,更是齐国生存的最直接威胁。从这个角度看,齐国在秦国每灭一国后的道贺,未必不是出自真心诚意。既然衰亡的结果无法逆转,亲眼看着秦国把自己的这些敌人一一消灭,然后以相对体面的方式退场,也许是齐国不坏的结局了。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进击的士族
旁落的皇权
跨越五百年的权力对抗史
国民历史读物《国家人文历史》专业团队
最新力作
展现士族潮起潮落的史诗级历史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