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在一个胡同里长大的。
胡同里的其他孩子,已经结婚了;胡同里的那些大人变老;而老人,已经基本去世了。
这个胡同没有收件地址,没有车,只有两侧房屋阻挡下的泥土,接受着三米宽光照。下雨时,一切都是下雨的样子;寒冷时,一切都是寒冷的样子。房顶上的引风机把火炕的灰烟吹到天上,鸽子从楼房飞向平房再飞回去,有的鸽子被有的猫吃掉。
差不多年龄的小朋友,在这片方圆两百多米的空间长大。我们手里攥着小纸片,在土地上拍,然后坐在土地上,汗流到土地里,变成土地的一部分。我们拿出珍藏的玻璃珠赌博,那是童年间唯一的硬通货。
三米宽的光照逐渐变窄,直到它挪到墙上我们够不到的高度。我们回了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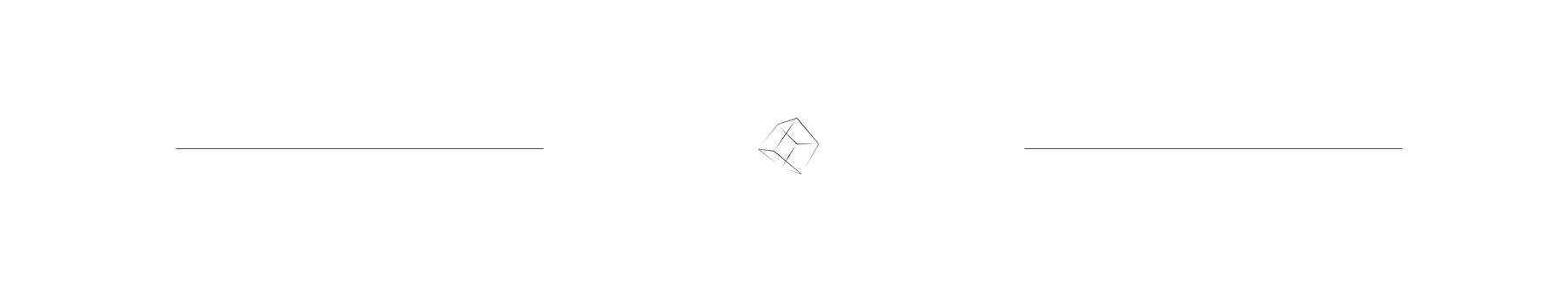
家和家的距离是墙的厚度。
冬天没有什么像样的蔬菜,所有人家把成吨的白菜摆在院子里,或者囤在房顶上,或者腌渍在巨大的陶缸中。
雪夜把所有的声音吸收掉,我躺在炕上,躺在姥姥和姥爷的身边睡不着。我看着冰晶窗花外的世界——月亮洒扫庭除,白色的雪片像各自搭乘了降落伞,深夜漫长,我知道就算起床,外面的天色也还是这样黑着。
冬天最好玩的是各式炮仗。
这么多年过去了,各种科技一直在进步,但炮仗,还是我小时候玩的炮仗。
我们在左兜里装着摔炮,右兜里装着划炮。划炮的杀伤力要比摔炮强一些,像划火柴一样划一下,三五秒的燃烧时间,最后在一个地方砰得爆炸。
那时候的大人并不太关心青少年的行为安全。我们尝试着把划炮丢在一切能产生增益效果的地方——挖的坑、啤酒瓶、别人的自行车坐垫、砖和砖之间。其实没太听说有谁玩爆竹被炸了,最多就是火光溅到了手上,拍一拍就完事了。
有的时候会买一袋更高级的各式炮仗,比如点个火,就能飞出来一个降落伞不知道飞到哪里去,比如可以像是莲藕一样可以咻咻咻像天上发射五十枚小弹炮的盒子。我喜欢这些特别的炮仗。
这条胡同的冬天,是在小孩子们的硝烟中度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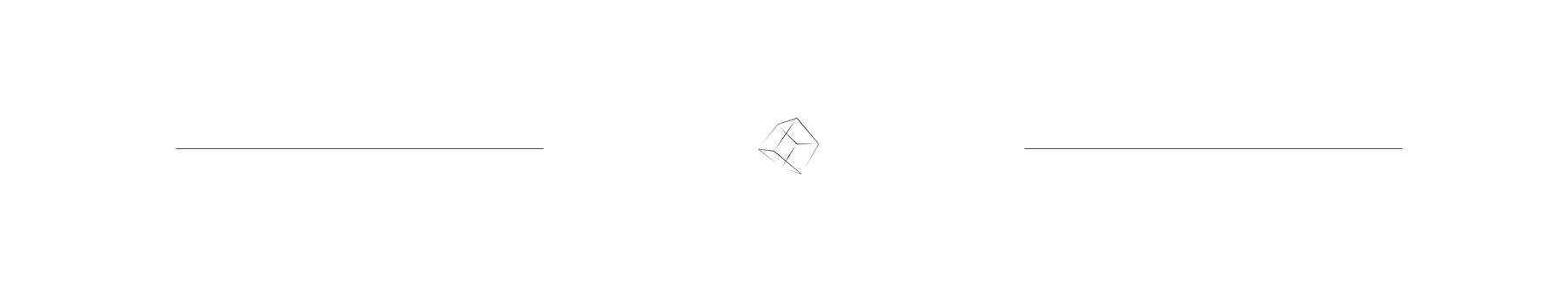
真正的小孩对昆虫不应该存在任何恐惧。
蝗虫很多。我们拆掉的蝗虫的腿更多。
课本上告诉我们蝗虫靠腹部呼吸,从保护生命的角度来讲,这显然不是一个孩子应该看到的信息——为此很多蝗虫的肚子在水盆中呛完蛋了。绿色的叫扁担钩,脸很长,头顶是尖的,和蝗虫比,看起来智商更低,最大的能有半个手掌那么长,腿的根部是紫色的,很性感。还有螳螂,比较喜欢出现在木柴堆里。苍蝇在院子里到处都是,拍苍蝇非常愉快,是需要高卡路里版本的捏泡泡纸。
菜粉蝶喜欢在花朵上呆着,大红蛱蝶喜欢吃烂掉的西瓜。草地里会有一些不知名的小小的蓝色蝴蝶,这种小蝴蝶最难捉到。事实上,我从来都没有捉到这种小蝴蝶。
我们在一片立交桥下面的草地里烤土豆。
不知道谁从家里偷了两个小土豆出来。
我们把草拔了出来,刨了个坑。找一些破纸枯草填在里面,点上火。土豆就放在里面。
我们从来没有电视上那样用一个网兜抓各种昆虫,都是用手。蝗虫和扁担钩,用手扣;抓蝴蝶,就先把草往一个地方快速拨倒,它就被压在里面了;螳螂抓住脖子;蜻蜓,慢慢靠近,捏住它一片翅膀。
瓶子是最常见的游戏道具。我们把虫子放进去,放几根草,倒几滴水——生态瓶。是可以在里面养很久没错,但还没等到它们死掉,我们就腻了。
据说立交桥下面那片巨大而阴凉的土地里,有骷髅。我见过一次白白的东西从地里支出来,吓得赶紧跑掉了。
我们躺在立交桥支柱支起来的小平台上。凉风穿堂而过。小汽车、陀螺零零散散地堆在身边。我们聊谁又把谁欺负了,谁要去哪里上学,谁家晚上做什么吃。我很喜欢莹莹家的炒豇豆角,但姥姥说,她家的豇豆角有什么好吃的,都不放肉。
躺得有点久,我们突然想起来那几个土豆。
回去的时候,土豆已经熟了。黑漆漆的皮,周围的草被烧焦,
烟消失在我们的头顶附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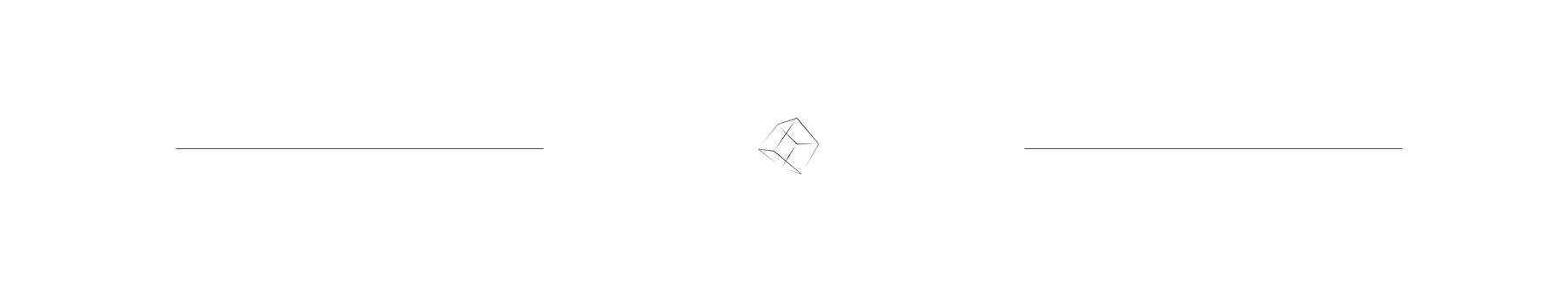
我最喜欢的玩具,不知道是如何出现的。
后来似乎问过几次,应该是妈妈怀我的时候就有了。
那是一个小小的斑点狗,里面填着米粒,软趴趴的,眉目间充满灵魂。
我从来没有给他起过名字,但是他扮演过很多很多角色——一个正义的战士,能飞能打,或者会魔法,可以使用火焰攻击敌人。有的时候他会黑化,变成我不喜欢的样子。但是最后,他都会被正义感召,改邪归正。
他拥有很多身衣服,这些衣服来自于红领巾、袜套、水晶梨外面的白色塑料。我需要他,他也需要我。
中间他的米漏过,我发现原来不是米,是砂砾。不过没有关系,后来姥姥用大米把他填好了。拥有了新的生命的他,脖子上因此有一个红色的线结。
妈妈后来给我买了另一只小狗玩具,是穿着衣服的史努比。但是我并不喜欢史努比,眼睛太小了,而且他的衣服,看起来不是很正经。
我还是更喜欢斑点狗。
所以正反派的划分,非常固定了。
有一次和家人生气,我就坐在床上,把这只史努比狠狠地往地上一摔。鼻子磕到了桌腿,掉了。这下,姥姥也没办法了。
斑点狗和没有鼻子的史努比是一对永不能和解的冤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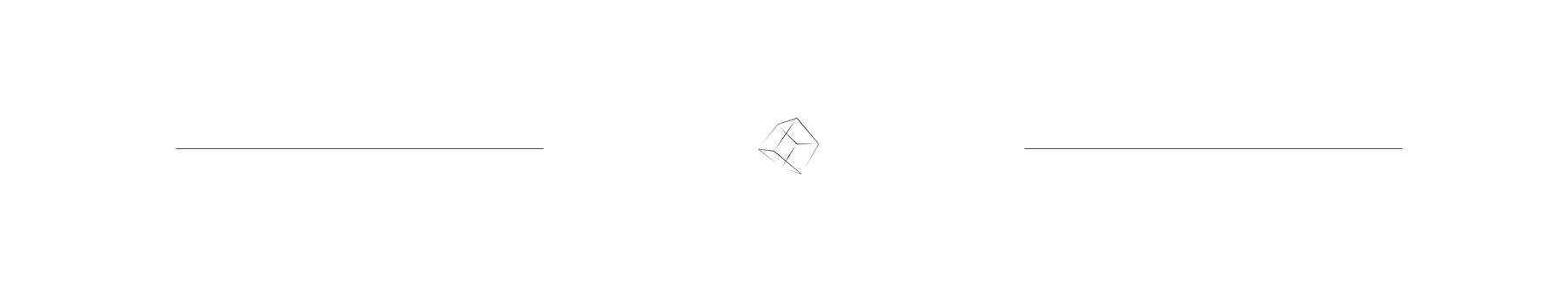
我仍保留一些那时候的照片。没有数码化的影像,能留下来的很少。
我穿着橙色的上面写着sport或者fashion的童装在院子里喂鸽子的照片。
在家里过生日搂着莹莹亲脸面对满桌蛋糕和排骨豆角的照片。
在班级门前举着立体手抄报的照片。
这些小事不算太重要,对我的人生也没什么决定性的影响。
我的童年基本是放养状态的。因此我干了没几件好事,剩下的都是无聊的事和坏事。
我是在一个胡同里长大的。
胡同里的其他孩子,已经结婚了;胡同里的那些大人变老;而老人,已经基本去世了。
我现在在传媒行业工作,每天要看那些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见各种各样的人。对童年的回望一直被歌颂着,不是因为我们喜爱自己无需负责的样子,而是在小孩的世界里,快乐可以没有价格。
我们无法再被一根五毛前的冰棍吸引了,无法不对写着sport的衣服产生厌弃之情。
我们长大了,这很好。
只不过,如果我能穿越回那个烤土豆的下午,看着围在一团灰烬找土豆的孩子们时,我只会在墙角悄悄地看,看那略显可爱的烟在他们头顶的高度散掉。
我不想冲上去跟他说——“不要吃,这个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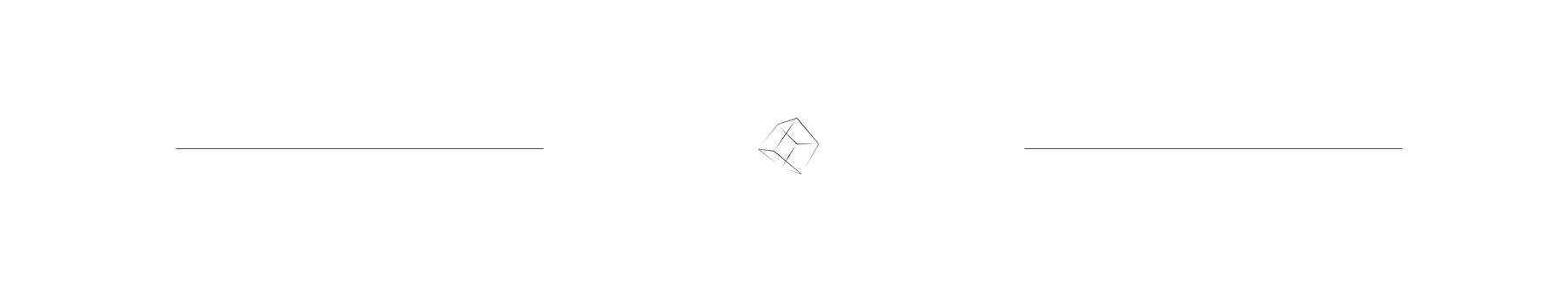
蜜芽玩乐节
上海
我在大巴上帮孩子们换玩具
可爱有的时候就很恼人
他们不太care一个玩具的价格甚至包装
有的时候就会单纯被颜色吸引
有的时候,她就会说:“我喜欢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