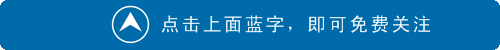
编辑。出版过《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庄子我说》、《尖锐的秋天:里尔克》、《陷阱里的先锋:博尔赫斯》、《像唐诗一样生活》等十来种书。现供职于某杂志。
“一个诗人有时候之特别可爱,并非他们作品特别好特别高,便因他是我们一伙人”,这是顾随先生的女弟子叶嘉莹在《顾随诗词讲记》里,所记录顾随先生的一句话。当年我读此书,曾撰一文《良师总被夜深埋》谓:“顾先生这话十分高妙有趣,令人拊掌大笑,可浮一大白”。其实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这句话不按牌理出牌,看上去很无厘头,不能作为一种评骘标准而贯之四海,却能打动人心。当然“一伙人”看上去像江湖团伙,由于小圈子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如是呈现在公共领域内,难免干犯普世规则。好在文艺评论的确不是科学研究,审美不是统计实证,故多年后我还能记得起这句“不评之评”。
读了杨渡兄的《暗夜里的传灯人》(台湾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版,下引若非注明则出自此书)——大陆中国文史出版社在次年出版了近乎同名的《暗夜传灯人》,但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肯定有一些删削,因没读过大陆版,故无法做内容差异之对比——我就想起传灯给他的这些人,虽不是所有人都互相认识或有生活上的交集,但说他们是一伙人,大抵是说得过去的。同时,翻台湾《文讯》过刊,看作家辛郁曾在其上开有一个“我们这一伙人”的专栏,更坚定了我用“他们这一伙人的禁果”来名此篇的想法。

“传灯”来自佛教术语,谓灯灯相传,不会熄灭;用世俗语言来讲,就是薪火相传。这自然都是在强调人力。但我认为人力要得到成全,还是要有“黑暗不能胜过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信念才行。《暗夜里的传灯人》区为三部分:一为四九年后大陆知识人之南渡;二系禁书之启蒙;三是岛上人物之抗争。三部分,简言之,可谓“人——物——人”的布局,虽然中间主要谈“物”——书籍,但书籍也是人写的,故以“传灯人”冠名也是恰切的。灯自然应该在“暗夜里”才成为必要,不过到了一个自由的环境里,犹如庄子所谓“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这样你就会理解晚年的李敖为什么蜕化到,你都不想提及的地步?那是因为台湾“日月出矣”。
台湾今天的文化传承更多走向了比较开放的自由竞争之境,倘非绝学,大多可以通过学院化与媒体的建制性传布手段来完成。南渡之知识人凋零殆尽,渐成纸上人物;书皆可出,禁之而成历史;抗争则庶民皆可参与,大多不劳英雄来举火也。这样说来,我们读《暗夜里的传灯人》没有意义么?自然不是如此。也许台湾人看这些事情真成了历史,而对于我们来说,书中的一切,可谓正在进行时。
国民党兵败退到台湾后,不少大陆知识人跟着撤退到海岛。其绝对数量与留在大陆的知识人相比,也许不算大,但对于台湾人口基数所能负担的需求来说,却不乏过剩之虞。因此才有像吕佛庭这样的书画家到台中师范学校教书,培养出了像杜忠诰一样的名书家的事。对他的画我没有研究,但家藏有吕佛庭先生签赠送人的《蜀道万里记》(《畅流》半月刊1972年发行),以浅白文言写出,实在是上佳的游记。
至于杨渡所列曾在其母校台中一中教书的老师如楚卿、杨念慈、蔡仁厚、齐邦媛,他们的书我都有幸读过。前二位我曾翻看过黎明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的他们之小说自选集,后者中的蔡仁厚我曾在《如何读懂当下的台湾——评陈世昌〈战后70年台湾史〉》一文里有所涉及,因为他是“四六事件”后,参加台师大吴自甦奉学校之命所组织的“人文学社”的学生,其中导师就有牟宗三。再后来还读过《蔡仁厚教授七十寿庆集》,至于齐邦媛大名鼎鼎的《巨流河》就更不用多说了。这样看来,大陆的中学生在彼时是不可能有这样的福气的,至于反右后有老师受贬下放,完全没有自由的教书氛围,惊弓之鸟,是不敢作自由之鸣的,不敢像齐治平那样以高歌代替教学。
知识人之南渡,杨渡谓之“渡海传灯人”。其实更为广泛地来看这个内战后知识人的迁徙流离的现象,更能体现出1961年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所谓之“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李济之于张光直,后来影响了台湾大陆两地的考古学界。殷海光之于林毓生,正可谓在台湾传灯,而在美国结果。余英时之由香港新亚书院,而至美国读书,而成文史大家,惠及台湾及改革开放后的大陆学子,王汎森、罗志田是其最著者。而杨渡提及的许寿裳、台静农、姚一苇等,前二位颇有声名,有黄英哲这样的许寿裳研究专家编辑出版了《许寿裳遗稿》,亦有大陆学者黄乔生主编出版了《台静农全集》,独姚一苇大陆人多不了解,从我家所藏的《姚一苇文录》与《姚一苇戏剧六种》来看,有相当的水准。这些人所传者不仅是书斋式的学问,更是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不过,自由这事儿没有保守主义垫底,没有真正的信仰来托起,其难免通往奴役之路,因为你做的看上去是在为争取民主自由,骨子里却可能为自己套上了绳索,特别是一些左派的做法,更是如此。书中说台静农被捕,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声援下,台静农被关后不久获释。国民党滥捕学生及其他人员,固然是不应该的,但于今的档案研究来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却是苏俄共产国际及间谍渗透的一个机构,其目的当然不会是为中国好,也不是为争取什么民权与自由。

我常在想,不知与杨渡同庚,曾是大陆诗人的老威,要是读了《暗夜里的传灯人》,他会作何感想。师承不同就不必说了,老威根本就没上过多少学,只是做过往来乡村与大山里的卡车司机,就是禁书也许只可怜地看过《少女之心》之类的手抄本。当然文革前,有门路有级别的人,也读过彼时分等级的内部所印之书,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灰皮书”、“黄皮书”,其中就有节译的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等。
什么是禁书?当然每个有权力的禁书机构与个人,其认知可能并不相同。事实上,也讨论不出一个普遍的的禁书规则来,但大抵事关掌权者的利益,可能就在该禁之列。要言之,权力不受约束,什么书该禁及不该禁自然有很大的随意性。关于禁书的具体做法,《暗夜里的传灯人》里有不少可以言说的地方。比如杨渡们办《春风》杂志,其实就是大陆的以书代刊,大陆有的是办法能堵住这样的漏洞,但他们把《春风》诗刊改成《春风诗丛刊》后就可以有效避免查禁:“因为他既非杂志,自然不必再重新登记。就算禁一本,下一本书照常出,而且依照出版法,出版是不需要出版社登记的,只要署上作者,谁都无法阻止。而《春风》诗刊是由作者群集体出版的,因而谁也挡不住。”套用时下流行的说法,真为国民党政府的智商着急啊,说明他们对彼岸的研究与学习也不深透啊。
即便你想办杂志,被他们禁了,你也有空子可钻。比如后来为争民主自由自焚的郑南榕,他办刊物的时候,就使了一招。这一招在我们这里看来是多么的小儿科啊,可在台湾却可以屡试不爽。“而郑南榕则开始经营《自由时代》系列周刊,他申请了好几个以《自由XX》命名的刊物,禁一个,再换一个,反正我‘自由XX’,风格一致,民众自会认识”(P88)。这还不是国民党的统治需要“进化”的地方,更搞的尚在后面。“因为当时的警总并无查扣未出刊书本的权力。依照出版法,得等到杂志、书籍印刷装订好了,才算正式出版,如此才有查禁的权利。”(P81—82)于是书籍杂志出版方与警总,都守候在印刷厂门口等着抢书,抢多抢少,就看双方哪边人多势众了。所以当他们写了一篇可能导致杂志停刊被查禁的文章时,他们考虑的只是“要不要为这篇稿子,和警总打一架”(P81)。也许我的感受不妥,但读到这样的话,真有点大人跟小孩子玩过家家的感觉。
我发现杨渡所谈的禁书,固然与我们所看禁书有不同之处。但他们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启蒙时,所读的书,与大陆八十年代的,也有不少相似之处,充分表明两岸社会有某种意义上的同质性。“此外,还有邓克保(柏杨)的《异域》,郭良蕙的《心锁》,李宗吾的《厚黑学》,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以及据说是全本的《金瓶梅》”(P65—66)。除郭良蕙外,以上的作家与书籍几乎都参与了大陆八十年代的启蒙工作,也都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禁书。柏杨在大陆抢滩的是《丑陋的中国人》,而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还使出此书的出版社及相关人员,受到诸种惩罚。从警总管控之毫无创意,只到印刷厂去与出版者抢书刊来看,大陆这样的惩处,台湾是没有的。因为台湾许多出版社都是私营的,在我们大陆人看来,到了可钻的空子非常多,想出就出的地步。
小说家陈映真从监犾出来不久所出的小说《将军族》之被禁,引起多方猜测,大家还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倘若禁书,很容易猜到被禁原因,管控者会觉得自己无能,不然怎能让你体会天威莫测、宸衷难断呢?“查禁的原因,本身就是禁忌,这就是‘禁忌年代’的特征。‘权威’要变成‘威权’,就是不容许你问他原因。最后逼得你猜测他的心思,揣摸他的心思,甚至暗暗讨论他的心思,如此才能让你想得太多,猜疑太多,满地阴影,最后什么都不敢做。”(P59—60)这对禁书心理及其后遗症的阐发,是相当有意味的。
《暗夜里的传灯人》提到的禁书,幸运的是,我拥有一些。看到这些书名,就有把它们从书柜里面找出来翻一遍的亲切感。如《春风诗丛刊》第一辑《犾中诗专辑》、《大地杂志》等。《春风诗丛刊》第二辑是“美丽的稻穗——台湾少数民族神话与传说”,其中有报道少数民族作家莫那能的《阿能的故事》,想起曾翻看莫那能口述、吕正惠校订的《一个台湾原住民》的经历。再回想起“原住民”这个词系一九八四年杨渡他们参与所定的称呼。“我们所未曾料到的是,‘原住民’这名词后来竟成为专有名词,修改宪法、原住民基本法等都依此改变了。”(P96)命名而被承认,是对人能力最为直接的肯定。以至后来杨渡在小说集中《九天九夜》(南方家园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6年版)中,《玫瑰指环》一篇里借小说人物谢慕真之口,纠正自己说原住民是山地人的口误。
与作家陈映真、画家吴耀忠交谊非浅,同时也是杨渡朋友的台湾左翼作家施善继,在他前两年出的《毒苹果札记》(远景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4年版)中曾有一段话论及“左”的问题,他说到:“‘左’并不可怕,对‘左’的无知才可怕,缺‘左’对人体有害,如同缺‘钙’对人体有害。瞎了左眼剩下右眼,看见世上的物体都成了平面,偏偏为我们装义眼的眼科大夫搞错了,他弄一颗右翼属性的人造眼球,以至吾人脸上的两颗眼球右右顽癖,积重难返回天乏术。”(P373)缺左是否就是如同人缺钙,这当然不好证明,因为这只是个比喻,但观察问题的角度,一定有所阻碍则是必然的。
国民党戒严时期为反共,禁止左倾读物,对左倾人物也加以打压,杨渡说:“然而,对台湾文化来说,它还有一个救(大约应该是“致”之误——冉注)命的缺陷:由于长期的政治禁忌,所有左派的书全面禁止,台湾变成一个缺少‘左边眼睛’的社会。如同一个人,有左右双眼,才能维持平衡,对前方飞来的物体,才能有一种立体的空间感,判断远近距离。但台湾只有一个平面的世界观。那就是以美日为马首是瞻的、资本主义阵营的世界观。”(P101)这一说法与施善继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是朋友,或许应该早有如此共识。故《暗夜里的传灯人》所写的人物,严格说来没有写到比较右的自由主义者,大约与杨渡的交往圈子,以及八十年代台湾比较多的左派知识人,参与创办党外杂志有关。
杨渡与陈映真是1981年施善继介绍认识的,书中除了写到陈映真外,还写到他们共同的朋友、画家吴耀忠。同样施善继在《毒苹果札记》里也有不少篇幅写到陈映真、吴耀忠。陈、吴二人既是同案,被关了七年多,也是至交,当陈映真主编“诺贝尔文学奖”系列丛书时,便邀吴耀忠作封面。这套书我曾零本购得十来册,当时既没有注意封面为谁所画,也没太在意谁是主编,因为那时没读过陈映真的书,也不曾见过吴耀忠的画。
杨渡书里细致地描绘了吴耀忠为给陈映真小说集《山路》一书,画封面,找他做模特的事。“他想画一幅青年革命者,手中提着人头包袱,在风雨和血汙中,勇敢前行”(P257)。而施善继对此回忆道:“耀忠的《山路》,当年为陈映真小说集《山路》的出版而画,但当小说集问世时,人们看见的书封,却是耀忠的另一幅《山路》,而不是今天的观画者给第一幅《山路》另取的书名《提着头颅的革命者》。”(P340)大约是这个“提着头颅的革命者”过于敏感,被审查者拿下来之故吧。大陆所出林丽云著《寻画:吴耀忠的画作朋友与左翼精神》买回来了,尚未来得及读,不知是否有这样的细节?
岛内一些与威权时期的国民党政府抗争的人物,在台湾解严前后的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先后移居大陆。《暗夜里的传灯人》里所记录的,最著名的莫过于陈映真与黄顺兴。陈映真参加了大陆官方作协的一些活动,黄顺兴直接当上了全国人大常委。陈在北京做了些什么,杨渡的书并未细述,故不得而知。而黄顺兴把他在台湾的大炮性格带到大陆来,在人大会上公开喊出了“我反对”,而反对的则是著名的三峡工程。这样做了一回后,官方冷他,他也就知趣辞了算了。真正的左派,你如果到了大陆太适应,可能说明你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左派,或许只不过是能见风使舵罢了。
2017年1月30日至31日写就,同日改定于成都
这是第
248
篇文章
值班编辑 | 小窗
-END-
文章皆为作家原创作品
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欢迎将原文转发朋友圈
回复作家名字查看历史回顾
:
蒋方舟 费勇 李海鹏 慕容雪村
冉云飞 土家野夫 王小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