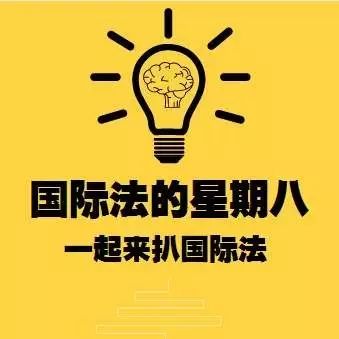年轻的时候,冈仓觉三受日本政府公派,到国外去研究欧美的艺术史和现代艺术运动。回来之后,他对亚洲艺术,尤其是日本艺术,有了更深的理解。
欧亚大陆之间的分割并不是亚洲民族所自然产生的想法。相反,它源于欧洲在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某种思维方式,是科学进步所带来的启蒙思想以及启蒙思想在社会秩序上的逐步应用所带来的历史产物。
当代欧亚对峙的局面与欧洲优越的科技水平密不可分。一些亚洲思想家,或像泰戈尔或贾拉尔·艾哈迈德(Jalal Ahmad)这样的辩论家甚至提出了
一个有趣的说法:这种对峙并不是亚洲人与欧洲人之间的,而是亚洲人和欧洲机器之间的。在欧洲优越的科技水平背后,是欧洲人对科学的新认识:自然界是能够被无限度(或几乎无限度)地改变的。从一开始,欧洲人就清楚地知道他们所建造的新文明的独特之处。整个十八世纪,大陆之间的比较作为一个意象,出现在几乎每一个图书馆或画廊。而欧洲经常被描绘成一个拿着地球仪的女人,被数学和科学仪器包围。
比如,在威尔茨堡住宅宫殿入口楼梯的天花板上,威尼斯艺术家吉安巴蒂斯塔·蒂皮罗(Giambattista Tiepolo)在中心描绘了阿波罗和奥林匹斯的其他神祗,然后沿着壁画的侧面描绘了当时已知的四大洲。
亚洲的形象坐在大象上,非洲的形象坐在骆驼上,美国的形象坐在鳄鱼上。只有欧洲的形象不是坐在动物上,而是坐在宝座上,被人类发明的产物——艺术、科学所包围。
欧洲人几乎能够控制整个世界,这是科学、经济生产和政治社会上的一系列革命的直接结果,其根本原因是他们对其他不同的、未知的可能性的系统性的探索。如果把权力看作是一种改造现实的能力,那么欧洲人已经发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变革的方法:欧洲是世界关系的中心,与此同时军事力量增长极快;欧洲的经济、文化,甚至是无形的国际声望,也在不断增长。因此,正如霍奇森所说,所有的民族都需调整其政府结构以适应现代欧洲的国际秩序,调整他们的经济以适应与工业化的欧洲之间的竞争,甚至调整他们现代科学观念。这一切都是科学所带来的,包括机器。
现代科学被视为在逻辑水平和方法层面上一个决定性的突破,而社会也被理解为在理性的基础上一个重新组织的过程。
在孟德斯鸠、亚当·斯密或黑格尔的作品中,亚洲大陆时常作为一个落后的、古老的、欧洲所摆脱的曾经的形象而出现。
亚洲社会时常被看做是一个落后的社会,自远古以来就一直停滞不前。正如黑格尔所说的,“世界的历史从东到西。欧洲是历史绝对的终点,亚洲是历史的开端。”当中国的历史开始时,世界的历史也就开始了,因为中国作为最古老的帝国,也是正如黑格尔所说,最新兴的帝国;一个排斥改变、默守陈规的地方,取代了我们所说的“真正的历史”。
正如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家汪晖所写的那样,欧亚之间的分裂具有许多鲜明的特点:亚洲政治帝国与欧洲民族国家的对立;农耕、游牧社会与城市社会的对立; 政治专制与追求个人自由、法律制度发达的对立。基于这些区别,欧亚也发展出了对科技发展的作用不同的观点。在欧洲拥抱科技的时候,亚洲却似乎注定要停滞发展,成为一个永恒“静止的大陆”。
Ahmet Hamdi Tanpınar的小说《休憩之心》,——一部关于伊斯坦布尔,一个同时坐落在欧洲和亚洲的城市——的主人公自言自语地说:
“东方是一个静坐和等待的地方”。在欧洲社会开始迅速转型,进入现代化进程的十七世纪,人们才开始频繁提到“欧洲”这个词,并非巧合。欧洲和亚洲不再是仅仅只是地理概念;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文明形式,代表着不同的历史时期。
但列宁不这么认为。他曾写道,俄国无疑是一个亚洲国家。对他而言,这与地理无关,而与在沙皇统治下的中世纪和“可耻的落后”的历史有关。现代性、资本主义或工业化原本都被看作是欧洲的,却能在全球扩张。十九世纪,“欧洲”一词逐渐被“西方”所取代,显然表明了其背后具有普遍吸引力的现代观念与旧社会的二元对立的象征意味。
这种反对意见是欧洲殖民主义的重要基础,但它也为那些认为亚洲能够拥抱现代性并加入发达国家集团的人们的观点建立了理论基础。这种观点从日本发端,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兴起。比如,福泽谕吉就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日本应该通过投身其中来避免西方文明的冲击,与它们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享受同样的文明成果。他将这种论断命名为“离开亚洲”——这也是他1885年3月发表的一篇社论的标题。
历史上的对立开辟了欧洲与亚洲、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鸿沟。如今,这两者之间的分裂是史无前例的,无论这种分裂是新兴的科学方法带来的,还是资本主义的进步所带来的。在现代欧洲之前,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亚洲社会所在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
吉卜林写道:“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它们永远不会相遇”。
然而,这种区别从一开始就是暂时性的。即使那些敢于宣称欧洲社会比亚洲社会更先进的人们也不得不承认,基于这种衡量标准,亚洲能够通过科学和工业革命、学习借鉴科学基本方法和原则而及时赶上。历史的发展有一个简单而奇特的结构:从欧洲先开始,然后再扩大到其他地方。当然,没有任何融合理论可以反驳吉卜林,因为他的想法正是:只有在亚洲开始变得越来越像欧洲之后,东方和西方才能相遇。
这些见解反映出了问题的严重程度。我们再也不能说,欧洲和亚洲之间的区别仅仅只是文化形式上的差异。现在,这两大洲似乎存在于不同的平面之上。当这两个平面相交时,就带来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关于现代生活的意义,关于我们来自何方,又将往何处去。
欧洲人对待亚洲的态度有一定的矛盾。一方面,亚洲似乎代表了现代性所对立的一切,像是欧洲在自我界定时所参照的反面形象。另一方面,欧洲人又对亚洲充满好奇和向往。更加具有反思性的人们可能会将亚洲视为一种遗迹,代表着那些欧洲所遗失的,真实鲜活的场景,令人反思:最初选择现代性是否可能是一个错误。
作为一位长期居住在北京的英国人,朱丽叶·布雷顿在1922年写道:“欧洲游客可以在中国回忆起那些比如今更加奇异和迷人的昨日,那时还没有工厂或铁路,去惊扰亚洲梦幻般的平静。”不过,这样的反思只能被轻声低语,默默欣赏,并且即使这样,也仍然可能会被另一种焦虑的情绪所抵制:如果欧洲是在过去的某个时候从亚洲脱离出来,那是否意味着,它会再次失去被定义的自我,就像德国哲学家卡斯·雅斯贝斯(Karl Jaspers)所说的那样, 再次“沉入”亚洲?
欧洲从亚洲出走,或许象征了一种大胆和解放,但也带来了两个危险。首先,欧洲人的生活与其起源脱离。其次,欧洲回归亚洲的危险将持续存在。大陆之间的再结合成了一个恐怖的幽灵,一旦发生就可能会彻底摧毁欧洲的独特性,而亚洲则会将自己视作是一个永恒的世界,将欧洲吞并,并在欧洲消灭之后继续存在。当然,从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的故事走向来看,这将会是一个峰回路转的结局。另一方面,如果亚洲像欧洲一样朝现代化发展,就表明,现代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条普遍道路。历史地来看,大陆之间的关系是解释现代历史的密码,一旦我们理解了,很多事情就会昭然若揭。就像雅斯帕斯说的那样,“欧亚大陆是伴随整个西方历史而来的密码”。
两大洲之间的分离集中于对政治和文化的理解上,却仍然是未经审视的。每个人都认为这种区分是理所当然的,却又没有人能够阐明它所依据的理由。当作家赫尔曼·冯克瑟面对在多大程度上存在欧洲的问题时,他在某种“风格统一”中找到了答案。他敏锐地意识到,一种与东方相区别的、崭新的欧洲风格。
什么是“风格统一”?是科学和技术被视作欧洲原始和本土体验的一部分,因此可以被更充分地接受,而不会被视作是一种入侵,就像宗教在印度进入各个活动领域,出现在食物、饮料、服装、娱乐、家政和生活的所有主要场合一样。这意味着,科学不仅在欧洲现代社会占据着中心,其原始精神也不断激励和引导着每一个活动。
赫尔曼﹒凯泽林 (1880–1946) 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旅行家之一,
因为他明白,旅行意味着创造新的体验世界,并使我们超越想象。他希望把自己放在这样的环境里,尝试去理解,从而改变他所固有的理解范畴。“欧洲不能给我带来什么。它的生活太熟悉了,并不要求我做出任何新的改变。它的生活也太狭隘了,整个欧洲基本上是一种精神。我希望去那些能够要求我去以另外一种全然不同的姿态生活的地方,那些必须要彻底更新一个人感知事物的方式之后才能理解的地方,那些我被迫需要尽可能多地忘记目前为止我所知道的地方。”
当从欧洲过境到印度时,他经历了这样的变化。印度思想似乎站在西方思想的对立面上,认为没有任何形式的抽象可以帮助人们获得形而上学的知识。为了迈入更高的层面,人们需要获得新的更深层次的意识状态。西方思想的抽象层次从低到高,从特别概念到一般概念,从这些概念到思想,从思想到关系;而印度思想则跨越了不同的体验。凯泽林在印度看到的是灵魂从低级到高级形式的提升。在西方,这种提升则表现为从具体描述到抽象形式的思想。“印度对西方的绝对优势取决于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即,在真正意义上,文化是通过提高深度来实现的,而非扩大广度 。而且,这种提高还取决于文化的集中程度。”毕竟,瑜伽系统完全是由集中的力量构建而成的,这看似与抽象的力量完全相反。完美的瑜珈师应该把他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一点上,然后他就可以知道关于这个点的一切。相比之下,抽象化则是试图从尽可能多的对象中得出一些总体思想或原则。
今天的旅行者们不再会有这样的感觉了。问一问你自己:当你降落在一座位于某个神秘边境的另一边的城市,你是否会发现一些根本性的不同——并不是列出一堆看起来不一样的事情,而是那种本质上的区别。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将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尽管根据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会存在着一些发展上的差异,但现代化本身已经成为一个普遍或接近普遍的方案。
当过去被视作不可改变、意义非凡的自然秩序也能够被不断地操纵、改造时,现代社会就出现了。这就是现代的科技精神,将自然改造成新的形式和结构,带来了那些意想不到的新事物,既使得人类的生活更加愉快,也更接近了那永恒不变的宇宙核心。科学进步仰赖于对持续创新的期待,对试验创新的鼓励,对既定的权威的否定,基于一种假定:创新的试验会带来创新的现实,迫使我们修正原来的知识。
现代人们发展出他们自己的个性,就像城市规划师为一座全新的城市创造地标。一切都是空白,等待着人们去填充各种各样的内容,而这些内容总是与这个组织原则相关,从这个原则中衍生出来。这些是生命对世界的保证;或者,用一种更好的说法,是生命对世界保证,它将变得不同于当下。而现在,
环顾四周,现代生活已经无处不在:现代城市的街道,摩天大楼的外墙,智能手机的像素化屏幕,电脑内部的电路,报纸和杂志的封面,商业计划和组织的电子表格,远洋的集装箱运货船。而这背后的原因,当然是因为现代生活就是一个自由空间,其中的内容不断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