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史嘉柏(David Schaberg)
翻译:张瀚墨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
ohistory
点击此处阅读本文的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请见东方历史评论今日推送的第一条消息。
关于第十三章《前帝国时代的中国北方边疆》
第十三章是狄宇宙(NicolaDiCosmo)的《前帝国时代的中国北方边疆》。在这一章,狄宇宙通过在不同部份对其讨论的每个历史时期的考古和文献两组不同数据进行区分对待,恰到好处地处理了考古发现与文献证据不一致的问题。他认为,关于汉人和他们北方邻居的联系与冲突最早出现的历史记载,“往好了说,是模棱两可”。他说:
近来的考古工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参考框架,通过这个框架,我们可以追溯北方地区从商到战国时期的文化发展。尽管应该抵制以传统历史资料来包装考古发现的诱惑,尽管文献记载与物质资料的不对称为迥异的解释留下了空间,北方文化发展作为一种广泛的文化现象,其大致轮廓已不再像从前那样模糊了。(原文第887页)
基于此,狄宇宙没有把目标放在根据现有史料编写一部连续的北方地区历史叙事上——就像他在同一页提到的那样,那种编写历史叙事的做法事实上也不被考古证据所支持——而是在现有证据许可的前提下,尽可能准确地着手回答以下问题:“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匈奴草原帝国是如何诞生的呢?”(原文第887页)以此设计本章,狄宇宙就避免了目的论的观点,拒绝像别的学者那样使用“原始的匈奴”这一名称(原文第891页),将目光聚焦于这一草原帝国仅仅是因为它在战国晚期成为支配中国北方的主要力量。
本章的第一个重要部份,“北方文化分期”,总览了其后本章其他部份即将涉及的历史时期。该小节大致上以物质遗存为依据,当然也尽可能地参考了传世文献所提供的社会经济因素和证据(原文第889页),将这段历史分成四期:第一期,公元前两千纪,还未形成游牧部落的牧区时期;第二期,约公元前1000到公元前650年,北方“贵族武士精英”以及独特冶炼技术的出现时期;第三期,公元前650到公元前350年,游牧业的成熟期;第四期,从公元前350到公元前209年,该时期的巅峰期即是强大匈奴帝国的创立(原文第889~893页)。在关于文献证据的问题这一点上,最有启发性的莫过于狄宇宙在论述公元前650到公元前350年这一时期时的一个观察;他认为:“中国边疆地区[农牧业]混合考古遗迹的存在,与传世文献里跟骑马牧者有关的信息的缺失,很可能在暗示,这些由牧人和农民混居的社群充当了中原与游牧草原之间的缓冲地带。”(原文第892页)也就是说,他所考察的考古信息澄清了史料的社会背景,并有助于解释传世史料在某些问题上的沉默。
在此章剩下的部份里,狄宇宙对所有四个时期的考古发现都进行了检视,系统地涵盖了北方地带逐渐扩张的所有地区,并在每一个时期都加进了关于传世文献见证的注释。他详述了北方地带独特的青铜器皿(原文第893~896页),讨论了战车的起源(原文第903~905页),解释了影响中亚及北方草原向游牧生活过渡的诸多因素(原文第909~911,924~926页),并严格区分了史书里提到的戎狄和更远游牧族群的不同(原文第948~951页)。联系到匈奴的崛起,他认为:“所谓的前匈奴文化……应被视为不同中心地区的共时性演进,而在这些中心地区,游牧贵族制或者通过迁徙或者通过内部演化得以确立。”(原文第937页)他让我们注意到贵族制的发展:贵族制不但通过青铜器(尤其是跟战车与马匹有关的青铜器)来表现其地位,而且维系着跟中国合作伙伴在政治上、外交上以及商业上的联系(原文959~960页)。处理传世文献时,狄宇宙一般来说强调它们的不足,极少仅靠传世文献证据来立论,并经常指出史料所称与考古发现的不同之处。尽管这种方法部份上取决于关于北方地带文献证据的稀少,但再多的文献资料也难以让人忽略差异或者夸大确证。从本章将依据考古和依据文献得出的观点并列检视的意义上说,狄宇宙对边疆地区的处理成了《剑桥中国古代史》的缩影;但从其侧重揭示文献文物的疑点和偏见而言,他的处理又胜出了《剑桥中国古代史》。
关于第十四章《留给帝国的遗产》
最后,为《剑桥中国古代史》收尾的任务落在了鲁惟一的肩头。为此,他在《留给帝国的遗产》(也就是本书的第十四章)中,罗列了一系列的评论和感想。如果我们把《剑桥中国古代史》比作一场早期中国研究学者的聚会的话,鲁惟一这一章就好像是晚饭后的主题讲演。鲁惟一的大量学术著述,既运用考古证据也使用主要历史文献,涵盖了汉代历史的方方面面,这使他成为独特的人选,有资格将汉代政治文化发展与其前代联系起来,并来填补先秦时期通常来说是模糊的历史与《剑桥中国史》里涵盖的确知的“历史”领域之间的空白;而《剑桥中国史》正是始于杜希德(DenisC.Twitchett)和鲁惟一合编的秦汉卷。当然,他的这一章没有展现严格的论证,而只是对于最重要的延续性的领域的松散的评论。
在第一部份,也就是“帝国的建立及其危害”一节,鲁惟一讨论了汉代统治者是如何采用周制、秦制及其他战国政体制度的。“过去的教训”一节包含了对史料的小心处理;像《剑桥中国古代史》里其他少有的几位作者那样,他强调说,传到我们手上被称作历史的材料中,有一大部份是基于轶闻途说,很多是口头流传的,其准确性大都经不起推敲(原文第971~973页)。在这一小节他还考虑了“战国”一词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起源、对于过去的观点的形成、以及一般认为的汉代史学家不讲因果关系的特点等。“宗教仪式”一节重拾陆威仪一章最后部份的主题,将重点放在祭天、祭山、以及对远离都城的其他地点的祭祀上。在“诸子学说”部份,鲁惟一谈到了儒家的幸运,但强调在统治哲学上的儒道互补;他还拿出部份篇幅介绍了黄老好刑名思想。在“王权传统”部份,他认为君权与责任并糅的观念在汉代得以缓慢地发展。“一统的观念”部份跟陆威仪和狄宇宙的讨论都有交叉,主要讨论了“中国”一词以及用于其他族群的各种称呼、中原诸国居民所感觉到的与文化意义上的外族相区别的观念、以及神话传说和文献记载里对于世界结构的主张。同样,“制度规范与行政实践”一节也涵盖了《剑桥中国古代史》里的其他作者涉及到的材料;在此,鲁惟一讨论了法律准则的产生,汉代对秦行政实践的采用,档案(尤其是历法和人口土地登记)的使用及类型以及对官僚、军事和经济实施控制的标准。在“城市、宫殿、王家祠堂与坟墓”中,鲁惟一审视了展示宫殿以及其他权利中心特征的建筑工程。本章的结尾,鲁惟一提到了一个汉代及其以后的朝代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也就是能否找到“严格的、有节制的政府模式与人文伦理价值关怀的可行的平衡”的问题;对他而言,汉代对王与天的关联的再肯定,以及附带的对于任人唯贤思想的正式承诺,即使不总能保证这一平衡的达成,也使其成为可能(原文第1031~1032页)。
尽管鲁惟一这一章在很多方面都是这一历史时期的桥梁纽带,但作为《剑桥中国古代史》的结论却稍嫌欠缺,这可能是因为这一章从一开始就没有指望成为该书的总结。像该书里的其他作者一样(尽管更没有理由),鲁惟一极少提到其他章节,尽管对于遗产的讨论原本会从广泛的参照互检中直接受益。这一章主要依赖传世文献,绝大部份篇幅里将考古证据置于边缘,并以此在一部将正在历史、考古和其他学科之间进行的对话戏剧化了的著作里,给予了“传统史学”最后的话语权。最后。尽管鲁惟一将前帝国和帝国时期清晰地系连,他错过了一个对本书前言以及通篇都提及的学科问题作出结论的机会。
早期中国研究的三个问题
确切地说,对于早期中国的讨论可能应适当地提及三个问题。第一,《剑桥中国古代史》的题目及其内容里所谓的“中国”指的到底是什么?本书的作者们在使用“中国”一词时是不是基于共同的概念基础?第二,先秦时期的什么东西(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使其与秦、汉以及之后的时期明显区别开来?②它是不是主要关于从分裂到帝国的过渡?它是不是更多地跟这两个时期的史学家们使用的材料有关,即考古发现的文献资料对早期中国史学家而言地位更重要,而历朝历代的历史对于研究帝国时期的学者来说更有发言权?第三,如果像本书编者在简介中所说,前帝国时期主张用多学科的方法进行研究(原文第13页),那么《剑桥中国古代史》作为学科实验的结果又是什么呢?对照之前我对本书各章的评论,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书中所包含的章节,简单来说,并非是互补的。“凡例”中的注脚里提到的“阐释与方法的不同”(原文第xxiv页)在《剑桥中国古代史》中比比皆是,让人觉得不同的学科——尤其是“传统史学”和考古学——往往是损害而不是加强了彼此的学科基础。就像我在前文指出的那样,贝格利对恪守文本者偏见的批评,从不少传统史家和考古学家那里均得到某种形式的赞同(大部份是默默地赞同);这种批评认为,早期文献资料大都不能被简单地看成可靠证据,相反,它们反映的只是其作者或编者对于过去的认识,而我们对文本本身却知之甚少;这事实上使传统史学处于防守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把文献资料放在具体背景下来考虑,如果对其不经证实就加以使用,文献所提到的表面价值很可能根本上就没有价值。
《剑桥中国古代史》里,对“中国”一词的定义要么侧重实用主义,要么令人困惑不解。事实上,任何国家或民族的名称都指示了某种长期存在的地理、文化、语言事实,同时也意味着基于这些不同事实而产生的某种本质的延续性的存在。对于一个民族名字的最有激情、最有影响力的祈用通常不会让人注意到地区和地区之间、群体和群体之间、以及个人和个人之间的细微差别。为了能经得起严格检验,国家或民族名字的最保险的使用方法是,要么在对其进行严格的定义之后再使用,要么干脆避免使用,而代之以最能体现其相对独特的延续性特征的名词。《剑桥中国古代史》的大多数作者采用了以下方式来对待这一问题:即大家使用“中国”一词,仅仅因为这样做便于指称古时候的这片地理区域,尽管那时候住在那里的民众构成成分很复杂。当然,也有少数学者在解释证据的时候拒绝搬用后来的关于中国认同的看法。在这一点上,《剑桥中国古代史》的两位主编试图做到不偏不倚:
毋庸讳言,我们必须看到早期中国文化多样性的存在,这些文化因时因地而异,其界限也有待于研究。但对于这种文化多样性的认识,并不能分散我们对于中国文化奇妙之处的关注,在我们看来,它恰恰加强了我们对中国文化的关注,也增强了中国文化历史的丰富性。(原文第13页)
因为《剑桥中国古代史》导言中没有提供对“中国”一词的地理或其他意义上的定义,上文所引两位主编的意见,事实上将发生在这个地区的各种各样的古代文明都总括成某种历时性的大一统,而这种大一统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即使的确存在过,作为一个科学概念也属不确定值。
《剑桥中国古代史》里的好几位作者是从系谱学的意义上谈到“中国”和“中国人”的;当后来被公认为是具有独特的“中国”特征的现象在古代制度中得以预见的时候,他们就会使用“中国”或“中国人”这样的词汇。这样的用法,如果从语言使用的角度看,相对而言没什么问题,因为保留下来的文献显示出这种用法的延续性,而这种延续性也适合定义一种语言的语言学标准。但在其他情况下,“中国”和“中国人”这样的词语跟真正的内容很少有关,或者根本就无关,其主要作用就是表明文化的延续性。经常是,当不同的作者寻求将他们所研究的时期和材料荣列于第一的时候,没有经过严格定义的“中国”就被说成是从此开始形成了:
只有那时[一万年前],人们才开始意识到,在这一地区有一个将来会被称作中国的独特的文明。(原文第37页)
确凿地说,这些[周代的]经典里的某些或者很多观念,在商代甚或更早的夏代和新石器时代就已经被预见到了。但是,如果说更早的时期可以被说成是中国历史的创建期(这一基础尽管是必须的,但在大部份的时间里却是以潜伏的、看不见的方式),那么,可以肯定地说,西周必须要被当成其中最重要的部份。(原文第351页)
这一时期[春秋时期]最重要的发展,是思想史层面的重要突破;在这一层面,孔子道德价值提供了封建伦理的全新阐释……春秋时期开始的这一思想突破将最终引领中国发展出持久的集体认同,即中国文明。(原文第545页)
在有些地方“,中国”和“中国人”这样的概念在那时就已经莫名其妙地存在了:
这里的讨论,将集中在中国本土同质的艺术和建筑传统的基本发展、重要特征以及地区差异,而不会涉及边境地区发现的、通常是表示外来文化认同的艺术和建筑形式。(原文第653页)
此时此地的世界,像一个6世纪晚期的中国人将会看到的那样,正是我们称作中国的北边的那一半……生活在边疆的人们不遵循中国的风习和臣道;这些人被看成是外国人,零星地散布在整个国家。(原文第747页)
很明显,在所有以上提及的语境中,“中国”或“中国人”这样的词语,只是作为非常模糊的概念被援引。只有非常宽容的学科才会允许如此宽泛地使用这样基本的词汇。
另外一些作者,在他们的章节里讨论商周贵族内部的特殊文化发展,而这些发展为后来的共有的中国文化认同准备了道路。尽管有人可能会问,吉德炜在说“最初阶段的中国文明”(原文第232页)时认为其中究竟有多少文化延续性,但我们必须同意,他所指的政治、宗教和艺术实践,对于后来意义上的一统的形成是有帮助的。罗森在讨论西周的时候也指出,西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刻,这一时刻既见证了对于统治者所扮演角色的那些看法的形成,也见证了便携的社会器皿被用来为这种观点进行宣传”(原文第449页);但她清楚地指出,她在这里使用的“中国”指的是“中国大陆”,也就是西周贵族宣扬其思想以便于消除认同差异的地方。罗泰指出,周礼被用来区分采用和不采用它们的不同群体;这种区分,更具体地说用来“对中国人(自称周、夏或者华夏)和野蛮人进行对比”(原文第544页),还会在后来继续被用来表明对中国的认同。鲁惟一的那一章做了一件非常有用的事,那就是对跟早期中国相关的很多语汇进行了检视(原文第992~995页),并讨论了中国大陆上导致大一统观念形成的诸多因素,但其结论却又不无怀疑:“试问,前帝国时代中国村庄和城市的居民是从何种意义上——如果果真如此的话——愿意宣称跟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其他居民是兄弟关系。”(原文第1002页)事实上,以上这些作者是在表示,“上古中国史”的观点并非是在寻找本质上属于中国的东西的最早表现形式,而是意在表明那种独特的、持久的中国认同的观念是如何在某时某地获得了动力。
现在来讨论前面提出的第二和第三个问题。考虑到先秦历史研究的独特性和多学科方法的影响,我们可能会再一次回想起吉德炜那一章开头所讲的,其中有提到晚商甲骨作为“真正历史”的起始和“初期中国”文明的文物的话(原文第232页)。出现在贝格利具有强烈批判性的那一章之后,吉德炜的一章意义重大,远超过它所包含的丰富的内容本身;这一章应该被当作是对史学方法的辩护和史学研究的典范来读。正像我在评介这一章的时候指出的那样,吉德炜在写作这一章的时候,既在开始就指出了其证据的局限,又在后来指出根据这种证据所得出的结论的局限。他的方法所体现的原则是研究其他主题和时期的史学家们所共用的:那就是,要小心求证,不要希望文献里的那些公然的断言是真实发生的,而是要知道,不管怎样,那些文献不过是它们所属时代的反映和遗迹。
这一原则与史前和历史时期之区分的相关性,以及更概括地说与《剑桥中国古代史》所包含的整个时期之历史地位的相关性,也能在罗宾•科灵伍德(R.G.Collingwood)的某些评论中捕捉到。在其1926年之《历史哲学讲座》中,科灵伍德一开始是拒绝历史和史前时期之间的区分的,但之后他又认为这种区分自有其道理。“从这一区分的观点看来”,他写道:
历史时期跟书面材料相连,而史前时期则不具备这样的资料。在这种观点看来,合理地完整而准确的叙事,只有当我们占有可据以写成历史叙事的书面材料时,才得以被建构起来;而如果没有这样的书面资料,我们只能将一堆模糊无据的猜测松松垮垮地拼凑在一起。这种观点是完全不正确的。书面材料并不像这里讲的那样,可以独享可信与翔实的美誉;而且,几乎也没有什么不能通过非书面证据来解决的问题。
但从另一方面,科灵伍德又认为,这种划分从史学家的教育角度而言又的确有价值,他说:
如果我们从一个史学家成长过程的某一点、而不是从他的观点和未来的他的角度来考虑,如果我们从一个刚参加历史工作的史学家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对他——而且只对他——而言,确实存在着未加工的史料(包括契约和执照、毁弃的建筑、钱币和陶片等)和化简了的历史材料(即已经写好了历史叙事)之间的区别。二者的不同在于,简化了的材料已经被整理成跟他正在试图把这些材料转化成的东西一致的东西,而未加工过的材料则要求他去做此时他还很难胜任的工作。
这也就是说,刚参加历史工作的史学家,还弄不懂文物,只能先从简单的史料开始,然后才能越过它们,得以理解未加工过的材料(应当指出,其中也包括书面文本)。就像科灵伍德接下来写的那样(与黑格尔哲学一脉相承)“,这种错误是通往真理的必经阶段”。
我们可以把上文的“史学家”换成“早期中国史的书写”。诚然,从科灵伍德的时代到如今,人们写过很多关于历史叙事和数据之间的关系的东西,以及关于某一个历史学家的历史叙事跟他或她的前辈建议的历史叙事之间的关系的东西。很多时下的史学理论家倾向于不提通向真理的过程,而是谈论真理的连续表述,而真理也要适应史学家赖以工作的正在变化的历史、文化和学科条件。但科灵伍德的观察也可看作是直接针对研究早期中国的史学家所面临的问题的:事实上,研究早期中国的史学家当下考虑的应该是学科内的而不是超学科的问题。在科灵伍德看来,上个世纪发现的大量的新的考古学证据所带来的影响,大到可以消除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界线的地步。过去的学者不得不主要依赖晚期文献简化了的叙事——比如《史记》——来说事儿,但现在必须要把这样的叙事放进由近期发现的更原始、更直接的证据组成的材料中来考虑。进一步说,只要是考古学成功地将先前的权威文本变成或多或少可疑的文本文物,过去可能被看做是历史时期的东西现在就呈现出史前时期的特征。
尽管有吉德炜和《剑桥中国古代史》其他一些学者作榜样(他们全部都得对传统史料的有用性作出判定),整体看来,正是古代的权威文献的问题,使得《剑桥中国古代史》成为早期中国历史研究学科内的本质上的不一致性的见证。即使在《剑桥中国古代史》作者群内更小的组群里,在如何使用传世文献这一点上仍然存在着基本的不同,更别说对于诸如判定特定文献的年代及可靠性这样更具体的问题;这就导致,即使经过了彻底修改,那些单个的章节合在一起也难能形成统一的、连贯的记述。当然,能够产生此类统一的、连贯的记述的概念上的可能性——即使这一记述会立刻被指责为歪曲和刻意同化材料——是学科内在连贯性的标志之一: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学者和另外一个学者不仅在材料的接受上产生分歧,而且在利用材料得出结论的方法方面也不能同意对方的话,那他们肯定难能写出互补性的作品。这种情况下,有必要认为他们研究的是不同的主题,属于不同的研究领域,甚至属于不同的学科。换一种说法,如果在使用材料的框架方面没有公开的讨论,缺少内在的一致性,那么史学家的写作就会彼此误解,就难以形成确定的、正式的渠道质疑彼此的结论。
《剑桥中国古代史》就是这样一本书,从这个角度而言,它代表了整个早期中国研究领域的现状。像《剑桥中国古代史》里的作者一样,别的早期中国研究学者——或称作史学家——的论证(出色与否视情况而定),很少触及如何在使用证据方面保持一般一致性的问题。但是让人欣慰的是,这种学科性的散漫并不是建立在某个国家学术研究的传统之上:作为独特的群体,从事中国研究的中国史学家和从事中国研究的西方史学家表现出同样的学科多样性,而且,在传世文献的问题上,这两个群体同样既包括自由思想家,也包括几乎原教旨主义者。这种区分也说明,史学方法上的诸多分歧,并非由于国别的不同,而是基于不同的信念,尤其是学者们对于传世早期文献的不同信念。一种极端认为,传世文献以及流传下来的对它们的解释(比如《史记》或《书》的章节以及后来的序言对其具体语境的猜测),如果不能证明有误,就一定是可靠的;而且,通过改述、概述、或直接引用,那些记载可以未经修改地拿来用书写现在的历史。正如科灵伍德所言,传世的文献已经被被加工成当今史学家想要产生的同质的东西。
另一种极端认为(这里我得承认自己对这一极端的认同),传世文献并非完全可靠,不应被当成历史权威直接引用,除非能证明这些文献源于可能而且令人满意地产生对于历史言行的高度准确记载的历史环境下。进一步说,某种文体(比如在任命和盟约中,书写被用来记录具有约束力的准法律性语言)可能会被证明符合产生精确史料的条件,但这绝不能被理解成证明精确性在这些文献中成为准则的证据,这就像司马迁对君王纪年明显准确的记载并不能保证关于刘邦母亲怀孕的神话传说是真实发生的一样。历史以及准历史性的轶闻是为其使用者服务的,而准确性只能缘于将那种松散的、娱乐的、利己的谎言拒于门外的共同一致的努力。我怀疑那种关于早期记述可靠性的信念,可能长时间或永远得不到任何关于这些文献出处的令人信服的记述的证实,那种类似于吉德炜所采用的方法(即文本被看成是文物而不是历史权威)将永远有利于更有说服力、更持久的历史重建。不管怎么说,我所指出的那种以信与疑之间的冲突为特征的方法上的不同,在早期中国研究领域是如此基本、而分歧是如此之深,它可以被用来解释早期中国史所承认的方法上的巨大的多样性;面对这样无法解决的学科问题,学者们难免会对确立更严格的、共同的史学实践感到绝望。
《剑桥中国古代史》所覆盖的内容截止到战国时期,只是在鲁惟一关于遗产的评论中我们才可以找到几点跟帝国时期有关的联系。根据科灵伍德对于历史时期和史前时期的划分,或者更恰当地说是对于简化了的和未经加工的材料的划分,我们应该指出,将上古中国(《剑桥中国古代史》涵盖的范围)和帝国时期的中国(多卷本《剑桥中国历史》所涵盖的范围)区分开的与其说是帝国的到来,还不如说帝国历史文本--具体地说是朝代史--的到来。由于其结构以及其中司马迁的自传,《史记》就变成某种自证的材料,甚至考虑到其自身所包含的矛盾以及其对轶闻材料的依赖性时也是这样。当《史记》与班固的记载了很多相同的汉代资料的《汉书》结合,它确实标志着历史材料方面的至关重要的、质的变化。而对于更早的时期,我们根据考古和文献所能做到的,也不过是编写一系列片段的历史以及有限的一般性记述,因为这些证据尚不足以用来编写更完整、更具体的上古史。从另一方面说,《史记》以及之后的朝代史的长篇巨制给人以无所不包的印象,它们所开创的叙事结构持续主宰着史学家对帝国历史的重建。
最后,我想说,“历史时期”和“史前时期”都有彼此学习的地方。将帝国时期之前的文本看成是出自某种像朝代史那样竭力构建的统一而连贯的背景下的产物是一个错误,因为这种连贯性,作为历史文化的成就,在汉代之前是不存在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有理由干脆承认,从战国时期传下来的文字记载在很多时候难免有矛盾混乱之处。同时,大量接受关于帝国时期的朝代史记载,就好像其全面性可以保证那些记载能够满足我们自己的史学要求,这将导致——用科灵伍德的话来说——囚禁历史的发展。即使对于汉朝,或者汉以后的历史时期,历史的编写很难离开考古发现和证据以及其他的学科独立发展,因为没有这些证据历史就无法检验其对文献的依赖。因此,《剑桥中国古代史》中这种考古学和传统史学的对立,应引起我们对早期中国研究领域当下习惯的学科连贯性的质疑。当然,本书中所显示的方法上的并列以及在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方面的无能为力,也构成了迈向中国整个历史研究真正的多学科方法的第一步。
勘误
编制勘误表向来被视为褒扬重要史学著作的一种方式。我提交下面的并不完全的勘误表,意在希望本书在未来的岁月里会被继续使用和批评。跟传统的做法一致,我既标出了小错,也列出了那些更大一点儿的问题。我在有关考古学的章节里发现的问题相对较少,这似乎反映出那些章节的作者的负责精神,但也可能部份是我在此领域所受教育不完善的结果。
本书的两位主编坦言,他们不得不忽略上古中国史的若干方面;因为有的题目太专业,有的则是在现有的证据中缺乏支持,所以那些方面不会在本书中论及(原文第18页)。除了他们提及的那些省略,还有几个其他的方面人们期待应包含在这样一部著作中。《剑桥中国古代史》里不见有系统的亲属称谓和系统,没有职官表,没有对于职官的标准翻译,也没有关于不同作者对职官翻译的一贯指引。另外一个奇怪的现像是,北方包括了若干在中国历史上很长时间内不属于中国的地区,但本书包含专门写北方的一章;相比而言,南部和西南地区自汉以来就属于中国,但本书却没有相应的章节来处理。作为一部标准的参考书,《剑桥中国古代史》原本可以得益于一个本书所有作者都应参考使用的关于重要传世文献标准版本的书目,但是本书没有包括;类似的书目可以在陆威仪的《早期中国书写与权威》中找到。另外,作为一部参考书,本书是有用性也因缺少关于学者的索引多少打了些折扣。尽管某些重要学者的名字确实出现在索引中,但不细心的读者可能只会注意到郭沫若的作品被引用,而杨宽的却没有;同样,他可能还会错误地认为林巳奈夫的作品只在第七章被引用,而不见于别处。在理想的情况下,一部索引完整的《剑桥中国古代史》,除了一般索引和学者索引以外,还应该包括一张所引用或翻译的传世文献段落清单。如果只看本书关于《左传》的索引,粗心的读者会以为第八章只提到《左传》三次,只会是意外地发现原来这一章几乎是完全地建立在对于《左传》内容的改述和概述的基础之上。
不但在这里,我在前面的评论中也提到,《剑桥中国古代史》里的索引没有尽可能地做到参照互检,这在本书凡例的一个注脚中也提到(原文第xxiv页)。证据显示,本书的索引是集合了单个章节的标志词,而每一章的标志词都是由该章作者或其助手在没有严格指导的情况下完成的。这种做法或许是可行的,但必须要有更严格的标准,必须要对结果进行彻底的检查。否则,一个在书中的不同部份套用了不同标准的索引,严格地说根本就不算是索引。尽管有些章节的索引比别的章节做得要好,但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任何一位想认真使用本书的读者都不得不对现有的索引做出补充和更正。有几个低级错误应该立刻得到更正:书中第1138页的“Shu Liangge”和“Shu Lianghe”应该在一起,因为索引指出他们指的是同一个人,即被公认是孔子的父亲;即使不回答这个名字应该怎么读、应该做何分析之类的棘手问题,一个参照互检(即“‘Shu Liangge’: see ‘Shu Lianghe’”)就会对读者带来便利。同样,第1123页的“Guan Jingzhong”和“Guan Zhong”也应该放在一起,而且或许应该提示读者参照同页的“Guanzi”词条。还有,第1134页的“Qi Hou”应跟“Qi Huan Gong”一条链接或放在一起,因为他们指的是同一人。第1137页的“shi (Knight; manofservice, officer)”,也就是shi士,竟然不负责任地在最后把倪德伟一章讨论的shi“势”也包括进来。第1142页的“Wei”(即“魏”)一条包含了第347页和第560页两个参考索引,这是错误的,这两个参考索引应当移至同页的“Wey”(即“卫”)条下。第1142页的“Yu(state)”一条将三个不同的国名混在一起了;应该将其分成不同的三条,即“Yu盂”(出现在第307页)、“Yu”(出现在第369、394~395、397~400、428、430~431页)、“Yu鄅”(出现在第502~503、509页)。索引中别的不准确之处,多数是省略的错误,因为太多而无暇在此提及。
现在我们转向本书具体的章节。首先,导言部份没有明说要不要标出重要人物的生卒年月;安特生(J.G. Sndersson)(1874-1960)的生卒年应该却没有标出(原文第4页)。《论语》不能被称作是“哲学论文”(原文第7页),这样来描述《论语》必定会误导那些中国研究之外的读者。另外,春秋时期铁器不太可能“得到广泛的使用”(原文第16页),关于这一点,参考下面对第八章的相关评论。还有,最近对于“百家”的含义的研究表明,将其翻译成“百个哲学家派别(‘Hundred Schools’ of philosophers)”(原文第16页)在程度上过于夸大了思想家群体所能有的连续性和组织性。
第一章。首先,更新的关于跨地区假说的陈述表明,本章所提“[人类进化的]跨地区模式……认为在旧大陆的多个地区存在着从直人到智人的平行进化”(原文第41页)这一说法不确。跨地区假说的支持者在解释他们观点的时候,明确否认了“平行进化”的观点。另外,“公元前5000年前后中国主要区域文化”(原文第49页)的地图虽然不可或缺,但就像在本书许多其他的视觉示意图中所看到的那样,读者希望这张地图也能提供那些地名的汉字;而且,前面已经提到,地图上所示的大龙潭地区,虽然用阴影标出,不知为什么却没有在相随的文字里提及。还有,本章关于书写的一段是这样开始的:“传统中国史学具有世界上最长的连续的史学传统,从书写开始的时候就开始了。但是,书写并非在所有的地方都能保留下来,结果,中国的那些文献记载保留最多的地区,就无可避免地比那些文献资料发现稀少或者根本就没有发现的地区要显得更重要。”(原文第55页)这段文字不仅错误地认为中国现在所有地区同时使用书写,而且不正确地指出中国的历史书写像甲骨文一样古老,或者比甲骨文还有更古老。事实上,中国的历史编纂,严格来说,不早于战国时期,而读写能力的普及则是更近的事。最后,将神话时代划分为三个时期(即三个分别为神、半人半神、传说君王所主宰的时期(原文第65~71页)),使得中国的神话时代成为希腊宗教的平行产物,但这也造成了使用中国神话证据时的矛盾和困惑。
第二章。那种认为“命”字里的“口”为破音字而“令”字表音的说法,并不能百分之百地解释金文中“命”字和“令”字的几乎互用的现象。对于二字之间联系的其他解释应将注意力放在其所代表词语的形态学特征上。
第三章。地名Xin’gan既被写成“新淦”(原文第135页;对照原文第14页)又被写成“新干”(原文第171页;对照原文第404页)。按规矩,《剑桥中国古代史》使用的繁体中文字形,即使对待中国大陆的出版物也是这样,而且不管怎么说在标准简化字表里也找不到“淦”字的替用字。另外,关于三星堆烧埋动物的仪式在公元前两千纪是独一无二的说法(原文第212~213页),跟第四章所说的安阳地区所发现的对动物进行烧、埋、沉的现象(原文第258页)不一致。
第四章。许多读者会对本书编者没能使用上古汉语的标准参照、或者为编者没能鼓励本书的作者们使用更多的重建的上古汉语而感到遗憾,尤其是在这些重建有利于澄清语源学要点的地方就更是这样。在本章所说的关于“王”字(原文第262页)的语源学观点以及将甲骨文字形“田”等同于后来的“甸”字(原文第272页)的处理上,重建的上古汉语在某些情况下会帮助解释在普通话转写过程中消失了的形态学特征以及语意上的细微差别。本章有一个地方使用了上古汉语的重建(原文第282页),但没有给出出处,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单单在此处运用上古汉语的重建是可取的。
第五章。那些认为西周的终结即意味着整个“朝代”的终结的参考文献,尽管跟战国的某些文献的说法一致,还是会让那些更熟悉传统用法的读者感到不解。另外,引用《诗》里的诗篇的时候(原文第300页及其之后的部份),一定要说清楚本章引用的只是诗的局部,而非整篇。本章的某些段落,让人根本不清楚依据的是什么文献资料(比如原文第310~311页)。关于“周代主要聚居地”(原文第312~313页)的地图和讨论,给人造成应国乃东周时期“主要独立诸侯国”之一的错误印象。讨论周公和召公关系的时候(原文第313~317页),一定要在参考文献中提到松本雅明的重要贡献,他的研究专注于周召二公的后代在建立二公传奇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本章所提到的“天本身……归根结底,即[成王]的父亲”的说法,引发了“天子”一词真正含义的问题(原文第316页)。尽管我们对这个词有一个常见的翻译,早期文献不用它来指示天与父王的关系;在此,或许我们不应该将“天子”解释成“天的儿子”(the son of Heaven),而应该解释成“天所指派或喜爱的贵族”(the gentleman appointed or favored by Heaven)。将《穆天子传》称为“历史小说”(原文第323页注73)肯定会误导非专家读者。严格来说,说《周易》“在大多数情况下其单挂的爻辞都对应着单个图像”(原文第338页注116)是不对的。另外,对于记载公元前780年和776年发生了日食(原文第348页注142)的参考文献一定要重新检视;根据更近的计算,东亚地区在上述的两个年份里均不见有日食发生。
第八章。写“周代封建网络”(原文第549页)而不提及得到广泛讨论的将欧洲封建主义模式应用到早期中国时所引发的固有困难,显然是不恰当的。《国语•郑语》部份不能理所当然地被当作说明东周早期郑国拓疆垦殖的证据来使用(原文第550页);同理,《国语•齐语》部份也不能被信以为描述齐桓公统治时期行政措施的材料(原文第554页)。作为对“霸”的讨论(原文第551~562页)的补充(该讨论极少触及该“系统”的原始以及通常所认为的制度化的原因),此处应该引用跟此主题有关的主要日文文章。鲁桓公六年所记是《左传》中记录楚国统治者称王的参考资料,但桓公六年不能被理解为楚国统治者是在那一年“采用了王的称号”(原文第556页);而只能说《左传》在那一部份初次称其为王。晋献公或者征服了“十六小国”(原文第559页)或者征服了“17”小国(原文第567页),而不可能两者都对。晋文公死后楚军大败晋联军的著名战役发生在Bi邲,不是Mi(原文第561页)。文中对于一次发生在公元前579年个诸侯国之间的会议的记述多处有误(原文第561页);这有可能是本章作者将此次会议与《左传》下一页所记的发生在公元前546年的一次更重要的会议混淆了的结果。晋献公的四个儿子并非是晋献公分别与四位戎女所生(原文第569页);晋献公的大儿子申生是由齐女所生。我们也至少不能简单地认为“文字记载和考古数据在关于铁器方面好像是一致的”(原文第579页)。一部关于早期中国冶金的重要研究著述(此处没有引用)认为,那种以为铁器在春秋时期得到广泛使用的观点是有问题的(原文第578~580页;参照原文第15业)。
第九章。本章在所举战国时期研究史料中不提及司马迁的年表有些异乎寻常(原文第588-593页),因为那些年表的确提供了《史记》中别的地方找不到的信息。像在第八章一样,楚国统治者初次采用“王”的称号的意义值得进一步讨论(原文第603页)。文章认为,“事实上,战国没有制度史,只有个人传记”(原文第603页);这在比喻的意义上而言是对的,但对于缺乏想象力的读者而言,需要指出传记作为一种文学式样是汉代的发明。文中也使用了“奴隶”(slave)一词,因为该词在前面被讨论过而且被拒绝使用(原文第285~286页),读者可能会问该词在此处是如何严格地定义使用的(原文第613页)。最后,文中认为秦王和齐王于公元前288年使用“帝”的称号是”第一次将这一神圣称号用于人王”(原文第637页);这多少有些误导,因为到这个时候,这一称号已经是从王室祖先为人而非神的角度来使用的。
第十章。如果能知道作者根据什么资料来确定战国时期的几次迁都的日期,那将非常有用(应为第654页)。文中说,“因此,一个龙山时期的城镇(为奚仲所建?)就被吸纳进商代的“双城”(为仲虺所建?),后来又变成了西周的宫城”(原文第660页);如果能避免文中出现的一些诸如此类的将文献资料与考古信息混杂的猜测,那将是有益的。另外,说“‘陵’字首次用来表示死始于公元前326年的赵肃侯的陵墓”(原文第716页)严格来说是不准确的;如果我们认为《史记》中该字的首次出现的时刻等于该字在历史上的最早的使用时间,那我们不得不将“陵”字是使用推向更早,一直到帝舜的陵墓时间。
第十一章。“墨”字作为墨子的姓,意思可能是刺青或纹身,而不太可能是烙刑(原文第760页)。在讨论保存在《孟子》里的告子思想时,文中说,“Gaozi is quoted as holding that the significant aspects of morality, which is called yi, as outside our nature…(据称引,告子认为,德——即义——的重要方面(或作:义作为德的重要的方面)源于性之外……)”(原文第775页);这样模糊的语言让人不能确定到底告子的义即德呢还是只是德的某些方面;而无论那种情形,以上提法都会招来一大堆没有答案的问题。由于惠施的思想是结合形式论证的发展来讨论的,引导读者联系《说苑》里提到的他对类比论证的辩护也应该很有用。庄子和惠施关于鱼之乐的著名辩论也被本章引用,用的华兹生(Burton Watson)的翻译(原文第783页);但他们辩论的中心所在即疑问词“安”字的模糊使用(可解为“怎么”或“在哪儿”),但这种模糊性没有在华兹生的翻译中体现出来,而文中所引用的谢迪克(Harold Shadick)和乔健(Chiao Chien)所编古汉语教材里的解释并没有揭示和复原这一辩论的中心所在。还有,并不是整部《吕氏春秋》都“在公元前239年完成”(原文第808页),而只是现存《吕氏春秋》的前十二章,这在书中有明确说明;至于剩余的部份什么时候完成我们不得而知。最后,本章结尾写道,“中国哲学在此时变成了关联性的思想,因为这已经成为(并且将大致上持续到现代时期)中国人所能思考世界以及他们本身的唯一方式”(应为第812页);这种提法过于简化,根本就没有考虑到科学和医药知识的不一致性,包括本书它处所讨论的思维方式。
第十三章。文中所提到的匈奴王“冒顿”通常读作“Modu”,不是此章所标识的“Maodun”(原文第893页);或许此处需要注出为什么不采用传统的读法。另外,用来表示图13.1的英文字母明显有错置的现象:“B”和“C”应该互换位置(原文第894页)。
第十四章。本章在讨论西汉历史学者可能得到的资料的时候说,“汉代最早直接将《左传》引作参考文献的是刻在一方不早于公元前六年的石碑上的碑文”(原文第973页);这种提法是误导性的。那可能是最早提到《春秋左氏传》这一题目的参考资料,因为很明显司马迁和其他学者正是以《左传》(跟其他材料一起包括在《春秋》题下)为主要材料来书写春秋时期历史的。关于国家宗教、国家宗教在前帝国时代的延续性实践、以及其使用碑文的讨论(原文第978~982,999页),现在应该根据1995年以来发表的重要参考文献予以补充。关于老子思想和法家思想关系的讨论(原文第984~988,1008~1010页)一定要提到《韩非子》中将《道德经》解释成论政府权威一类的文章的那些章节,以及其他重要作品。文中所说的“汉代第一位皇帝统治期间的两次广为人知的事件”,被暗指用以说明“一些人感觉需要……带进文明思想来影响朝廷举止以及施政决定”(原文第985页),文中所提的那两次事件到底为何未作说明。将《国语》中的任何一部份定到公元前5世纪前都不太可能(原文第994页);现在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将《国语》及其所包含的成分混杂的内容定到战国晚期。⑤文中所说的《仪法》中的某些内容有时候用来代替《仪刑》也是靠不住的,至少从文中所引用的证据来看是这样(原文第1006~1007页注104);在其所引用的段落里,杜预是在改述诗篇,而不是在徴引该诗的变体,这一点从语法和韵律来看一目了然。文中还说,“荀子可能是[前帝国时代]最擅长政治分析和政治思想表达的思想家”(原文第1008页),这种提法不应该成为让普通读者阅读《韩非子》的障碍,因为在很多人看来,《韩非子》里的观点要远比《荀子》里的论述更精妙。另外,提及晋盟书的时候(原文第1010页),也应该参考英语世界一流的学者罗凤鸣(Susan Weld)的研究成果。①讨论军事组织的时候,文中说:“尽管前帝国时代诸侯国之间战争的教训或许仍然保留在[秦汉]军官的脑海中,但对于这些战役的描述却没有保存下来,即使这样的描述的确存在过。”(原文第1021页)这一说法似乎忽略了《左传》里的那些名副其实的著名的战争描述。
作为这样的大部头作品,《剑桥中国古代史》的排字错误和抄写错误相对算少。在我发现的大约四十处错误中,只有以下几个值得在此指出:马家浜的“浜”字不应写作“滨”(原文第52页);甲骨文转写中有乱码(原文第242页图4.4说明);“jurisdications”应为“jurisdictions”(原文第247页);《诗》篇《緜》(《毛诗》第237首)不应写作“绵”(原文第301页);孔晁的“晁”字应读为“Chao”而不是“Zhao”(原文第312页注47);叶县应读为“Shexian”而不是“Yexian”(原文第324页);“Üniversitat”应为“Universität”(原文第327页注86);“floundered”应为“foundered”(原文第329页);尹吉甫的“尹”字不是“殷”(原文第346页);《诗》篇《烝民》(《毛诗》第260首)的“烝Zheng”不是“丞Cheng”(原文第346页注131);“夨”字错写为“矢”(原文第400页);正文在参照图6.28b和6.28c说明问题时次序颠倒,或者,可能图6.28的说明本身弄颠倒了(原文第441~445页);“献”应该为“甗”(原文第508页);祭仲的“祭”应读为“Zhai”,不是“Ji”(原文第655页);虒祈应读为“Siqi”,而不是“Chiqi”(原文第669页);“Nivision”应为“Nivison”(原文第747页注5);孔丘的“丘”不应作“邱”(原文第752页);“291”应为“241”(原文第872页注146);“millenium”应为“millennium”(原文第889页);在对猃狁和西戎词义进行解释时位置弄颠倒了(原文第920页);“J.C. Andersson”应为“J.G. Andersson”(原文第937页注146);后稷的“后”不应作“后”(原文第980页);嫪毐的“毐”不应作“毒”(原文第1021页)。
(《国学学刊》授权刊发,见2017年第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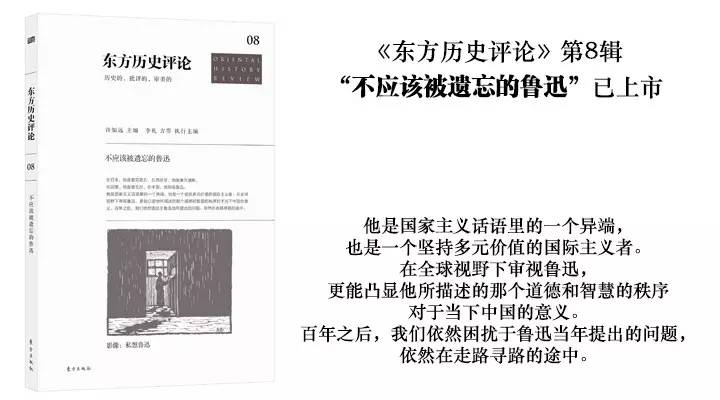
点击下方
蓝色文字
查看往期精选内容
人物
|
李鸿章
|
鲁迅
|
聂绀弩
|
俾斯麦
|
列宁
|
胡志明
|
昂山素季
|
裕仁天皇
|
维特根斯坦
|
希拉里
|
特朗普
|
性学大师
|
时间
|
1215
|
1894
|
1915
|
1968
|
1979
|
1991
|
4338
|
地点
|
北京曾是水乡
|
滇缅公路
|
莫高窟
|
香港
|
缅甸
|
苏联
|
土耳其
|
熊本城
|
事件
|
走出帝制
|
革命
|
一战
|
北伐战争
|
南京大屠杀
|
整风
|
朝鲜战争|
反右
|
纳粹反腐|
影像
|
朝鲜
|
古巴
|
苏联航天海报
|
首钢消失
|
新疆足球少年
|
你不认识的汉字
|
学人
|
余英时
|
高华
|
秦晖
|
黄仁宇
|
王汎森
|
严耕望
|
罗志田
|
赵鼎新
|
高全喜
|
史景迁
|
安德森
|
拉纳・米特
|
福山
|
尼尔・弗格森
|
巴巴拉・塔奇曼
|
榜单|
2015年度历史书
|
2014年度历史书
|
2015最受欢迎文章
|
2016年最受欢迎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