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书单
丨
2018年2月-3月书单
丨
2018年4月书单
丨
2018年5月书单
丨
2018年6月书单
丨
2018年7月书单
丨
2018年8月书单
丨
2018年9月书单
丨
2018年10月书单
丨
2018年11月书单
今年读书163本,本月读书19本。
永远保持一份战栗与警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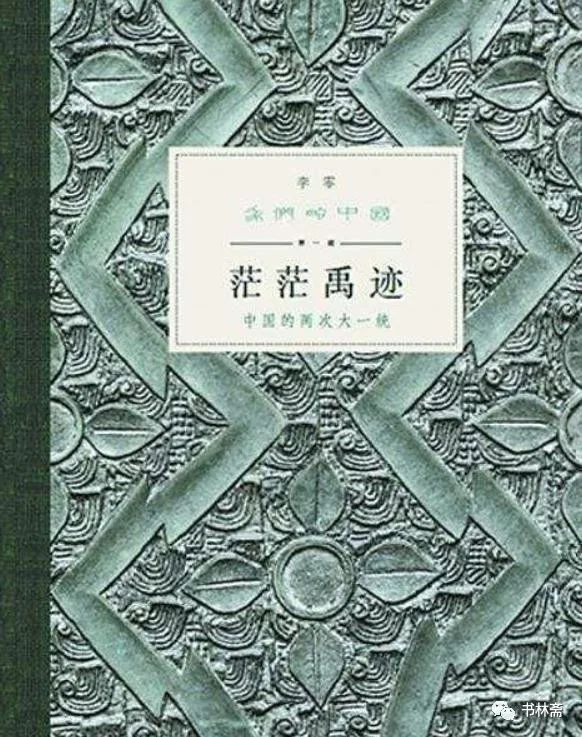
李零老师一直在试图构建一个三代以前的中国,一个文化共识角度下的中国,因此具有中国的特殊性,而恩格斯的定义其实具有的是普遍性。
这种共识构建或者不可解释,或者处于不断的争议与运动中。本书从文化一统写到族姓源流,然后通过豳公盨和《禹贡》来构建禹对中国覆盖土地的文化意义,最后将目光放在了最后完成大一统的秦身上,构建起秦和周密不可分的联系。
虽然是好几篇论文的合集,但是很明显,李零老师在这些文章里有一个清晰的脉络,那就是:我们是有源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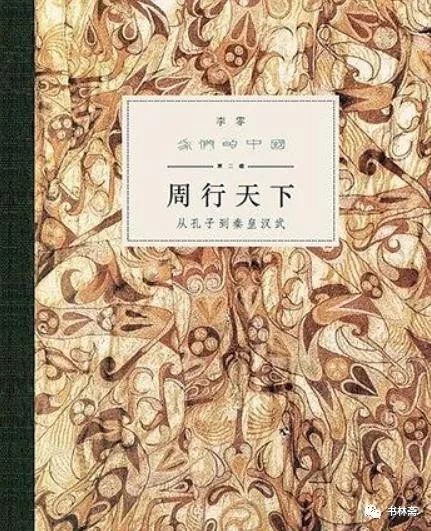
这一本的建构很明显就不如上一本。
其实从孔丘到嬴政再到刘彻,是一个很有趣的建构过程,贯穿在其中的,是儒家的一整条脉络。
一部战国史,其实就是一部儒家内斗史,从儒商子贡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开始,春秋就结束了战国就要开始了。紧接着的田子方、吴起接连登场,间接影响到了李悝、商鞅、荀卿、李斯等。这种内斗,其实早在孔丘还活着的时候就开始了,比如神奇的宰我之死,老夫子死后,曾参和卜商更是分庭抗礼,和王阳明死后王学分了好几支一样。儒家不只有儒生,还有儒商、儒将、儒农等等,但为什么最后只剩下了儒生呢?因为后来我们对战国儒生的认知只剩下了一个人——孟轲,而孟轲其实并没有拜师,他只是自认是孔丘孙子子思的学生,他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子私淑诸人也。但谁也没想到,曾参这一支在千年后的真正胜利,来自一个没有拜过师门的好辩后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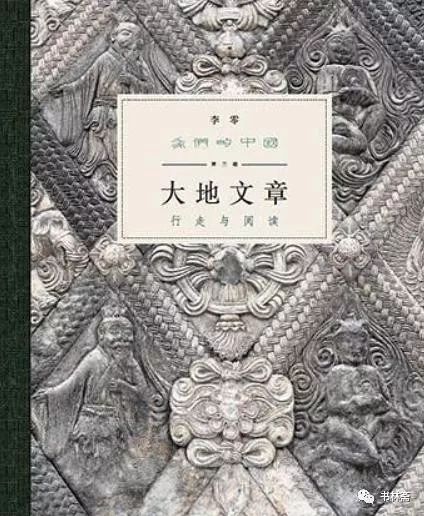
这其实是一本历史散文,没多大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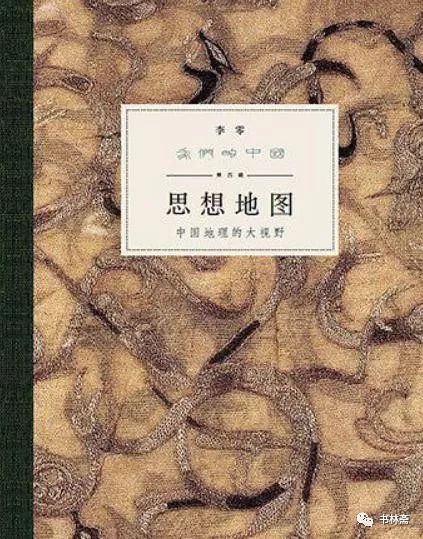
孔丘是一个巨人,嬴政也是一个巨人。在很多人的心中,这两个巨人是永远对立的。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孔丘出生在的那个地方,曲阜,是嬴姓的祖庭,后来嬴政祖先那一支迁到了西北,生根发芽。孔夫子和秦始皇就这么被奇妙地联系上了。大概就在公元前1000年,周灭商,秦人的祖先离开了曲阜,鲁人的祖先来到了曲阜。
更重要的事是,他们都很看重泰山,也都很看重天下。孔丘登泰山而小天下,他东观大海,南瞻吴越,西眺秦晋,北顾燕齐,他的志在天下,是周公旦的天下,是周天下;嬴政登泰山而封天下,他五巡疆域,刻石标记,宣示着这一切都是他的天下,他也志在天下,是秦王政的天下,是秦天下。
他们面临的,都是大一统的概念。孔丘怎么也没想到,他毕生的心愿之一,结果在嬴政的手上被重新建构了,虽然那并不是他本身的愿望,但是孔丘和他的历代弟子们一个个前赴后继地谱写了战国史,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发现,战国思想史诸子百家,没有哪家可以和儒家彻底划分界限。
巨人从来都不是互相鞭挞的,相反他们是可以互相理解的,也是互相继承的,只是继承前一个巨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打倒他。

典型的民国文风,于体例、观点上都和现在的最新研究有差异,关于西周和上古史的部分,更推荐王玉哲先生的《中国上古史》。
但在这本书中,通过弭兵之约,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一个点:春秋的本质不是争霸,而是一次制衡,是一次在周天子王室的衰颓中,诸侯们寻求自身新的利益点的过程。所谓的春秋五霸,也截然不同于战国时期的你死我活、勾心斗角,而是在寻求各国的平衡态。
那么这样的平衡态在什么时候被打破的呢?
《资治通鉴》第一句话:「
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
当你周天子都默认了大夫可以升任为诸侯,那么平衡自然也就不需要了。

不读这本书,也许你实在是想象不到郭沫若其实是一个十分真诚、可爱的人,行文间不断地承认自己过去某某认识是错误的,并且不断提出新的见解,尽管如此,他的学术功底确实是扎实,从简简单单的史料中就能挖掘出大量的内容,并加以发散,这个本领是需要浑厚的基础的。
至于这本书所引发的那首诗,本质上是一次借题说话,不必因此而小看了这本书。郭沫若的学问之深,纵使一般大家亦难以望其项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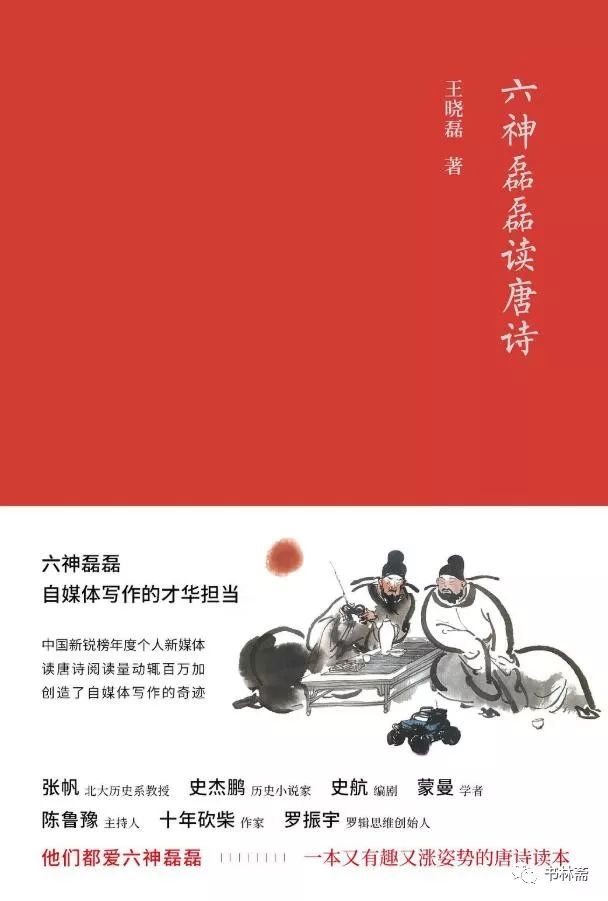
诗人是最能感知时代情绪的。
六神磊磊写唐诗和当年明月写明史一样,都是以通俗诙谐的手法,写情绪。这一点很重要。对于不了解唐诗的朋友,可以读一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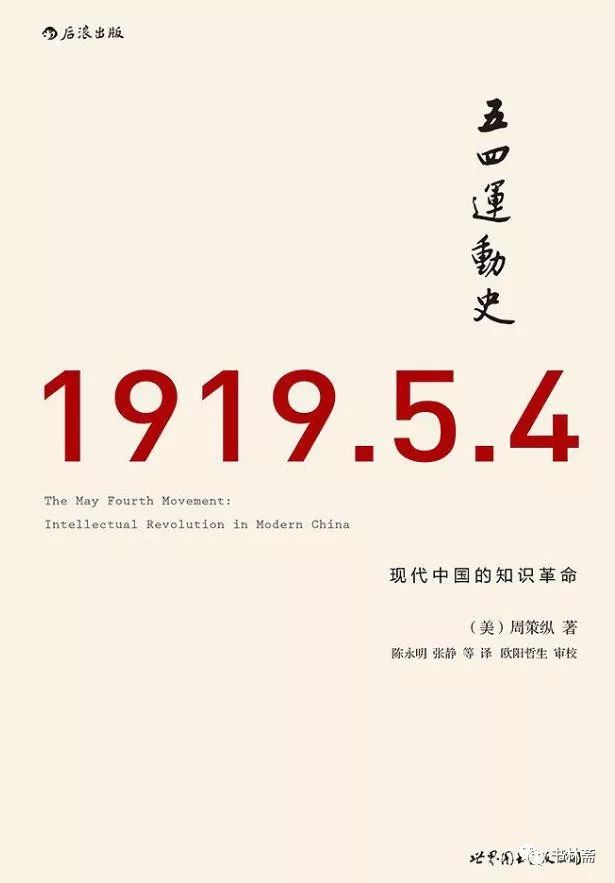
五月四日只有一天时间,但五四运动不只有一天,狭义说它持续了一个多月,广义地说它持续了好几年,从1915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开始祭孔,到1923年孙中山发表越飞宣言,在这八年时间里,整个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要追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就势必要追溯到五四运动。
从社会性质来看,自然能够理解,为何五四运动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之间的分界线,因为舞台上的主人不同了。五四运动中的人们,有一种古典的责任感,也有一种迫切的情绪,这一切使得它是如此地与众不同。
是需要我们来好好了解一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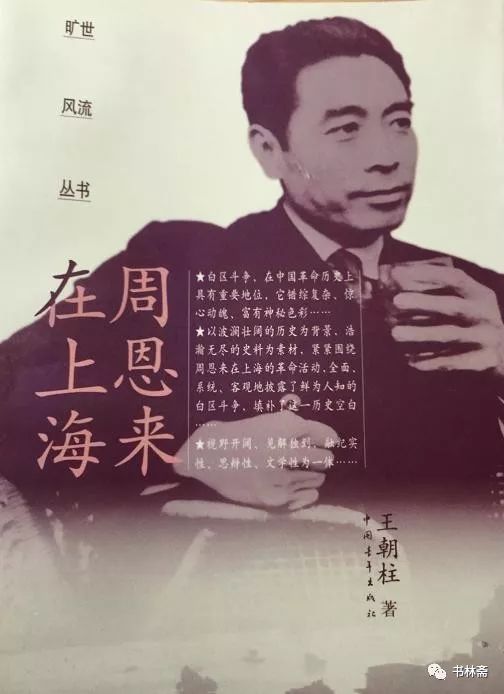
在党史里,向来是从三大起义后就直接跳到了井冈山根据地,然后引出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出政权等耳熟能详的正确路线,但正确不是凭空得来的,是通过无比严峻且残酷的烈士们的鲜血得来的,而这些鲜血,就是一次次的试错。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党的中心不在根据地,而在白区,在上海。党的负责人也不是后来的主席,而是后来的总理。本书就从这个角度出发,用比较详尽的史料细节,写出了总理当年在上海待的那几年所经历的种种,最后认同了农村包围城市的论断,走向苏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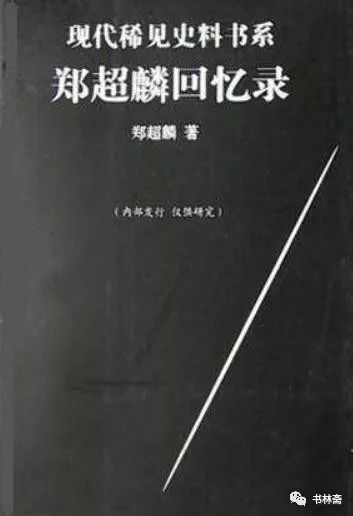
一个走了错误路线的人,一个被历史抛弃的人,一个有趣但没意义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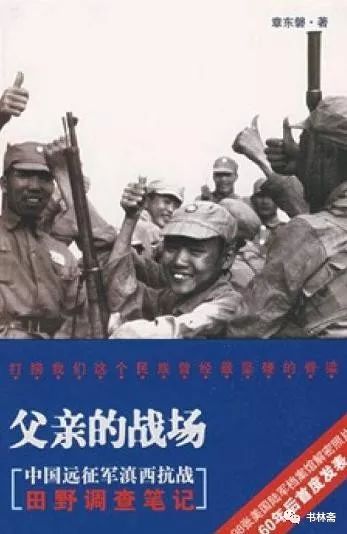
家里书太多了,把书柜都压塌了,朋友戏谑说这叫历史的厚重。于是我就把一部分厚重的历史卖给了一些朋友。
在把其中一本(即本书)卖给朋友的前一个晚上,我又一次打开了这本书迅速读了一遍。
这本书讲述的是作者如何意外闯入滇西抗战的事情,于我而言,那也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儿了。那天晚上,一个日常在实验室待得很晚的大学同学回来,到我宿舍时跟我说他晚上看了一部凤凰大视野的纪录片《中国远征军》,很感人,从那时起我便与它结缘。
然而三五年过去了,我的情绪已经被解构掉了,就像这本书说的那样,这是父亲的战场,我们的远征,我不会忘记这些情绪,但我不再需要这些情绪了。
而新的情绪,早已在烈火中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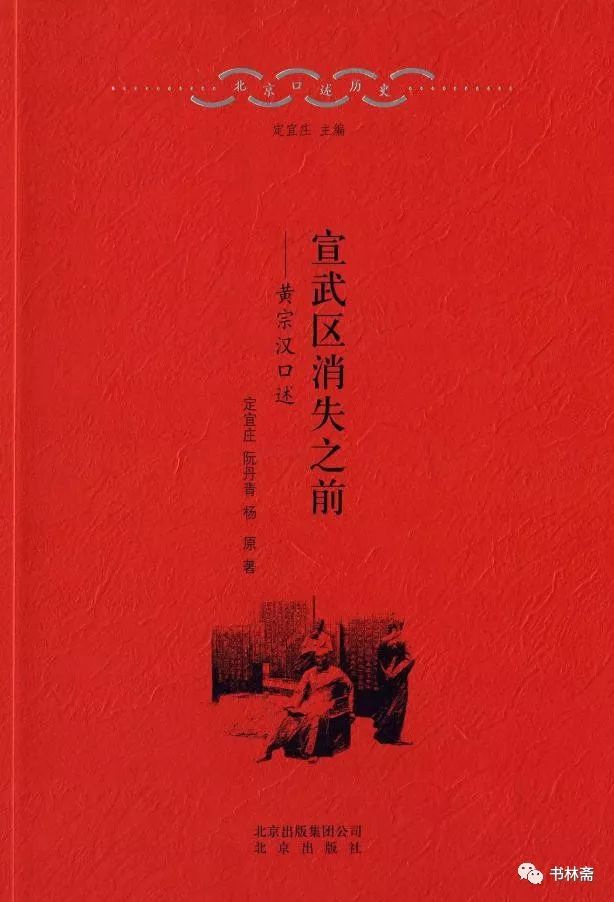
黄宗汉老先生有一个初恋,北大物理系的女大学生,是解放初期和他相识相爱的,但因为黄宗汉是宣武区的区干部,而他的初恋的父亲是国民党,这自然是不可能在一起的了。
后来她和一个中山大学物理系的教授在一起了,不过却一直和黄宗汉有信件来往,黄宗汉也不忌讳把这事告诉自己的妻子,这些信件他妻子也都看过。
五十年时间过去后,1998年,北大百年,他的初恋回来参加纪念,他们终于又见了面,说起当年的事情时,女方忽然说,她的父亲其实是大革命以前的国民党,是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27年以后就退党了,这在组织审查上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本来是没有问题的,但因为一个疏忽,人生就这么倏忽而过五十年。初恋的爱人去世了,初恋自己也得了癌症。
黄宗汉和他老伴邀请她去自己家作客,她不肯,她说:「
不,我不去,那个原来应该是我的家。
」
莞尔。我想黄宗汉那时一定很想给她一个拥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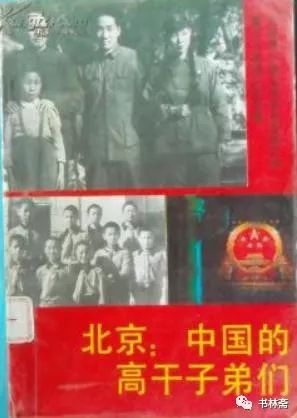
典型的九十年代读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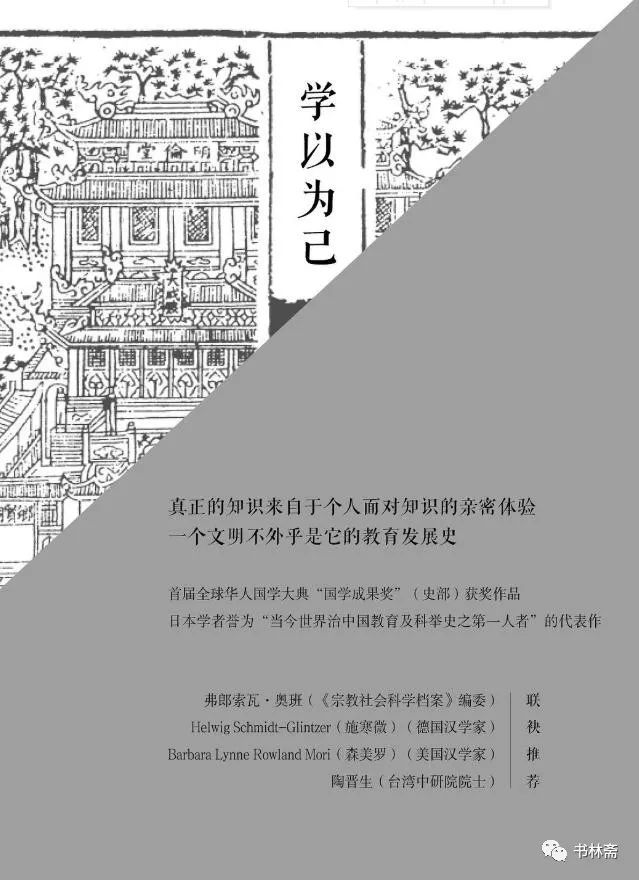
当读到作者一句「
在古代中国,学校才是社会的缩影
」时,便已知作者不过是一个传统的文人,再读到作者歌颂那些地主阶级的殉道者时,这本书便知道在讲什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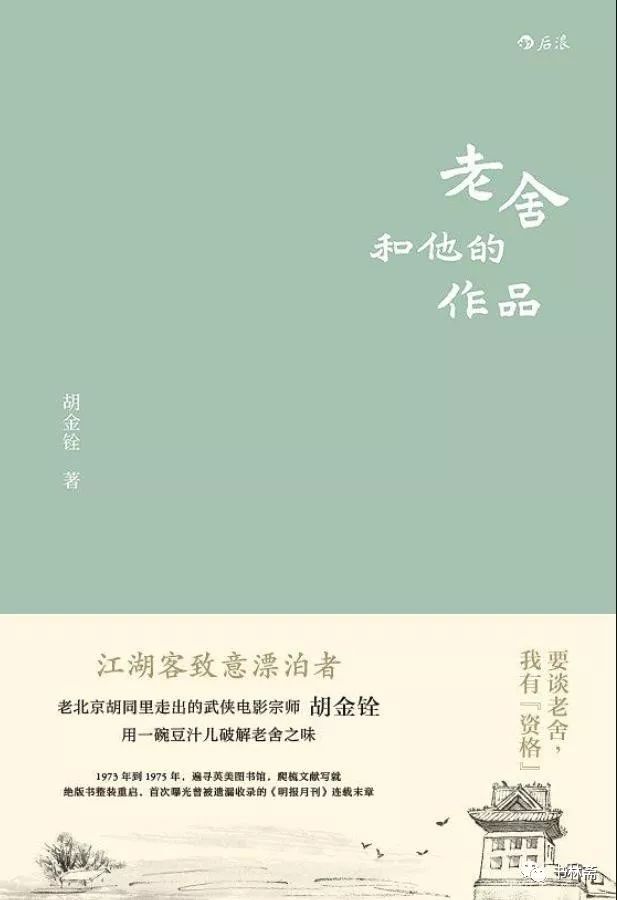
胡金铨上来就表示,用各种文论对老舍作品的解构他是不信服的,迅速地,他用了老北京的豆汁儿来试图解构并同时建构起老舍和他的作品。
文学评论的作用是在解构一部作品,而有心人会在解构的同时重新建构他想建构的内容。胡金铨看似没有用文学理论解构老舍,其实只是跳过了用理论解构老舍作品的环节,直接对老舍及其作品进行有关豆汁儿的建构。
如果是一个普通人,我们要讨论的应该只是这种建构的价值,因为每一种建构,都是对老舍的再探讨,而现在对老舍进行建构的是胡金铨——也就是说,我们在读的这本书,一方面是看胡金铨如何建构老舍,另一方面还可以从胡金铨对老舍的建构中解构胡金铨的一部分——这是看名人不按常规套路聊名人的有趣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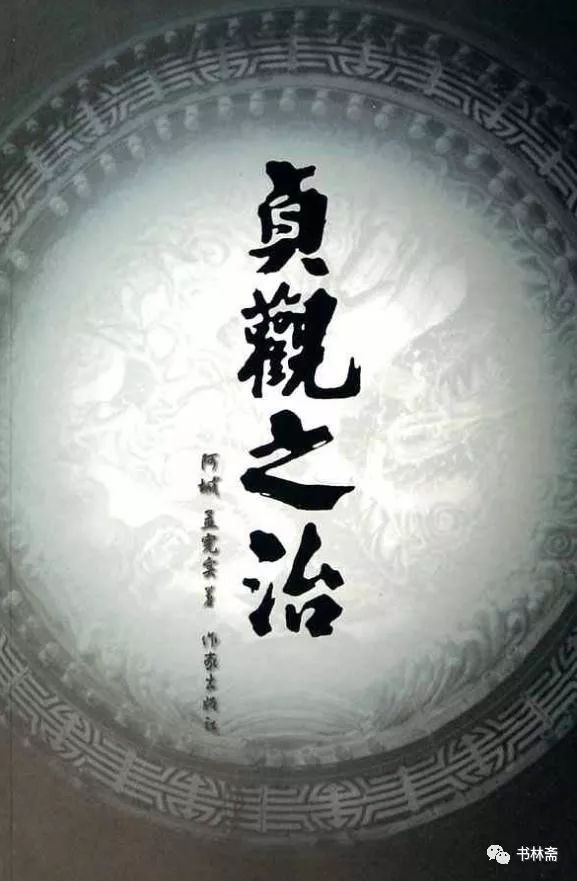
电视剧《贞观之治》的剧本,孟宪实和阿城两位老师编剧,遗憾的是几乎没有一场戏算得上是戏,没有起承转合,没有任何波澜,一直在不停描述状态,没有任何对事件的建构。但仍旧看得让人津津有味,编剧不懂戏,但很明显懂历史哲学。
准确地说,《贞观之治》拍的是贞观朝的宏观政策,而不是历史事件。
如果你读过《贞观政要》,并且对此很感兴趣,那么这本书和这部剧可能适合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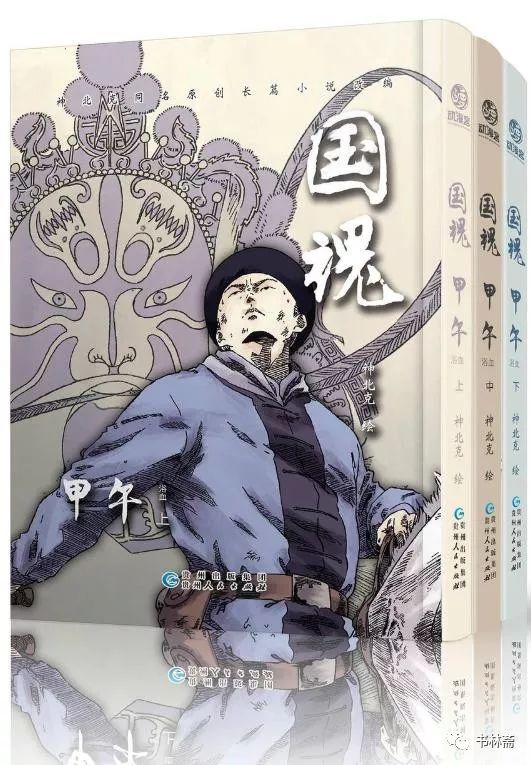
愿为长安轻薄儿,生于开元天宝时。斗鸡走犬过一生,天地兴亡两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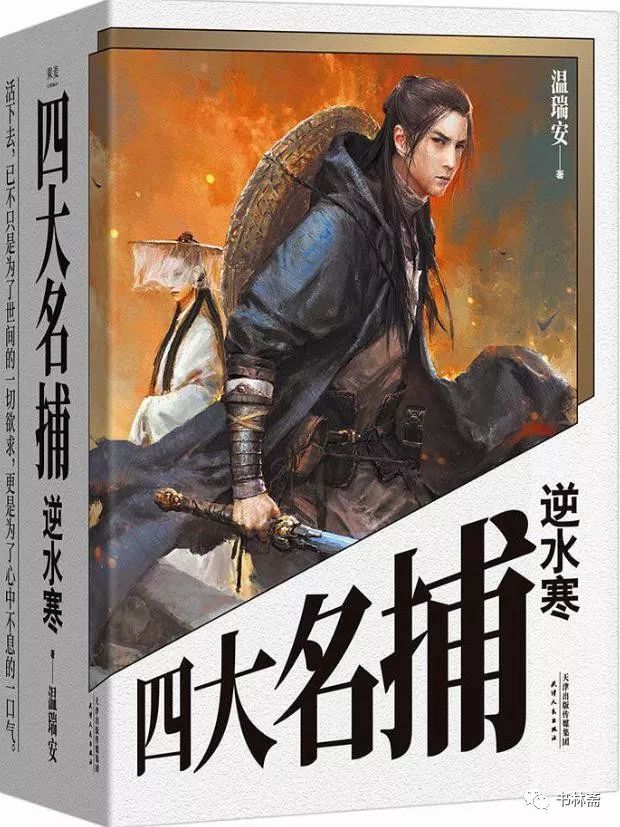
《绣春刀》诞生的时候,总会有人说,这是「
不一样的武侠
」,迥然于金庸的「
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那是在夹缝中进退苟活的鹰犬,在朝廷的刀俎中挣扎的鱼肉,是君权的威压下失落的江湖。殊不知早在温瑞安笔下,这样的江湖早就屡见不鲜了。
相比于电视剧中、天涯论坛上惊才绝艳的钟汉良版顾惜朝,我印象最深刻的,不过是那个旦夕间被扭变局势,仰人鼻息、卑屈求存的顾惜朝。这是温巨侠的江湖里最残酷的底色,没有什么易水寒的悲壮,只有庙堂倾轧与逆转下的棋子与尘埃。唯一值得向往的,是戚少商、铁手临阵前的肝胆相照与震天长吟,是息大娘与赫连春水蓦然倾吐衷情的江风明月……
1986年的《逆水寒》,是温巨侠彻底疯魔前的绝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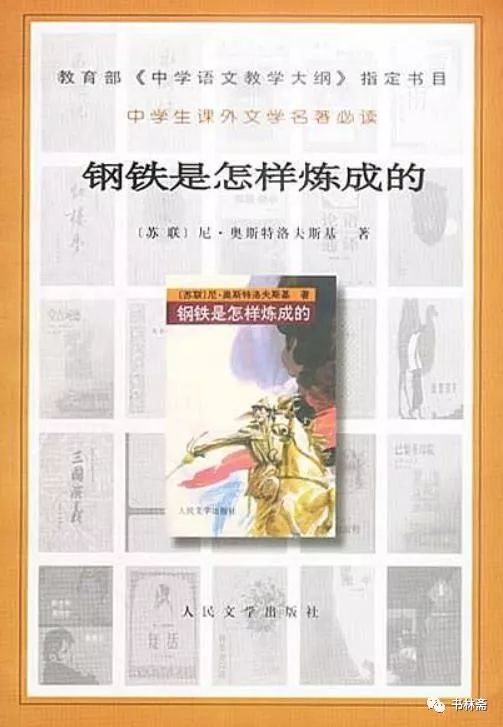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它给予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经把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这个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了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当我还在学生时代时,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周日下午五六点,天刚刚变暗,仿佛预示着第二天又要上课的烦心事到来。
我的2018年关键词是解构。从年初到年末,通过各种重逢与告别,解构了过往,解构了念想,解构了理论。解构到极致是会虚无的,因为连执念都被解构了。但是这不重要,因为解构的同时也在建构。明年我就26岁了,于是我不禁想到一个问题,我56岁时在做什么?
也许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因为我们所有人都要先记住此刻的情绪,它会稍纵即逝,未来的我们会一遍遍回想起这令人怀念的时光。而属于2018年的关键词是什么呢?也是解构,解构掉过往熟知的一切。
阅读原文处可查看文章集锦。
来公众号「书林斋」(Kongli1996)、微博「孔鲤」及豆瓣「孔鲤」。
我写,你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