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TITUTE|批评·家
|
理论与历史碰撞/个例与议题交织
文|
马琳娜·茨维塔耶娃
/
译|
张猛/
责编|
批评+

本次推送的是马琳娜·茨维塔耶娃评述另两位与她同时代的伟大诗人,
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与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熟悉那段历史的人,可能已经很了解这三位以及他们各自取得过的成就。除了
茨维塔耶娃、
帕斯捷尔纳克和里尔克三人之间的通信以及留在世界文坛上的一段佳话之外,还有
茨维塔耶娃对马雅可夫斯基以及叶赛宁的推崇,在她看来,马雅可夫斯基与帕斯捷尔纳克这两位同龄人
都
在诗歌中最终找到了自己。
表面上来看,马雅可夫斯基和帕斯捷尔纳克之后走的可能并非同一条道路,然而在茨维塔耶娃的笔下,她不仅让这两位在时代中比肩而立,而且把自己从这两位身上感受到的诸多截然相反的性格成组成对地并置在一起,贯穿了正片评述,编排成了一曲“
时代拐角的
”合奏,院外分四期推送。
在这一期中,茨维塔耶娃
提及
马雅可夫斯基
从向世界展示自我开始,从标榜自我、公开炫耀开始,
热爱表现和自我展示,
什么也不害怕,听众越多,他的叫声也就越高,他的读者
只有一个——俄罗斯;相应的,帕斯捷尔纳克
悄然隐遁,自我遮蔽,
没想要荣耀,或许害怕诅咒之眼,
从来都不会有广场,但他将来会有,他
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个声音。
某种程度上,
帕斯捷尔纳克的诗集应当随时都带在身边,就像是护身符,以抵御所有齐声吟诵马雅可夫斯基的人们。
从本质上来说,他们都没有读者,因为
马雅可夫斯基有的是听众,而帕斯捷尔纳克那里则是偷听者、偷窥者,甚至是跟踪者。
茨维塔耶娃引用了
丘特切夫的诗句:一切在我之中,我在一切之中。一切在“帕斯捷尔纳克”之中,“马雅可夫斯基”在一切之中。
我们还可以就此补充一点:当我们考察那段历史时,找到了众多马雅可夫斯基的形象,从各个时期不同场景中的照片,到各种各样与话语组合在一起的拼贴图像,然而在帕斯捷尔纳克那里,除了为数不多的几张标准肖像和一些生活即景之外,就不再有太多其他的资料了。我们倒是从中发现了一组拍摄于不同时期的照片,几乎完全相似的构图和神情,他兀自站
在窗台前,望向窗外的
远方,但他眼前的窗似乎从未打开过,而窗台边的他似乎从未离开过,
这样站着,并将一直站下去
……

Борис Леонидович Пастернак
|
1890年2月10日-1960年
5月30日


马琳娜·茨维塔耶娃
|
Марина Ивановна Цветаева
现代俄罗斯的史诗与抒情诗|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与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
|
一
本文
5500
字以内

说起俄罗斯的现代诗歌,如果我把这两个名字放到一起,那是因为他们比肩而立。可以在说起俄罗斯的现代诗歌时,提到他们中的一个名字,他们任一个,并且不提另一个——也同样会呈现出全体的诗歌来,就像在每个大诗人那里呈现的一样,因为诗歌不会在诗人们内部分散,也不会分散到诗人中间,它在自己的所有现象中间都是一体的,是一个,在每个诗人那里都是完整的,因为,本质上说,不存在诗人们,只有单数的诗人,从最初直到世界的末日都是同一个,是同一种力量,被染上特定时代、部落、国家、方言以及经过这种力量时的面孔的色彩,这些时代、部落、国家、方言和面孔就像河流一样,被同样的岸、同样的天空、同样的底部所支撑。(否则我们无法理解维庸[1.
法国诗人,
约1431-1474],我们现在是把他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他的,甚至忽略纯粹地在身体上无法理解另一种语言。我们正是要返回到他那里,就像返回到故乡的小河一样。)
因此,如果我把帕斯捷尔纳克和马雅可夫斯基并排放在一起——使他们比肩而立,而不是把他们放到一块儿——那不是因为提一个名字不够,不是因为一个需要另一个,一个可以补充另一个;我再重复一遍,每一个都完全自足,俄罗斯也因为任何一个而自足,并且不仅仅是俄罗斯,诗歌本身也是如此——我这样做,是为了再次说明,五十年的时间出现一个大诗人已属不易,而上帝在五年的时间两次显示奇迹:这是诗人完整的、圆满的奇迹。
我让他们比肩而立,因为他们在时代之中,作为时代拐角的领导者,这样站着并将一直站下去。
我听到一个声音:“俄罗斯的现代诗歌”。“帕斯捷尔纳克也就算了,可是马雅可夫斯基怎么可以,他可是在1928年……”
首先,在我们谈论一位诗人的时候——愿上帝保佑我们记住他所处的时代背景。第二点也即回过头来说:谈论起这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我们要记住的不仅仅是他的时代背景,我们还必须记住的是未来的时代。这样的一种空缺——世界上第一位大众诗人——是不会那么快便被填充的。因此,如果我们,或许还有我们的孙辈们,要回头看马雅可夫斯基的时候,需要的是朝前看,而不是向后看。
当我在一个法国文学会议上听到所有的名字,却没有听到普鲁斯特的时候,我会显露出天真的惊讶:
“那普鲁斯特呢?”“可是普鲁斯特已经死了,我们讨论的是活着的人。”(法语,译者注)我每次都像从天上掉下来一样;他们是根据什么标志来判决一个作家的生死呢?对于一个尚且在世的X,他的现代和有效难道不是因为,他可以出席这场回忆,而马塞尔·普鲁斯特之所以被除名,就因为今天他无法到场,是个死人吗?这样的判断只适用于竞走运动员。
作为回答,可以这样善良、平静地说:
“我去哪里找像我这样有飞毛腿的人呢?”
马雅可夫斯基用自己的这双飞毛腿已经远远迈过了我们的现代性,并且还要在某个拐弯处等我们很久。
___________
帕斯捷尔纳克和马雅可夫斯基是同岁。二者都是莫斯科人,马雅可夫斯基在那里长大,而帕斯捷尔纳克则一出生就在那里;二者都是从其他领域转向诗歌,马雅可夫斯基来自油画,而帕斯捷尔纳克则来自于音乐;二者都借鉴了别的成分成为自己的:马雅可夫斯基借鉴的是“普通木工凶狠的目测力”,帕斯捷尔纳克——所有的含蓄特点;二者都达到了充实丰富的境界;二者都不是立刻便发现了自己的位置,都是在诗歌中最终找到了自己。(顺便提一个想法:最好不要立刻在其他方向找到自己的位置,而是要在自己擅长的地方发现自己。在别人的地方会犯迷糊,在故乡可以收获自我。至少可以不靠“尝试”而把事情解决。)
两个人的探索岁月(德语,译者注)都结束得早。但马雅可夫斯基转向诗歌写作还有革命的原因,并且我们不清楚,哪个原因占的成分更大。来自于革命事业的原因。他十六岁时就已经坐牢了。“这不是荣誉。”但却是一种标志。对于一个诗人来说这不是荣誉,但对于一个人来说它是标志。对于这位诗人来说——它也是荣誉:从为自己的信念买单开始写诗。
他们每个人的诗歌面貌都很早便形成和表现出来。马雅可夫斯基从向世界展示自我开始:从标榜自我、公开炫耀开始。帕斯捷尔纳克呢,——谁能说的上来帕斯捷尔纳克从哪里开始的?已经很久没人知道他的消息了。(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在1922年的一次谈话中说:“他有一项十分光彩的名声:专注于地下”。)马雅可夫斯基热爱表现,而帕斯捷尔纳克则悄然隐遁。马雅可夫斯基自我展示,帕斯捷尔纳克则自我遮蔽。如果说现在帕斯捷尔纳克留下了名字的话,那么这个名字是没那么容易留下的:适合培养天才的时间和疆域都是偶然出现的;培养天才的场所是开放的,甚至不是开放,而是天赋的(法语,译者注),倘若这种天赋的携带者不是那种持有异己思想的话(要知道有一批被供养,但是却被窒息的诗人)。

马雅可夫斯基在红军营地|


马雅可夫斯基这个名字本该永远都留不下来的,但却被永远保留下来了。也可以说,这名字要比他本人出现的更早。后来他就不得不奋力直追。马雅可夫斯基就会有这样的经历。这个少年在自己身上感受到一种力量,具体什么样的力量——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张口说道:“我!”别人问他:“我——是谁?”他回答:“我: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那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又是谁?”“我!”在这之后就没什么了。随后,后来——就没什么“后来”了。后来就有了这个:“那个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就是我。”众人大笑,但这个“我”在耳朵里、那件黄衬衫在目光里——留下来了。(唉,其他一些人直到今天也没在他身上看到、听到别的东西,但没一个人忘掉他。)
帕斯捷尔纳克呢……人们是知道这个名字的,但那是他父亲的名字:亚斯纳亚·波良纳的艺术家、色粉画家、女人和小孩头饰的设计师。我在1921年便听过这样的评论:“嗯,是的,波利亚·帕斯捷尔纳克,画家的儿子,有教养的小男孩,人很好。他来过我们这儿。他现在在写诗吗?可是,好像他以前是搞音乐的……”在父亲的绘画和自己少年时期的(非常强劲的)音乐中间,帕斯捷尔纳克被夹在中间,就像处于两座山中间的峡谷。作为第三者的诗人该在哪里确定呢?在帕斯捷尔纳克身后已经有了三个小站点(从最后一个开始):1917年——《生活,我的姐妹》(1922年前后出版),1913年——《在街垒之上》,而第一个,也是最早的,甚至连我这个写诗的人也不知道书名叫什么。又能问其他人什么呢?在1920年之前只有少数一些人知道帕斯捷尔纳克,他们看着血液怎样流淌,草叶怎样生长。关于帕斯捷尔纳克,可以用里尔克的话来说明:
“他们的目的是开花,而我们想要默默无闻地劳作。”(德语,译者注)
帕斯捷尔纳克没想要荣耀。或许他害怕诅咒之眼:那只普遍的、事不关己的、空洞无物的荣耀之眼。俄罗斯也应当这样提防外国旅游团。
而马雅可夫斯基什么也不害怕,他站在那里高声喊叫,叫得声音越高——就有越多的听众,听众越多,他的叫声也就越高——直到达到《战争与和平》里的状态,引来综合技术博物馆几千人的听众——在这之后传遍全俄罗斯一亿五千万人口的广场上。(就像我们说起歌手会用到“竭尽全力演唱”这个词,说起马雅可夫斯基可以用“竭尽全力喊叫”来表达。)
帕斯捷尔纳克从来都不会有广场。他将来会有,现在也已经尊在众多孤独的人、同样也众多饥渴的人,等待他这样一眼孤独的泉来滋养。人们跟随马雅可夫斯基或者帕斯捷尔纳克前行,就像在未知的河水里涉足,沿着某些可信的东西朝一个地方走去,但这种依托在哪里?是什么?猜测着、摸索着、连蒙带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路,所有人都是分散的、不能协同的。处在帕斯捷尔纳克那里,就像站在小溪旁边,相遇是为了重新分离,每个人都畅饮一番,每个人都清洗了全身,将小溪留在身体里、带在身上。而在马雅可夫斯基那儿,就像在广场上,要么是打架斗殴,要么是齐声放歌。
帕斯捷尔纳克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个声音。马雅可夫斯基只有一个读者——俄罗斯。
在帕斯捷尔纳克那里,读者不会忘掉自己:他们找到了自己,也找到了帕斯捷尔纳克,也就是说发现了新的眼光,新的听觉。
在马雅可夫斯基那儿他们忘掉了自己,也忘掉了马雅可夫斯基。
阅读马雅可夫斯基,需要所有人一起读,几乎是齐声诵读(以人声熙攘、集会的方式),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出声地读,尽可能地比每个读者自己读的时候声音更高。整个大厅一起朗读。整个世纪都在朗读。
帕斯捷尔纳克的诗集应当随时都带在身边,就像是护身符,以抵御所有齐声吟诵马雅可夫斯基两个(不可违背的)真理的人们。更好的方式是——就像所有时代诗人写作、人们阅读诗歌的方式那样——在树林里,一个人,不去关心是树叶组成了森林,还是书页构成了帕斯捷尔纳克。

马雅可夫斯基在演播|


我说过:世界上第一位诗人是大众。现在我还要再补充一句:第一位俄罗斯诗人是演说家。从《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的悲剧直到最近的一首四行诗节:
众所周知,“事件尘埃落定”,
爱情的小船在日常生活上撞得粉碎。
我们对生活精打细算,那张记录
彼此疼痛、不幸与侮辱的名单毫无用处。
在他的整个的生活延绵中,到处是与鲜活的瞄准器之间的直白言语。从演说家到市场上拉拢买卖的人,马雅可夫斯基孜孜不倦地将一些东西钉在脑子里,要从我们那里实现某些东西——不惜借用最粗俗、也永远成功的任意手段。最近的一个例子:
在亚历山德拉·菲奥多洛夫娜的床上,
懒洋洋地躺着亚历山大·菲奥多洛维奇。
这一点我们永远都知道,那些所有人都清楚的名字的发音,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但却是绝妙的!我们不管怎样看待亚历山德拉·菲奥多洛夫娜,或者是亚历山大·菲奥多洛维奇,或者是马雅可夫斯基本人,我们中的每个人都会对这些诗行感到满足,就像对一个公式感到满意一样。他是那种永远能够在任何事情上取得成功的诗人,因为应当成功。因为在那个马雅可夫斯基勤勉踱步的边界之上,不停地犯错,也就是说——不停地被打碎。马雅可夫斯基的所有创作是伟大与老生常谈之间的平衡。马雅可夫斯基的道路不是一条文学的道路。走在他这条路上的人每天都在证明这一点。力量是无法模仿的,而没有了力量的马雅可夫斯基毫无意义(法语,译者注)。能够引向伟大的那个公共的场所——往往是马雅可夫斯基的公式。在这一点上他——在另一个时代——另一种话语里——类似于雨果。我记得马雅可夫斯基对他很敬重:
每个少年体内都有马里内蒂的火药,
每个老人心中都有雨果的智慧。
之所以是雨果,而不是歌德,不是没有道理的,对于后者,马雅可夫斯基没有任何与之相近的地方。
帕斯捷尔纳克在和谁说话呢?帕斯捷尔纳克在自言自语。我甚至想说:在本人在场的情况下,就像现场只有树木或者狗一样——人不会背叛它们。帕斯捷尔纳克的每一个读者都感受到了这一点——他们会暗中偷窥。他们的目光并不投向帕斯捷尔纳克的房间(他在那里做什么?)而是直接投向他的皮肤深处,肋骨的里面(他的体内发生了什么?)。
在他(已经持续多年)努力脱离自身,用某种(甚至是所有的)话语、某种方式来谈些东西,帕斯捷尔纳克坚定不移地不那样言说,不讲那些东西,最主要的是,他不对任何人言说。因为这是一种思想在发出声音。他出现——在我们中间,忘记——排除掉我们。一种梦中或者是半睡半醒状态下的话语:“睡意朦胧的公园在咿呀学语……”
___________
(读者试图与帕斯捷尔纳克对话,这让我想起《爱丽丝漫游仙境》里的对话,其中每一个问题对应的答案要么是延后的,要么是跳跃的,要么根本跟主题无关——本来应该是十分确切的答案,但在这儿却不合时宜。两者之间之所以相似,是因为在《爱丽丝》中展开的是另一种时间,梦中的时间,而帕斯捷尔纳克从未走出过这种时间。)
___________
无论是马雅可夫斯基,还是帕斯捷尔纳克,从本质上来说,都没有读者。马雅可夫斯基有的是听众,帕斯捷尔纳克那里则是偷听者、偷窥者,甚至是跟踪者。
还有一点:马雅可夫斯基不需要读者的共同创作,有一双(最普通的)耳朵——就可以听到,听完——又冒出来。
帕斯捷尔纳克整个地处在与读者的共同创作之中。少数一些人阅读帕斯捷尔纳克很轻松,或许,相比帕斯捷尔纳克书写自己来说,他们又完全是不轻松的。
马雅可夫斯基对我们的影响传达到我们身上,帕斯捷尔纳克的影响则是在我们体内。帕斯捷尔纳克不是被我们读,他是在我们身体里完成。
关于帕斯捷尔纳克和马雅可夫斯基有一个公式。这是来自丘特切夫的一句两位一体的诗句:
一切在我之中,我在一切之中。
一切在我之中——帕斯捷尔纳克。我在一切之中——马雅可夫斯基。诗人与山。对于马雅可夫斯基来说,要想存在(实现),需要有山。如果单独囚禁马雅可夫斯基——他什么也不是。对帕斯捷尔纳克来说,要想有山,只需要生下来。若单独囚禁帕斯捷尔纳克——他就是所有。马雅可夫斯基需要用山来达到目的。通过帕斯捷尔纳克,山将会得以实现。马雅可夫斯基感觉到自己,我们假定一下,是乌拉尔山,——他便成为了乌拉尔山。没有了马雅可夫斯基。剩下的是乌拉尔山。帕斯捷尔纳克想象乌拉尔山在自己身体内,就用自身制作出了乌拉尔山。没有了乌拉尔山。剩下的是帕斯捷尔纳克。(通用的说法:没有乌拉尔山,只有帕斯捷尔纳克的乌拉尔山,就像它原本的那样:我是在引用所有读过《柳维尔斯的童年》[2.
帕斯捷尔纳克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以及乌拉尔诗歌的读者的话。)
帕斯捷尔纳克——吸收,马雅可夫斯基——输出。马雅可夫斯基把自己变为了外物,将自己溶解在外物之中。帕斯捷尔纳克将外物变成了自己,将物溶解到自身之中:是的,哪怕是最难以溶解的物体,譬如乌拉尔山的岩石。所有乌拉尔的岩石都溶解在他抒情诗的语流之中,正因为这些,他的诗歌语流才那样沉重、那样笨重,以至于它成了——不,甚至不是巨流,因为它溶解的是均一的土壤——而是一种饱和(整个世界)溶液。

帕斯捷尔纳克在窗前|


▶
版权归译者所有,译者已授权发布。

▶
院外计划
不同的板块分进合击:
汇集、
映射、交织、对抗,突破各自的界限,
打开已在却仍未被再现的环节,把握更为共通的复杂情势,
循序渐进、由表及里地回应
批判者与建造者的联合
这一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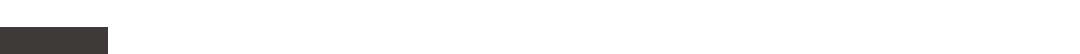
与马雅可夫斯基共事
写于马雅可夫斯基逝世十周年纪念活动前夕。与此同时,罗钦科与斯捷潘诺娃还在筹备发行单独一期《建设中的苏联》杂志,以纪念马雅可夫斯基。这个自革命前夕就站在先锋派运动旋涡中心的新派诗人,极擅长用其动听而富有感染力的演讲方式在公开场合朗读他的诗歌,搅动起一股疯狂的、未来主义的情绪。1912年,罗钦科在喀山聆听了一场如马戏般“翻天覆地的舞台景观”的未来主义演讲,留下了他关于马雅可夫斯基的最初印象。罗钦科这个原本已有左翼倾向的艺术学生,也因此成为了马雅可夫斯基的坚定追随者。对于罗钦科而言,马雅可夫斯基是富有魅力、却又够不诗意的诗人,是无私体贴的朋友,也是虚荣好胜的赌徒。
罗钦科袒露出对革命初期时光的复杂情感,他屡屡强调,尽管借回忆马雅可夫斯基牵出了左翼艺术家的无数生活、工作轨迹,但他不是颂扬也绝非要赞美那段为新艺术斗争的生活。可同时,罗钦科耿耿于人们已经有意忘记、闭口不谈“是左翼艺术家最早开始与布尔什维克合作”的事实。马雅可夫斯基恰自杀于革命时局的转向之时,他的死之复杂性,同罗钦科对革命的复杂感情一起藏匿于这篇零零散散的回忆书写中,带着罗钦科曾在少年时代有过的那般忧郁。
一|一张海报,三个未来主义者|有敌视的人,也有仰慕的人。后者是很少的。很显然,我对他们的喜爱远远超出仰慕者的程度;我还是一个追随者。
二|我们就是“新信仰的主谋”|对我来说一切都很不容易:要讲述回忆,要克服所有的疑虑,尤其是关于这一切偏差和对我本人的生平描述是否正确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