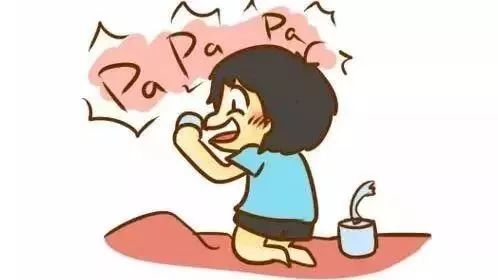读博士对我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十岁之前,我就明确了当科学家的想法,小时候的我会经常拿着电路图、显微镜或者pH试纸出去玩。高中时,我参加生物竞赛做组织培养:切一块小萝卜,然后看它长成一个完整的组织。这是我第一次在实验室里直观感受到生命的神奇,让我决定要做一个生物学家。大学时,我参加了好几个科研项目,了解到人体内不同的细胞如何协作、一层层地传递信号。这样一个非常精妙和有意思的系统让我产生了很深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所以我决定继续攻读博士,做生理病理方向的研究。我觉得我有能力做好科研,用我的智慧把科研项目设计得精巧且完美。
但博士期间的科研经历,并没有按照我预期的方向发展。
首先是我没有意识到由于科研的不确定性,努力不一定产生成果。我想我们刚开始读博士的时候,都是非常懵懂的。但出于幸存者偏差,有些科研做得成功的人会告诉你:“只要你足够努力,或者只要你足够适合科研,你就一定能做好。”但我当时的项目就属于,虽然我努力思考,也努力实验,但就是不能产出成果的状态。所以我产生了“一定是我不适合科研,所以才做不好这个项目”的想法。
另一方面,因为成为科学家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我把所有的自我价值都寄托在这件事情上。因此当科研不顺利、没有好的文章发表,以及没有得到导师和同事在科研上的认可时,我的自我价值感就降低了很多。
最后的结果是,我没有自信了。当我以前受到外界的规训时,我有底气说这不是我的问题,而是其他人或者是刻板的教育体系的问题。但读博的时候,我有时候会觉得自己的自我认可并不是特别站得住脚。以至于到最后,我对别人的评价变得非常敏感。当别人说我可能更适合做其它事情而不是科研时,我有时会觉得他们说不定是对的,尤其是在我科研做得不太顺利的时候。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读博士之前让我觉得很自豪的地方,好像读完博士之后突然都没了。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博士第二年的感恩节。当时我已经做了一年的基因敲除鼠表型筛选,但一直没有筛到新的表型。那天晚上,我一边在实验室加班,一边给好朋友打着电话。突然我看到了一个新的表型。我立马换到了第二个生物重复样,发现表型还在!不是随机的!我当时就哭了,最开始是因为高兴,但很快这种高兴变成了委屈:同年级的同学一年级时课题就有明确方向了,为什么这件事情在我博士二年级才发生?这种情绪上的改变,在我博士四年级的时候也发生了一次。当时我第一次讲海报,特别开心。但讲完之后我就想:“好像也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别人二年级就讲过了。”虽然科研大多数时候是一个人的旅程,并不需要跟别人比较,但我心里对自己有一个预期的时间线,而我觉得我的进度一直是远远落后于这个预期的,所以在读博期间,我一直觉得很屈辱。
后来我反思当时科研之所以如此不顺利,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这个项目确实难度比较大、随机性强。但另一方面,我跟导师之间的沟通也存在问题。实验室的主流方向跟我的课题有较大的差距,所以导师在我的课题上花的时间较少。而我虽然读了很多相关的论文,但作为一个科研新人却缺乏科学上的直觉,所以并不知道问题所在。本来我们可以很好地互补,但由于那时我们都对一个良好的博士培养过程比较懵懂:在我之前导师很少带学生,而我也是第一次读博士,所以我们的沟通一直没说到点子上,这也是比较遗憾的地方。